印度次大陆常被视为地缘政治的 “天然堡垒”—— 北枕喜马拉雅山脉,东接东南亚雨林,西临阿拉伯海,南望印度洋,广袤的恒河平原孕育了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这片占全球陆地面积 2.4% 的土地,承载着 17% 的人口,拥有全球最高的耕地面积和热带季风带来的丰沛降水。
尽管其耕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46%,远超中国的 14%,但恒河平原的沃土与德干高原的贫瘠形成鲜明对比,导致农业生产呈现极端不平衡。更关键的是水资源分布的时空错位 —— 全国 60% 的降水集中在 6-9 月的西南季风期,东北部乞拉朋齐年降水量可达 10000 毫米,而西北部塔尔沙漠却不足 200 毫米。这种极端差异使印度陷入 “旱涝两重天” 的困境:2022 年热浪导致小麦减产 8%,2023 年雨季又使 300 万公顷农田被淹,粮食产量波动幅度长期维持在 10% 以上,远高于中国的 3% 以内。
印度全年无霜期理论上可实现作物三熟,但持续高温加速土壤有机质分解,导致土地天然肥力低下。德干高原的红壤区有机质含量普遍低于 1%,而中国东北黑土区可达 3%-5%。为维持产量,印度农民被迫过量施用氮肥,每公顷化肥使用量达 163 公斤,是中国的 1.2 倍,却因缺乏磷钾配合导致利用率不足 30%,形成 “高投入 – 低产出” 的恶性循环。农业生态困境使其虽拥有世界最多的耕地,粮食总产量却仅为中国的一半,单位面积产量更是只有中国的 36%。
印度半岛伸入印度洋的地理位置,本应使其成为海洋贸易的枢纽,但历史上却形成了 “陆权思维锁定”。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虽阻挡了外敌入侵,却也切断了与亚洲腹地的陆路联系;东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沼泽密布,成为与缅甸的天然屏障;西部的塔尔沙漠则是与巴基斯坦冲突的永恒导火索。 “易守难攻” 的地理特征,反而助长了印度的战略被动性 —— 独立后 70 余年中,印度与周边国家爆发了 5 次大规模战争,军费开支长期占 GDP 的 2.5% 以上,挤压了生产性投资空间。
热带季风的不稳定性使印度成为世界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遭受 2 次气旋、5 次大规模洪灾和 12 次区域性旱灾。2023 年古吉拉特邦气旋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该邦 GDP 的 3.2%,而同期中国台风造成的损失仅占全国 GDP 的 0.3%。这种频繁的自然冲击不仅直接破坏生产设施,更形成了 “灾害 – 贫困 – 灾害” 的代际传递:比哈尔邦等灾害频发区的贫困率高达 3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8 倍,大量资源被用于灾后重建而非长期发展。
17 世纪东印度公司到来前,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手工纺织业中心,占全球纺织品贸易的 25%。但殖民者通过摧毁传统手工业,将印度改造为原料供应地 ——1900 年印度出口商品中 80% 为棉花、黄麻等原材料,工业制成品仅占 5%。这种 “去工业化” 政策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印度独立时现代工业产值仅占 GDP 的 10%,人均工业产值不足中国的三分之一。殖民时期修建的铁路网络看似先进,实则完全服务于资源掠夺,90% 的线路连接原料产地与港口,而非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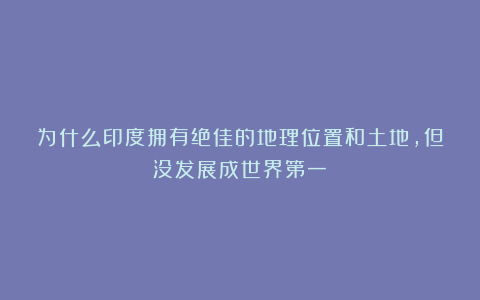
英国为便于统治,刻意维持了印度土邦与直辖区的分割状态,全国最多时有 562 个土邦政权。这种行政分裂的惯性延续至今,印度虽然名义上是联邦制国家,但各邦拥有高度的税收自主权和政策制定权,导致全国统一市场难以形成。例如商品与服务税(GST)直到 2017 年才勉强推行,比中国晚了 22 年;各邦环保标准差异巨大,使跨区域投资成本增加 20%-30%。中国秦朝的 “书同文、车同轨” 传统,为后世统一市场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基础。
尼赫鲁推行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虽旨在摆脱殖民经济模式,却陷入了 “官僚主导” 的泥潭。1956-1990 年间实施的五个五年计划,通过 “许可证制度” 对私营企业实施严苛管制,创办企业需经过 70 多个审批环节,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仅 0.5%。这种制度僵化使印度错失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时,印度工业占 GDP 比重反而从 1950 年的 17% 下降到 1990 年的 16%。直到 1991 年经济危机后,印度才开始放松管制,但官僚体系的惯性使其改革进程比中国缓慢得多。
尽管印度宪法已废除种姓歧视 75 年,但 4000 余种亚种姓构成的社会金字塔依然坚固,跨种姓通婚率不足 5%。表列种姓占人口 16.6%,却集中了全国 40% 的贫困人口,其识字率仅为 66.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0.9 个百分点。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婆罗门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达利特人的 8 倍,这种不平等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已注定 —— 比哈尔邦的调查显示,低种姓儿童的辍学率高达 45%,是高种姓的 3 倍。这种人力资本的分层损耗,使印度虽拥有 14 亿人口,熟练技术工人占比却仅为中国的 1/3。
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元信仰并存,却缺乏有效的融合机制。宗教冲突平均每年造成 200 余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的 0.3%。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印度教对牛的崇拜导致全国牛存栏量达 3 亿头,居世界第一,却因禁止屠宰造成每年 1000 万吨牛肉的机会损失;伊斯兰教的斋月习俗与农业生产周期时常冲突;基督教传教活动则引发文化抵触。这种宗教文化差异增加了社会协调成本,使政策执行效率降低 30% 以上。
农业虽占 GDP 仅 16%,却承载了 45% 的就业人口,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大规模隐性失业 —— 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 GDP 仅为中国的 1/4。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制造业占 GDP 比重长期徘徊在 15% 左右,远低于中国的 27%。更致命的是产业链断裂:印度软件业虽发达,但硬件制造能力薄弱,手机产量中本土零部件占比不足 15%,而中国可达 70% 以上。
印度每千人拥有公路长度仅为中国的 1/3,且 70% 为未铺装路面;铁路平均时速 46 公里,是中国高铁的 1/10;电力普及率虽达 99%,但年停电时间平均达 150 小时,工业用电成本比中国高 40%。这种基础设施滞后使物流成本占 GDP 的 14%,是中国的 1.7 倍,严重削弱了产业竞争力。尽管莫迪政府提出 “基础设施建设年” 计划,但联邦制下的财权划分制约了投资能力 —— 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仅为 41%,而中国达 53%,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长期低于 GDP 增速。
印度洋优势未能转化为战略主动权。印度虽控制着北印度洋关键航道,却缺乏相应的海权投射能力 —— 海军总吨位仅为中国的 1/3,航母数量不足中国一半。更重要的是经济影响力的缺失:印度与非洲贸易额仅为中国的 1/5,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足中国的 1/10。
印度虽通过软件外包融入全球经济,但其参与度远低于中国 —— 贸易战 GDP 比重仅为 48%,比中国低 20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额不足中国的 1/5。这种有限开放导致全球化红利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地区,信息技术产业贡献了出口额的 20%,却仅创造了 3% 的就业。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全方位开放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大,制造业出口占全球 14.7%,带动了 4 亿人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