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内容提要
自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多有关注其中的《自序》,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了阐释。通过强调这一文本的虚构性,考察其中包含的“书写”与“记忆”的复杂关系,本文重新探讨了鲁迅文学的“起源”的能量和冲动,以及文学写作与历史的关系。书写和记忆的辩证运动不但构成了鲁迅创作生涯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且也为如今反思历史书写、历史记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视角。
关键词
鲁迅;《〈呐喊〉自序》;书写;记忆
引言
自从鲁迅的《呐喊》出版以来,国内外研究者们对于这部小说集的解读早已汗牛充栋。无论是其中收录的一些著名作品——如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1918)、《孔乙己》(1919)或发表于《晨报副刊》的《阿Q正传》(1921)——还是作为整体的《呐喊》,这些文本对于 “新文化运动”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对于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小说编集时的一种交代,写于1922年末的《〈呐喊〉自序》,也构成了研究者们探讨鲁迅的早年经历、创作动机和缘由等等因素的关键文本。其中涉及的一系列议题或意象,如“铁屋子”隐喻、“幻灯片事件”和“弃医从文”的决定、从事文学事业遭受挫折后的十年沉寂等等,也反复得到了讨论。
不过,就像汪晖提醒的那样,《〈呐喊〉自序》(以下略称《自序》)并不仅仅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文本;毋宁说,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小说式的文本,有着复杂的内在构造。[1]这一点不仅体现为:当研究者将侧重点放在这一文本的不同细部时,文本整体呈现的面貌可以迥然相异[2];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序》中叙述的种种有关小说集《呐喊》形成之前的作者个人经历,经过叙事者的一种特定的形式设置,带上了某种非个人的、去心理学化的色彩,从而成为推动和促成《呐喊》诞生的各个重要环节。鲁迅对于这种形式设置的关键的提示,尤其体现于这一文本的第一个段落。通过重新细读这个关键段落和《自序》,本文将探讨其中凝结着的“记忆”与“书写”的复杂关系,并探讨这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文学的起源——反过来说,这一起源要求读者不断地回到现代文学的原点,不断地将文学和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放置在文学写作所开创的独特空间中予以重新考察。
《呐喊》,新潮社1923年8月初版。
一、“梦”与“回忆”
如果说《呐喊》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质起点,那么在形式和内容的意义上,可以说《自序》构成了这一起点的起源。从内容上而言,鲁迅确乎是通过这个文本向读者透露了《呐喊》的创作动机和语境;从形式上而言,尽管《自序》的写作晚于其中收录的各篇小说,但“序言”的功能使它占有了一个结构上的先在位置,一个既内在又外在的位置。因为和所有序言所占据的奇特位置一样,《自序》既属于《呐喊》,同时又相对于《呐喊》的诸篇小说而处在一个“外在”的视点上。而且,一旦打开《自序》便会发现,迎面遇到的第一个段落似乎又并没有回应读者对于“序言”的通常预期,即它应承诺给出的、关于创作背景和语境的交代。因为鲁迅以一个奇特而模糊的、关于“梦”和“回忆”的论述开场:“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3]
包括汪晖在内,既有的研究者似乎没有强调这个文本中“梦”和“回忆”的区别,仿佛两者可以替换——而研究者们有意无意默认的这一混淆,或许恰恰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文本效果,因为这两个语词的交替实在太过明显,仿佛叙事者在邀请读者进行这样一种置换,同时也邀请细心的读者思考其中的差异。在此,有必要完整引用《自序》第一段话: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4](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呐喊〉自序》首页(初版本影印版)
的确,在这里,叙事者很可能是在一般所谓“理想”或“梦想”的意义上谈论“梦”,因为后文明确提到了叙事者留学时期怀有的一个“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5]就此而言,“梦”可以相对直接地以语言和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它直接对应于叙事者曾经抱有的某些计划、打算、安排和意图。从后文的记叙可以知道,“梦”的内容包括救治国人、投身文学活动等等——总而言之,即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启蒙”的事业。(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将这里的“梦”和鲁迅在《野草》等作品中复杂编排的“梦”联系起来,或许并不恰当。)
无论如何,可以说《自序》开端于叙事者已然大半将其忘却、却也并不为之可惜的“年青时候”的“梦”。毫无疑问,在鲁迅眼里,同时代参与“新文学运动”的人们,也同样是尚未经历过“寂寞”的“做着好梦的青年”。[6]在这个意义上,开头一句“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的“也”字,不仅将叙事者与当下的年轻人隔离开来,也将他和自己曾经做过的“梦”隔离开来。
于是,当第二句话转向“回忆”的时候,“梦”和“回忆”的区别便清楚了:“梦”不等于“回忆”,但“梦”是“回忆”的内容或对象——或更准确地说,“梦”属于“不能全忘却”的过去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使用的拗口表述“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将“梦”和“回忆”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叙事者并没有说,自己仍然记得一部分的“梦”,而是说,有一部分“梦”无法被彻底忘却,而这些“不能全忘”的“梦”就成为“已逝的寂寞的时光”——也就是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进而使他感到“寂寞”。叙事者处在和记忆而非遗忘的斗争之中:他想要忘却,但是不能够。因此,“梦”与其说是主动“回忆”的对象,不如说是无法被忘却的、叙事者不得不记起的过去;反过来说,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不是梦本身,而是梦的破碎。记忆是梦的破碎或失败之梦。这些不断回归的记忆,构成了《呐喊》的“来由”,构成了鲁迅文学创作的起源。众所周知,无论是学医救治病人的梦,还是其后弃医从文、翻译外国文学以改造中国文艺的梦,甚至是所谓“启蒙”的梦,对于鲁迅的个人经历而言都是失败的经验——都是“梦”的不圆满和瓦解。无法忘却的是梦的碎片,而不再是曾经的“好梦”;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破碎的梦及其带来的寂寞,面对梦的破碎成为过去的失败经验,像有些论者主张的那样,认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叙事者出于对“好梦”的忠诚而开始提笔写作,似乎就没有切中要点。
二、作为身体性经验的写作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失败的经验构成了鲁迅文学的起源,但这些经验本身并不是文学性的经验,而是身体性、乃至生理性的经验: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7]
叙事者告诉读者,梦的瓦解的失败经验所带来的寂寞,如“大毒蛇”一般缠住他的灵魂[8],使他必须有所动作。不是为了再炮制一个“梦”,不是为了抽象的理念,而是为了存活下去,为了消除痛苦。为了生存,必须抵抗记忆。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讨论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时提出的关于“记忆”的区分,那么可以说,鲁迅在这里涉及的记忆固然不是主动想起某事的“意愿记忆”(mémoire volontaire),但甚至也不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9]——不是不期然地撞到主体身上、使当下和某段遥远的过去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偶然关联的记忆,而是一种更为激进的“非意愿记忆”,它始终纠缠着主体,同时却如外在于主体存在一般,使主体对之无能为力、被其压垮。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自序》或许就可以被解读为一则关于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记忆的寓言。
《〈呐喊〉自序》初刊于《文学旬刊》1923年第9期
根据接下去的叙述,鲁迅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是自我麻痹,不去面对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不问世事的“抄古碑”的十年,就构成了这种对于记忆的逃避乃至压抑。竹内好认为,这段时期构成了鲁迅文学的晦暗原点。例如,他在《鲁迅》(1944)一书中写道:
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10]
不过,与竹内好的判断形成对照的是,根据《自序》对于这段时期的描述,当面对令人窒息的、不能忘却的记忆的纠缠时,逃避和自我麻醉并不是唯一的应对方式,甚至不是恰当的应对方式。或许不采用“回心”等难解的说法,而借助精神分析的进路,可以更有效地说明鲁迅在这段时间内从“凝重的沉默”到“呐喊”的转变: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没有什么发生在主体身上的记忆能够被压抑和消除;试图压抑的记忆,始终会以某种变形的方式回返。具有症候意义的是,就在讲述了自我麻醉的“奏了功”之后,叙事者立刻提到了另一个“未能忘怀”:“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1]
不能忘却于曾经失败的梦,但也不能忘怀于由此造成的“寂寞的悲哀”——恰恰是在这里,遭到压抑和回避的“梦”通过“记忆”的变形方式而重新回到叙事者那里,从他的麻醉状态中撕开一个裂口,令他“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换句话说,这些不得不记起的失败的梦或梦的失败,恰恰是在貌似潜伏或被忽视的时候,重新要求这个麻痹的主体作出回应;记忆促使鲁迅不得不行动,不得不面对它,不得不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汪晖所说,鲁迅的书写具有“很强的被动性”。[12]不过,或许与之相对而具有“主动性”的,并不像汪晖所认为的那样,是困扰和纠缠着叙事者的梦(或记忆),而是出于生存需要的、身体性的抵抗动作,即写作。
在这里,书写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或许可以说,书写在此带有和记忆相同的构造或语法——两者都源于某种仿佛是外在的、主体无法控制的、强迫性的、却又内在于主体的命令,一种既“自律”又“他律”的命令:“不得不”(因此“听将令”就不仅仅是一个来自例如《新青年》编辑部的命令,同时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来自自我内部和文学内部的命令[13])。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书写也成为对于记忆的抵抗,成为对于不断复归并纠缠自己的失败之梦的抵抗。
因此,“书写”和“麻醉”构成了应对“记忆”的两种行动,虽然后者最终并不奏效,虽然强迫般回归的记忆会促使叙事者从后者转向前者,但两者终究是不同的行动。于是可以说,在文学本体论的意义上,十年沉寂的逃避和麻醉并不如竹内好所认为的那样,构成了鲁迅文学的原点,毋宁说,它构成了“文学=书写”这一原点性行动的消极症候。鲁迅文学的原点不是沉寂(也即自我麻痹),而是试图摆脱哪怕在沉寂状态中也无法逃避的、记忆的复归的冲动。相比于自我麻醉的回避策略,“书写”无法直面的记忆,为的是抵抗记忆,为的是忘却。与柏拉图以降的哲人们对于书写的理解相反,对于鲁迅而言,书写不是为了帮助记忆却反而助长了遗忘的手段,而是(徒劳地)忘却的手段。
在我看来,书写和记忆的这种对峙关系,构成了鲁迅文学生涯中一条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例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写于1933年的文章中,鲁迅又一次提到了写作、记忆和遗忘的关系,又一次强调了书写中包含的身体或生理意义上的迫切性: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14]
《牺牲》,珂勒惠支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鲁迅将这幅作品寄给《北斗》期刊作为对柔石等人遇害的纪念。
对于鲁迅而言,当时“左联”五位作家的牺牲太过沉重,以至于记忆本身——在既定事实的意义上,在客观和实证的意义上——成为令人窒息的负担。如果说《自序》中的“大毒蛇”意象仍然显得抽象,那么年轻的牺牲者的鲜血则实实在在地形成了记忆的重负,以至于“书写”成为写作者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15]
《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末页)
在这段关键的话中,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书写在此构成了一种忘却乃至背叛,但不是忘却和背叛牺牲者和他们的鲜血——因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16]——而是忘却和背叛那个既定的、似乎不可移易的事实(青年人的死亡)在当时被官方意识形态赋予的特殊意义。第二,因此,通过书写的介入,作为客观性事实的记忆对象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以便写作者可以“延口残喘”,可以呼吸,可以生活。书写通过背叛和动摇记忆而抵抗记忆,书写使得过去发生的事件不再仅仅是如石头一般不可撼动的客体,书写每一次的介入都为过去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书写将不断复归的、令人难以承受的记忆扭转为具有生产性的、带有裂隙和破绽的文本。
三、书写与赋义
对于鲁迅而言,记忆始终是一种身体性和生理性的存在,一种威胁到生存的存在,一种无法如实再现的存在。记忆的压迫促使人不得不行动,不得不写作,而书写既是对记忆的抵抗,也是对记忆的赋义和表达(articulation),书写为记忆带来不可预期的呈现方式。这种复杂的关系在1934年写下的《忆韦素园君》一文开头得到了具象性的惊人表现: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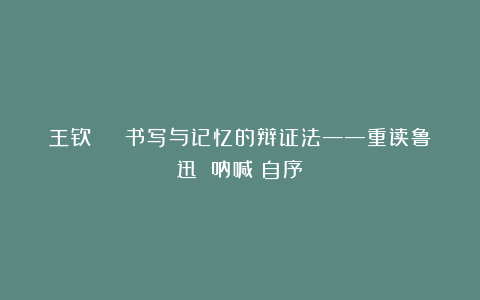
《忆韦素园君》手稿
在此,记忆有如被刮过的鱼鳞,以零落的方式牵动着生者的感受:一个鲜活而血腥的意象。记忆始终与当下相关,与当下的生命相关。记忆召唤生者当下的动作。在这里,这些零落的记忆将经由书写而得以“翻腾,闪烁”,得以被表达和重组,从而获得新的、不可预料的形式和意义:通过书写,主体才能“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于是,书写不仅是抵抗记忆的方式,也是为记忆构型的方式:经过书写的中介,压迫性的、指向失败经验和既定事实的记忆,将重新获得与当下乃至未来产生关联的可能。
然而,为记忆重新赋予可能性和意义,并不意味着篡改记忆,甚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记忆表征之间的对峙——仿佛一方面是创造性的记忆书写,另一方面是对于压迫性的、客体般的事实的记忆。毋宁说,记忆书写打开了一个文学性的空间,如张旭东指出的那样,在鲁迅这里,“回忆自身的叙事结构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是一种虚构”。[18]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根本性地表明,为何对于一段“相同”记忆的书写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经常以不同形式和意味出现,例如《自序》和《藤野先生》(1926)中对于“弃医从文”和“幻灯片事件”的不同叙述。尽管竹内好在两个不同版本的叙述之间做出了后者比前者更为“真实”的判断,但这里不妨先后撤一步,在将这两个文本同样视作“文学文本”的前提下,思考一下使得这些不同叙述得以可能的文学本体论条件。
在这一点上,鲁迅在1927年为回忆性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又一个“序言”——给出了提示。在这篇颇带有伤感色彩的文章中,鲁迅提到了小时候在故乡吃到的蔬果,并写到了它们留在记忆之中的、无法再现的美味: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19](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百草园
记忆与事实的背离这一具有怀旧意味的母题,在《社戏》(1922)、《伤逝》(1925)等作品中也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复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上述哪一个文本中,这一母题的出现都并不指向对于记忆的“祛魅”,而相反地指向了对于被事实所“证伪”了的记忆的偏执般的坚持。如果可以在脱离文本语境的情况下做一个暂时的鲁莽阅读,那么鲁迅在这里所谓的“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可以说对应着《伤逝》结尾的那个激进断语:“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20]
尽管已经有众多研究指出,《伤逝》的叙事者涓生在这里所谓的“真实”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真实”,而只不过是压抑“子君”的男性叙事声音所施加的另一层掩盖。[21]但无论如何,在明白了“不过如此”的事实之后依然坚持站在“记忆”这一边、依然坚持记忆中“旧来的意味”,在此成为写作者(此处是涓生)的一个决断,一个有关书写与记忆之关系的决断。就像小说中另一处所说:“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22]书写是为了生存:直接的、生理性的、切身意义上的存活,而不是抽象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伤逝》所呈现的涓生编织的“手记”,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在具体的、生理的意义上存活、为了继续前行而对不堪重负的记忆所做的表达;在这里,从这一表达的蛛丝马迹间寻求被“压抑”或“否定”的子君的“真实”,或分辩涓生和子君的是非对错,都并不损害“书写”这一行动穿透整个文本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不过,回到《〈朝花夕拾〉小引》,既然已经明了记忆和事实的距离,既然已经从怀旧和乡愁的情绪中解放出来,叙事者为什么还要“时时反顾”这只有在记忆上留存的意味呢?关键在下一句话: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23]
这里所谓的“十篇”,指的当然是收录在《朝花夕拾》里的文章。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以至于书写在这里成为记忆的某种转录或翻译,仿佛记忆内容可以依靠语言这种透明的媒介而忠实地、充分地、完整地、毫无偏差地获得另一种形式,即获得一种公开的、可流通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叙事者马上补充说,这些“抄出来”的文字与“实际”、与客观发生了的、如石头一般稳固的事实并不相同,以至于作为誊抄、转录或翻译的书写——就像任何一种转录和翻译都必定在过程中产生与所谓“原文”的偏差一样——在根本上不可避免地会偏离作为客观性事实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偏差并不源于某种偶然的失败或错误,并不期待纠正或质疑,因为“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换句话说,在书写的当下,这些对于记忆的表达具有唯一的真实性,甚至可以说,这些偏离“实际”的转录或翻译,构成了记忆对象本身。就像那些儿时的蔬果留在记忆上的“旧来的意味”无法被实际的味道所“证伪”,同样地,叙事者通过书写将自己的记忆开放给一个独特的、充满可能性的、不可证伪的文学空间:在这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已经无法构成对这些书写的质疑或反驳。这里没有历史实证主义者插足的余地。
四、书写的起源:重写
回到《自序》中有关鲁迅开始创作《呐喊》集中诸篇小说之前的个人经历的叙述。不难发现,这些“事实”在鲁迅以后的文章中会不时以其他面目呈现,或以其他方式得到再叙述;但在这里,它们均在第一段所设置的书写与记忆的复杂关系中得以重新组织和表达,以至于那些在其他文章中、在不同语境下根据不同的叙述和重述方式而可能带上个体性感伤色彩乃至竹内好所谓“回心”色彩的事件,在《自序》的叙事方式中,都执着而坚定地指向了当下的文学革命——父亲生病和家道中落令叙事者萌生了离开家乡、出洋留学的念头,而中医的无效使得他坚定了学医的意志;接着“幻灯片事件”让他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断,而一系列的失败经历又凝结为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并有待“金心异”的对话来促成又一次转机,让叙事者终于决定开始写作。可以看到,不同于《父亲的病》《藤野先生》等文章中的叙述,《自序》在记述这些个人经历时并没有留出太多的“闲笔”,并没有铺陈过多的细节,并没有徘徊于暧昧的对象上,而是将一切事物都安置在一个几乎环环相扣的、严格的事件因果序列中。自然,鲁迅说,这么做是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是为了“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也就是为了当下的现实意义;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这些叙述并不比(例如)《藤野先生》等文章中的叙述更加“真实”或更不“真实”——相反,无论何种叙述都是“真实”的,因为对于记忆的每一次书写或铭刻、每一次表达都是真实的。每一次的书写,都是对记忆的可能性和可能化(possibilization)的承诺,都是对记忆的客体化和意义固定化的抵抗。因为只有试图独占性地掌控对于历史的阐释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会试图以单义的手段将对于过去发生之事的表达固定为无法改变、不可置疑的权威话语;而与这种独断的、排他性的政治话语相对,文学性书写的每一次介入都同样真实、也同样脆弱地为记忆创造与当下和未来对话的可能空间,为看似封闭和死去的“过去”创造一个可以与当下现实和鲜活的生命平等沟通的空间。
书写的每一次介入都同样真实,因为每一次介入都是当下的介入,每一次介入都回应着当下历史和生命的要求;书写的每一次介入也都同样脆弱,因为每一次书写都并不试图以不可改变的、确定无疑的方式将历史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意义结构和语法之中。
正是通过书写,通过不断的书写和重写,鲁迅的失败之梦不再仅仅通往一个既定的失败结局,而是在不断的叙述和再叙述的过程中、在各种不稳定的意指链条中,将读者、也将他自己带向意想不到的出口。正如本雅明所说:“时间的分分秒秒都可能是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门洞。”[24]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意味着重写,意味着用形式和意义的多样性打破过去发生之事在线性历史框架中的单义性。而如果事件的发生本身已经是一次铭刻,一次文字性或非文字性的书写,那么在文学的意义上,每一次书写都已经是重写:书写起源于重写。
于是,鲁迅在《自序》中以述行的方式,凭借书写而将“大毒蛇”一般纠缠着他的无法忘却的记忆转化为使人前驱的“呐喊”。如张旭东所说:“记忆有自身的强迫和自身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生产性的暴力。然而鲁迅从一个纯粹文学的角度可以说把握了过去的暴力,强力地抓住它并将它用作一种表达方式。”[25]在文学的意义上,在叙事和构型的意义上,对于记忆的书写摆脱了“时间和历史、道德文化的粗暴主宰”[26],从而为新的生命、新的历史做好准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之前,在这个起点的起源处,也就是在《自序》这个独特的文本这里——甚至可以说在起源的起源处,在《自序》的起源处,存在着一种带有激进的文化政治内涵的书写,它将无法忘却的记忆所代表的那些通常而言并不属于文学的内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纳入文学的空间之中。
《呐喊藏书票》,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然而,这个动作本身却并不是文学性的,而是身体性、生理性、始终带有生存意义的。在借助书写和记忆相搏斗和抵抗的过程中,在为了生命而不得不“挤”出来的文字中,书写最终会将原本令人感到寂寞的、缠住灵魂的、使生命窒息的记忆,转变为丰沛的、向生命的新的可能性开放的叙述。如钢琴演奏前的调音那样,鲁迅在《自序》的第一段中为接下去要叙述的经历安排了一个独特的形式设置,使这些往事浮出地表并与当下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最后所说的,“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27]——这一次的书写呼唤和要求下一次的书写,不是为了修正错误甚或恢复名誉,而是为了下一次、再一次的新的当下生命、为了新的历史情境而重新将过去转化为当下的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次、每一次的书写都在生存的意义上对应着这一次、每一次的当下的生命和生活的要求,正因为书写的紧迫性和身体性,书写对于鲁迅而言始终不是有待鉴赏把玩的艺术品,而必定是要随着当下的生命一起消亡和速朽的“野草”。这既是鲁迅自己的愿望,也是书写作为一种与生命相关的动作、作为生存和呼吸的手段而产生的内在要求。因此,悖论性的结果是,一旦完成了书写的行为、甚至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刚刚形成的文字就已然是要被忘却、要被抛在脑后的东西。书写为记忆赋予了当下的活力和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一旦这种可能性得以被表达出来,作为形象和客观存在的文字本身就需要被忘却:在此,鲁迅一再提及的母题又一次回返——书写是为了忘却,或书写作为忘却。但是,既然每一次书写都要求、呼应着下一次书写,既然每一次书写都是不稳定的、脆弱的、开放的,忘却就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的遗忘,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遗忘,它意味着向着不同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开放,同时也意味着每一次书写所确立的意义结构都必须是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
本文注释(滑动阅览)
[1] [12] 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2] 例如,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鲁迅》(1944)中尤为强调鲁迅留学归国后“抄古碑”的十年,认为这一时期构成了鲁迅文学的某种堪称“无”的原点(参见[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与之相对,汪晖在他的解读中更强调鲁迅所叙述的几个“梦”之间的关联,突出其一以贯之的对于“梦”的忠诚(参见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近年来,也有论者通过实证式的研究对勘《呐喊·自序》和爱罗先科的《时光老人》等文本之间的关联,从而探讨“铁屋子”隐喻等意象的由来(参见刘彬:《“旧事”怎样重“提”——以〈呐喊·自序〉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基于影响的研究往往容易让研究者低估《呐喊·自序》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形式设置以及文章各部分细节在这一设置内部所得到的安排和规定。而后者正是本文希望讨论的内容。
[3] [4] [5] [6] [7] [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37、437、438、442、440、439页。
[9] 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 [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45-46页。
[1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明确交代,他所“未能忘怀”的是“寂寞的悲哀”,而不是尚未化为“寂寞的时光”的“梦”本身。也就是说,促使鲁迅不得不“呐喊”的,让他从静默状态中发声的,并不是他对破碎的“梦”的忠诚,而是“寂寞”——本来应该遭到压抑和回避,却仍然以“未能忘怀”的形式回归的“寂寞”。
[13]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关于《呐喊》写道:“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14] [15] [27]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93、502、502页。
[16] 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
[17]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65页。
[18] [25] [26] See Xudong Zhang, “Agonistic Memory, Compound Temporality and Expansion of Literary Space in Lu Xun,”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 13, No. 2 (2019), p. 209, 212,225.
[19] [23]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6页。
[20]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33页。
[21] 例如,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等。另一方面,也有论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这一文本放在涓生的主体构造层面予以考察,如邢程:《“苦闷”的再现——从厨川白村到“伤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2期。
[22]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33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4] [德]本雅明:《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6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形象与现实主义的边界研究”(19YJC75104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审:李静宜
二审:黄爱华
三审:姜异新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5年第3期,
原文、注释及相关内容欢迎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