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芝加哥是个矛盾丛生的大都市,阶层分化、犯罪、移民等现代转型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之成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与之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更剧烈的现代性大变局之中,燕京大学的社会学者们有着改造风气、建设社会的自觉使命。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就此开展了重要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二者共同的问题关怀使他们的研究形成了呼应和参照,燕京学派在吸纳芝加哥学派影响的基础上,更在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将社会学考察推向深入。本文中,各位社会学者就二者的关系做了精彩的对话讨论。
风、俗与生机
芝大和燕京的社会学田野
(《读书》2025年5期新刊)
二十世纪是霍布斯鲍姆笔下的“极端年代”,见证了欧亚大陆旧帝国的衰落和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与扩张。民族国家、政党组织、意识形态之争、族群身份的凸显所涌现出来的力量不断再造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而移民、城市化、资本垄断、经济危机以及消费主义下的孤独个体又不断瓦解传统的自然社区。社会组织领域的剧烈变动将社会学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使其从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蒙昧关系中脱身而出,将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重组视为核心命题。这一发展尤其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转型为代表。一九一四年,帕克(Robert Park)进入社会学系,很快成为社会学系智识的核心。他倡导田野调查,并以令韦伯叹为观止的芝加哥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带领后辈学生刻画城市景观。从出租车司机、舞女到失足的青少年,从城市统计学、生态区位到个人生命史,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上,都一改社会学的风气。社会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的附庸或是社会福音派的手段,而能从社会变化的搏动和脉络中理解时代中的“社会力”,这也开启了自进步主义时代以来围绕“社会”领域、“社会”议题来重塑政治组织的尝试。
与此同时,旧大陆的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诞生于此一时刻的燕京社会学也以北平为实验室,对窃盗、诱拐等各类失范现象,对北平的城郊、村镇在城市化中的变动进行了一手调查。无论在主题、方法还是关怀方面,芝加哥和燕京之间的关系都耐人寻味,几位学者就此展开了对话。
一、生命史、理解和教化
杜月:我们今天在这些经典文本中读到的并不是芝加哥学派对燕京学派的单向传播,更多的是二者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社区”作为一个自然史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学家的吸引力。“社区”概念将人类聚居区作为自然史中的生命形态去理解,这种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生命过程预设了一种源源不断地对外部环境变迁做出反应和调整的生命活力。在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视角下,城市社区的原型是植物的聚落。新的物种入侵之后会改变植物聚落原本的光照和土壤环境(比如松树会创造树荫),而这种改变的环境会使得更适合的植物(比如喜阴的橡树)继替原本的物种。在这一人文区位学的视角之下,外部物种的入侵恰恰是更加复杂的生命形态的基础。在《江村经济》中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蚕丝业向工厂企业的发展,作为一股“外界力量”引发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和一系列乡村社区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变迁,如婚期推迟和高利贷的入侵,以及村民对恢复社区活力的愿望,从而为另一股外界力量,即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进入社区做了准备。这种源于自然的生命活力并不会因长期的社会停滞而丧失,当外部力量入侵打破社区生态的平衡时,沉睡百年的乡村依然有潜力焕发新生。
第二个例子是,社区研究对于人格的关切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对于人心和人情的体认有很大的亲和性。芝加哥学派城市民族志学者核心的议题是迁移的“主观面向”:一个人离开原先的社区进入城市社区后,他的人格和性情发生了何种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城市生活展现为纷繁复杂的人性图景,在同一个街区之内,有以芝加哥舞女为典型的抛弃旧生活以融入新社区的“边缘人”人格,也有以中国洗衣工为典型的攀附于旧社区来抵御城市生活危机的“寄居客”人格。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格状态是一体的。一方面,伦理高尚的人格是社区组织的基础,比如杨开道讲乡约制度的根本政策就是中国传统的感化政策,须要依靠“有真人格,有真性情,可以感人,可以动人”的人作为感化中心。另一方面,社区也是人格形态的基础,比如费孝通讲“个人人格的完整,需要靠一个自己可以扩大所及的社区做支持”。社区研究对于人格的关注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们可以承袭自身的文化传统,回到具体的人心和人情中去讨论社会组织的问题。
王利平:在社区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联系研究者和“社区”中的人的纽带。此一时期的新现象是研究者以“平常人”的身份和心态置身于社会事实之中。当他们的好奇心或精英的改良心逐渐从社会研究中淡化,连接作为“普通人”的研究者与另一个“普通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呢?
早期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城市民族志中都有对犯罪的研究,而且都对步入歧途之人的“生命史”情有独钟。民族志案例中的主角大都不是大罪犯。克利福德·肖的经典作品《街头混混》(The Jack-Roller)借主人公斯坦利(Stanley)的自传展示了一个成长于破碎家庭、不招人疼爱的男孩。他不断徘徊在辍学和感化院之间,小偷小摸和打劫让他获得了短暂的自尊和成就感,而内心对美丑善恶的敏感又让他厌憎那些真正的成年罪犯。严景珊三十年代写作的北平惯窃的自传同样选取了一个人如何堕入以窃盗为职业生涯的故事,而不是将职业窃盗团体作为研究对象。严景珊选择窃盗作为对象,是因为窃盗是所有犯罪类型中最多且最普通的(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京犯罪统计显示,窃盗占总数的44.11%),是普通人最容易因为经济窘迫或是好吃懒做而滑入的犯罪类型。人们习惯出于道德感而畏惧或鄙视窃盗,也会对传奇故事中窃盗的手艺赞叹。但严景珊把握的既不是沉沦与拯救,也不是传奇,而是“窃盗也是一个人”的故事。肖在斯坦利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坏”男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如此细腻的感受,无论是对他沉浸其中的街区的眷恋,还是目睹成人监狱后发自内心的厌弃,都令他觉得犯罪绝不仅仅是由家庭、社区、堕落的伙伴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人步入歧途是对一系列变动的社会处境的连锁反应,是“一系列的体验”。田野民族志就是要将研究者置身于对象之中,去体认对象的人格形成,去解锁他的经验。在一个平行位置上,以共情之心揭示犯罪标签下普通人性格的形成,借由他的叙述催发自新的动力。因此,体察是早期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田野调查的共同出发点,由此出发,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伦理。
贾宇婧:《街头混混》不仅是应用生命史进行共情性研究的典范,也寄托着研究者对教化个体的期待。不同于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为代表的生物决定论者的路径,肖不厌其烦地通过少年犯斯坦利天真可爱的口吻来回溯他如何寄望于越轨来走出毫无温情的家庭,抵抗冷漠暴力的继母对他尊严感的伤害,但又宿命般地堕入更严重的犯罪。破败肮脏的波兰移民街区的确孕育了贫穷与苦难,但也是少年的情感之所系。通过对少年生命历程的自然主义呈现,肖在捕捉其天真本性的同时,内在化地理解了少年的犯罪行为,也洞见其良善本性与挣脱宿命的内在冲动——这是实现个体教化的根本,为社会工作者在此后开展的知识教育与价值引导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也深刻映照了伯吉斯将生命史方法纳入田野教学的期待,即揭示“个体内在展开的方式,他在道德上的纠结,他的理想追求以及现实中的成败经验”。
若用自然史的角度看待社区之解组,以生命史的方式去观察人格之解组,往往会发现,人格之解组就是社区重组的先声。这也是托马斯(W. I. Thomas)用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而非失范(deviance)来定义社会问题的原因: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规范和问题总是同时涌现,新的规范就在旧秩序解体的过程中生成。因而面对快速现代化不断加剧的外部冲突,与韦伯所提供的个体性的、悲观主义的应对方式不同,早期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城市研究者们以一种乐观积极的姿态应对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
二、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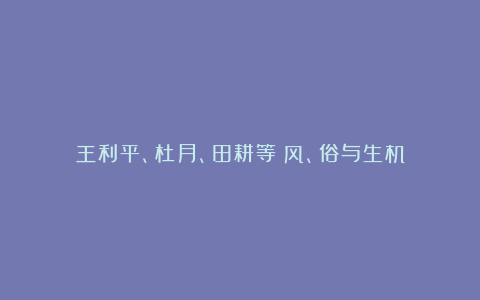
李小仪:对持续流动的生命体验的关照养成了个体的“心态”(attitudes),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则进一步构成了社会整体的“风气”(mores)。如何捕捉、描述并尝试塑造当时均处于转型之中的美国和中国社会的风气,也是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共同的问题关怀。正是在探寻民风民情的过程中,学者们得以走进特定地域空间背后广阔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并从中寻找现代转型中一系列问题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短短数十年从沼泽之上拔地而起的芝加哥,不但具备现代工业文明的原生底色,也是美国移民社会和拓荒精神的缩影。作为一座“典型的美国城市”,芝加哥的繁荣与衰落不但折射出美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万象,更成为整个都市文明史书写中考察现代性问题的天然试验场:作为一个巨大的“文明”产物,现代都市通过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将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谋生的人联结到一起,并汇入一张高速流动、筛选和分化的市场巨网。正是这张网将美国与大洋彼岸的欧洲连为一体,并将双方的“文化”交流从早期旅居式的散漫想象,拉入到了如何应对共性社会问题的现实讨论。矛盾丛生的现代大都市,由此成为这一时期的美国,乃至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大西洋世界“民风民情”的重要缩影。在芝加哥,一个个近在咫尺又截然隔离的都市社区,就集中反映了经济共生和文化共识疏离、私有财产与公共服务张力等一系列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越轨犯罪、阶层分化、移民融入乃至民主危机等多层面的社会政治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力图通过深入的城市社区研究,探寻开拓城市公共空间、凝聚内部社会共识的可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唤醒一座城市对其历史和角色的“自我意识”——一种基于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而形成的城市气质;由此在持续扩张的、日益显示出不确定性的市场秩序当中,重建于危机时刻能够“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的社区。
赵启琛:对于社区整体风气的刻画,使得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田野研究超越了服务于社会改良的城市调查,也突破了侧重描绘民俗和风俗的传统人类学研究。这种研究风格可以追溯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所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这本著作不仅是芝加哥社会学的典范,更为其后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提供了精神底色。托马斯在运用生命史方法对人物进行分析和刻画的同时,更着重体察了个体面对社会变迁时的心理变化。“心态”(attitude)和“社会价值”(social value)构成了观察和理解社会秩序变化的窗口,而这一视角被大量运用在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作品之中。这种对社会中人心的体察便是对风气的描绘。风气是无形的,它不像仪轨、制度那样能够按照模式刻画,而更多依靠研究者的感受、理解和共情。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和观念的塑造都是无意识的。同时,风气能够在风俗尚未变化的时候,敏锐地预示社会变动的方向。这种对于风气的描绘,使得芝加哥学派民族志不止于描述风俗、习惯和仪式,而是将社会秩序的变迁作为其核心关注。
如果读一读由帕克指导的博士生佐尔博(Harvey Warren Zorbaugh)的作品《黄金海岸与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1929),就能明显感受到其与传统民族志写作的区别。在这本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代表作中,作者从芝加哥河近北岸一个社区的变迁展现了芝加哥城市的风气变化。在这片只囊括了几个街区的空间内,芝加哥顶层名流所占有的黄金海岸,跟底层大众拥挤聚居的贫民窟比邻而居。城市里的富裕与贫苦、热闹与萧条背后展现的是身处其中的人在心态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这源于芝加哥城快速崛起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破碎和重建。这种对于社区整体风气的把握和描写,是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留下的宝贵遗产。随着一九三二年帕克来华访学,这种研究风格被带入燕京大学,也构成了燕京学派实地研究的底色之一。自此,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和燕京学派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田耕:燕京学派的前期和第一代芝加哥学派是同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社区当成风气酝酿的地方。清河镇作为燕大社会学系第一个试验区,是因为它是一个合乎调查理想的“自然社会区域”,不仅适合做整体的研究,而且其所以成为自然区域的理由,将会对社会学的调查者呈现。然而,在更年轻的赵承信看来,燕大在河北清河和山东汶上的试验区都属于乡建试验区,更典型的社区研究应该直指“社会学的实验室”。在赵承信的设想当中,“社会学实验室”是对未定的社会风气进行观察的场所,研究者的所言所行和被研究者的行动都应被视为研究的客观现实,对之要分别加以客观化。研究法的实验“就是现查员(investigator,赵承信译文)与村民的交互动作的一方面”,而村社区生活的实验,“就是村民彼此交互活动的一方面”。赵承信用“实验室”比拟燕大在平郊村的社区研究,是因为风气仰赖于发现,而不是约定俗成。
赵承信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正是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在帕克和伯吉斯的指导下发展出自然区域概念的高潮的时期。任何城市都有基于功能的空间划分,但并不是任何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都会构成自然区域。贫民窟、犹太区等之所以成为这一代学人的研究重点,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化渊源和政治影响,而是因为其处在过渡圈的生态动力上,基于生态位置和经络(nexus)而产生的民之性情在这一代学人眼中是更深刻的人性。自然区域是一个彻底的人为观念,因此在根本上并不相信由风到俗的制度路径。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无形当中走出了一条和他们的先驱孙莫楠(William Sumner)彻底不同的道路。
受此影响,吴文藻将社区研究前推到人文地理。社区的根本在于人、环境和文化,吴文藻这个概念的三个要素带有很明显的德国学者巴斯蒂安的色彩。好的社区研究能体现区域研究的潜能,一是“对现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二是将对人类行为的描写放在“纵横交错的复杂情境和相互关系”当中。吴文藻眼中,巴斯蒂安的“地理限界”开了此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区域”的先河。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民族志明白地包含了从“地理环境”和人(流动、适应和竞争)来研究区域的思路,这固然大大超出了此前进步主义社会调查,但较之民族学对“区域”(地方)的理解仍然远远不足。社区是可以被田野工作所接触的具体生活,所谓现代,其实意指“现在”,以吴文藻自己的话说,就是“活的文化”。对文化的感受不灭,现在就包含着历史。
吴文藻强烈的“现在时”是他试图整合风和俗的基调,他对燕京学派真正的改造和深刻的遗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其第一步的成果,是南迁后燕京大学在云南的一系列社会学民族志。
三、社区与现代社会转型
侯俊丹:清河试验之所以看重习俗的改良,也和抗战前的燕京社会学人对现实问题的关心有关,这个现实就是二十年代末国家权力下渗过程中县域行政陷入的危机状态。如何充分调动地方性资源,又保证基层社会与总体政治之间的协调一致,使其成为产生公共性福祉的来源,这一至今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近百年前便酝酿于燕京社会学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中。
二十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乡村生活运动,以保守主义姿态向作为民主基石的“乡镇”传统的复归,为许仕廉、杨开道等人提供了思考上述问题的域外视角,“社区”作为刺激社会效率生产,进而提升社会道德和团结的建制方案,构成了他们探索县域行政方案的理论基础。与今天被规定在政区范畴内来讨论的社区概念理解不同,在杨开道等学者那里,“社区”是因人的心态而不断改变边界和形态的实体,基于风俗和习惯而形成了内部秩序,由“社区”出发建设社会,意味着风俗和习惯构成了制约性条件,也孕育了生长、变迁的可能性。
这种整体性把握社会系统的视角,令杨开道敏锐地观察到政区的分割,以及围绕政区层级来进行行政结构建设,极易造成对“社区”这一由人们基于自然和历史条件而生发的生活形态的割裂的对待,在国民政府时期,对治安和财税治理效力的焦虑,随着权力向基层逐步深层地渗透,它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如多米诺骨牌一样,造成系统性的打击。“清河实验”正是在这一洞见基础上,调整地方社会和政府行政关系的躬亲实践,它在治理的单一逻辑之外,通过引入历史上的乡治传统,将“教养”原则重新带回到基层行政视域中。但这一努力并不意味着燕京学派学人向传统的复古式倒退,相反,他们同样警惕习俗的惰性及其可能诱发的狭隘的地方主义精神。“清河实验”正是在国家主义和地方法团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将这种平衡的政治原则的实现寄托于对基层社会中知识青年的培养。
对于这批深受“五四”洗礼的学人,科学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坚信有效的环境控制和组织建设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不二法门,这使“清河实验”不免陷入与复杂的在地性条件相龃龉的境地。对“清河实验”的整理与反思刺激着燕京社会学人们对“民情—制度”关系的更深入的思考,之后围绕“市镇”而展开的社区研究——无论是费孝通在云南禄村研究中对“社会效率”背后蕴含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反思,还是赵承信在平郊调查中对物质生产所蕴含的风习意涵的揭示,都体现了战后学者与早期燕京社会学之间的对话。这些研究通过对“社区”的人性复杂意涵的深层把握,拓宽了对中国现代转型理解的向度。
傅春晖:从学科史来中国看,早期社会学的市镇研究和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集中地体现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系列研究当中。帕克明确意识到了美国都市社会与中国乡村社会的不同,他到燕京大学的讲学活动促成了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把关注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
受帕克讲学影响的社会学研究中,杨庆堃的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深刻领会了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思想,其对于邹平市集的研究也得到了帕克的指点,认为他获得了“极有兴趣和重要的材料,且详以区位学研究观点相示”。当然,作为一篇习作,该论文不免带有一些形式化的色彩,不过杨庆堃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了很多拓展,在去美国之后,他关于鹭江村和佛山镇的研究,都更加注重家庭结构、社区意识和集体行为这些社会层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研究延续了帕克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有机体”的观点。
而更容易使人视而不见的其实是费孝通对于人文区位学思想的吸收和运用,这一点被后来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光芒给遮盖了。不过,即便是在他早期的研究当中,费孝通也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市镇问题的重要性,在《江村经济》中,就有一节和杨庆堃研究的对话,专门讨论了贸易区域和集镇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的《乡土重建》中,他以更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并在概念上定义了区别于乡村和都市的“市镇”。
可惜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费孝通关于市镇的研究没有继续开展,甚至在一段时间中,由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市镇本身就停滞发展或趋向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开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调查的时候,市镇研究才重新获得了关注。其实,在费孝通写作《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还很犹豫要不要用“集镇”来统称他所调研的这些“小城镇”,只不过后来约定俗成的叫法,使得人们忽略了这两者在历史上的因缘。从历史上中国看,城镇化的发展由来已久,而自明清以来其特点就是市镇的数目在不断增大。这种发展模式显然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大城市扩张为特点的形态有着巨大的区别,这种貌似“反常”的现象也引起了学界诸多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市镇就是中国城镇化历史的原型。因此,不论是从历史溯源、理论探索还是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都值得对市镇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当下城镇化进程的接续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有必要理清芝加哥学派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影响了。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