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娘蒸的馍馍。在我们村,我娘做的曲特别好。曲好,引子就好,这样做出来的馍馍就特别好吃。
十几岁,我就会揉剂子。揉啊揉,手掌根红了,面团柔滑了,于是就团一团,团成馍馍。把馍馍放炕头上,用被子盖了。借着炕头的温度,馍馍在棉絮的捂盖下慢慢醒发。到时间了,掀开被子,拿手指头轻轻一按,指肚刚一离开,“腾——”按下的手印复原了。
“醒了,醒好了,开蒸!”这个时候,锅里的水将开未开,泛着蟹沫。
柴火正旺,热气蒸腾。“闻闻,闻到馍馍味儿了吗?”母亲会问。“闻到了,甜味儿!”我说。
掀开锅,白生生、煊腾腾的馒头出现在眼前。空口吃馒头,我只能吃好几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何况家里有好几个能吃饭的小伙子呢!
有些味道,能记一辈子。
后来,吃学校食堂。那馒头黑乎乎黏歪歪,总有股脚吧丫子味道。再后来,买馒头坊的馒头。那馒头,太煊腾了,攥一把,瘪了;咬一口,味道是啥呢?形容不出,到处都是一个味儿。
于是,老是想,小时候娘蒸的馍馍咋就那么甜呢?什么时候能寻到那种滋味呢?一想,舌底生津,记忆就会泛起来,于是咽口唾沫,轻叹一声: 咋就没有好吃的馒头呢?
不成想,这次在滨州“粟说粮源店”,我又寻到了小时候吃的那种馍馍,尝到了“娘手揉出来的味道”。
是啥馍馍呢?就是“粟说粮源”推出的功夫馒头。既然是功夫馒头,肯定是下了功夫的,否则怎能叫功夫馒头呢?
时间就是心思啊!
“我们用的是’曲’,用’曲’制成’引子’,再经米酒发酵,经过制酵、和面、纯手工揉制、醒发、戗面、蒸制等工序,以三醒三发三戗面、三十六次团揉还原谷物原香。”赵建忠说,“经过这么多环节,蒸出的馒头肯定别有风味。”
说得好像繁琐,可对于像我这样会蒸馒头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一点都不难想象。“引酵子”醒了,手一搭,噗噗——加白面,使劲揉;揉好了,笼布盖上,醒发一下;面醒了,软了,再加面,继续揉,揉好再醒;如是者三,当馒头进锅的时候,已经被揉得“熟熟”的了。
“这样做馒头,一天能做多少呢?”我问。
“一个壮年劳力一天最多加工120-150左右,普通人一天也就 100个馒头左右。”赵建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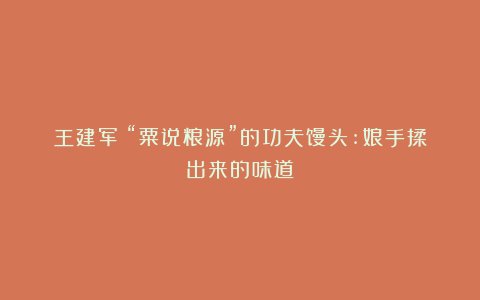
“那利润并不大。”我说。
“就是不大,即使都算成钱,也不过几百块钱!它带来的经济价值并不是多高,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做,就想把这个好的传统工艺保持下去,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人们现在吃的不仅仅是一块馒头,而是一种文化。”赵建中说,“你看看这些老曲,还有我们做的引子。”
我拿起一块老曲,轻轻嗅着。一丝清幽的酸甜味钻进鼻腔,又似乎沁入心田,我的情感破防了。今天,我一定尝尝这功夫馒头。
小蒸笼掀开的刹那,四个馒头静静摆在那里: 样子敦实饱满,表皮光滑如脂,细看竟透着淡淡乳黄,那是小麦最本真的色泽。我掰开一个,内部层层叠叠的纹理如云絮舒展,热气携着麦香、曲香、酒香扑面而来。咬下的第一口,眼眶突然发热。那是一种有韧劲的柔软,需要牙齿稍稍用力才能撕开,随即甘甜便在舌尖漾开。越嚼越甜,正是记忆里粮食最淳朴的甜法。没有工业香精的单薄,而是多种天然香气交织成的圆润厚味。
小时候的味道出现了,竟还是那味儿!原来,这味道从未远离,它只是被岁月悄悄收藏,等待某个契机再次苏醒。
忽然懂得:娘蒸的馍馍之所以甜,是因为揉进了日光月光,揉进了田埂上的麦浪,揉进了一代代人对手中粮食的敬畏。这种甜,本是天地人共同酿造的蜜。
我们的先祖,撷取大自然之物,并令其吸收天地之精华,制成了这神奇的老曲,这才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她像一条看不见的脐带,连接着大地的脉搏与心跳。
离开时,妻子买了两袋馒头,说等女儿中秋回来让她尝尝。呵——娘心就是细啊!回头望,“粟说粮源”那并不起眼的招牌隐约出现,像一枚温暖的酵母,正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悄悄发酵着某种即将失传的温度。
粟说粮源的功夫馒头
能剥皮的馒头
层层如云絮
层层到底
苘麻叶包裹的老曲
纯天然
古法
淡黄色的引子
舌尖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