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峰 井中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25年09月18日 20:28 北京
摘要:从铜器铭文、墓葬分布、葬俗特征等方面观察,梁带村墓地和刘家洼墓地应是包含国君墓在内的芮国墓地。根据对两处墓地中铜器墓年代的判断,梁带村、刘家洼遗址应是春秋时期芮国前后相继的两处都城所在。芮国都城在春秋早期晚段的变迁,可能与“芮伯万出居”事件有关。结合对虞国地望的认识,商末周初的芮国应在关中地区西北部。商末的争讼之芮与西周的公卿之芮似乎有别,西周初年芮国可能被重新分封。芮国在两周之际迁徙到关中地区东部,或与戎狄的侵扰有关。
史籍中的芮国首见于商末的虞芮之争,西周年间有劝谏周厉王的芮良夫,春秋时期被秦所灭[1]。但芮国的地望在早期文献中鲜有记载,后世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近年来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澄城刘家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芮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基于此,学界关于芮国多有探讨,但对遗址性质、年代的认识尚不一致。以下拟从考古发现入手,尝试探索芮国地望的变迁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墓地国别的确认
首先说梁带村墓地,其位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西北部,2005~2009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根据工作需要,发掘者将墓地划分为北、西、南三个区。其中南区大型墓M19、M26、M27出土的有铭青铜器较多,显示作器者为“芮公”“芮太子”“芮太子白”以及“仲姜”。“芮公”“芮太子”和“芮太子白”无疑是芮国国君和太子,发掘者推测“仲姜”是《左传》所载的春秋早期芮国的一位国君夫人——“芮姜”。根据这些有铭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发掘者提出南区大型墓为芮国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梁带村墓地为芮国墓地[2]。该意见为多数学者所赞同,但也有学者在同意梁带村墓地南区为芮国墓地的同时,对北区墓葬的国别提出不同认识。譬如,张长寿依据铜器铭文和葬俗认为北区M502是毕伯墓[3],谢伟峰则推测北区墓葬群属于戎化的毕公后裔[4]。
从墓地的整体布局和葬俗的相似性来看,我们认为梁带村北区和南区墓葬关系密切。其一,南北墓区紧邻,且均有带墓道的大型墓,这些大型墓很可能都属国君级别,它们的年代也很接近(详下),同一地点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不同国别的国君埋葬区的现象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考古发现中尚未见到,可能性极小。其二,葬俗方面,两区的墓向均朝向东北,随葬陶器均为火候极低的素烧明器,大中型墓基本都有成组的铜翣和棺顶串饰,中小型墓随葬品普遍较少,其中有些葬俗虽不为梁带村墓地所独有,但在当时中原也绝非普遍流行,两区葬俗的相似性无疑显示了墓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也赞同发掘者的意见,认为梁带村墓地南、北区共同组成了一处延续使用的芮国墓地。
至于北区M502,从其带有墓道的墓葬形制、较大的墓室面积等情况看,墓葬等级与南区大型墓接近。但其随葬的实用青铜礼器仅1件“毕伯鼎”,其余青铜礼器皆为专用明器,数量也不多,似与墓葬等级不符。这样看来M502的随葬器物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个中缘由尚难确知,但不宜仅据1件“毕伯鼎”就推定墓主为毕伯。
再看刘家洼墓地,其位于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西,2017年开始发掘,目前资料报道还比较少。墓地内发现的2座“中”字形大墓,也应属于国君级别。铭文方面,墓地出土了芮公、芮定公、芮太子白等铭文铜器,目前所有铭文均与“芮”有关,未发现其他国别的文字材料。葬俗方面,大墓集中埋葬丰富的青铜、金、玉等质地的礼乐器、兵器等随葬品,中型墓随葬品普遍较少,小型墓几乎不见随葬品,各类墓葬中陶器均罕见,这些特征都与梁带村墓地类似。发掘者认为,包括城址和墓地在内的刘家洼遗址应是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性遗址[5]。值得注意的是,刘家洼墓地包括2座大型墓在内的许多墓葬都是东北向,大中型墓多有成组的铜翣和棺顶串饰,这些特点也与梁带村墓地一致。刘家洼东I区M1放置于二层台上的木俑,形制与梁带村北区M502二层台出土的木俑非常相似,也表现了两处墓地葬俗的相似性。
总之,铜器铭文、墓葬分布、葬俗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显示梁带村墓地与刘家洼墓地应是包含国君、普通贵族和平民在内的芮国墓地。
二、墓葬年代的推断
梁带村墓地已发掘的墓葬,发掘者将其按年代早晚划分为两期三段,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前段、春秋早期后段。由于其中绝大多数中小型墓随葬品较少,特别是缺少时代特征变化明显的陶器和青铜容器,墓葬年代主要是根据墓地布局推定的,证据较为薄弱。刘家洼墓地已发掘的墓葬,发掘者推断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早段。比较而言,两处墓地的铜器墓随葬青铜容器较多,综合考察这些器物的年代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墓葬年代。而且,只有墓地内出现国君墓、国君夫人墓或太子墓等高等级墓葬,才能比较肯定地说国都在该墓地附近。两处墓地的铜器墓等级都比较高,更能反映墓地性质,因此以下着重讨论两地铜器墓的年代。
对两处遗址中随葬的青铜容器进行类型学分析,鼎、簋、鬲、甗、方壶、匜等实用器存在比较明显的式别变化(图一),另有盆、簠、盘、盉等实用器以及模型明器、弄器等。
图一 梁带村、刘家洼墓地铜器分组图
鼎 均为三足圆鼎。根据耳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立耳鼎。根据腹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二个亚型。
Aa型:立耳弧腹鼎。根据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
I式:足接于器底,足较长,粗细较均匀。
II式:足接于器底,足较长,上下两端明显膨大。
III式:足接于器腹下部,足较长,上下两端明显膨大。
IV式:足接于器腹下部,足较粗矮,上下两端明显膨大。
Ab型:立耳垂腹鼎,仅1件。
B型:附耳鼎,均弧腹。根据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I式:器腹较深,圜底,足较长。
II式:器腹较浅,圜底近平,足较长。
III式:器腹较深,圜底近平,足较粗矮,足底微出台。
簋 根据口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敛口。根据腹部、耳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五式。
I式:腹部垂鼓,器耳宽大。
II式:腹部垂鼓,器耳较宽大。
III式:腹部垂鼓,器耳较细小。
IV式:腹部圆鼓,器耳较细小。
V式:腹部扁鼓,器耳较细小。
B型:敞口。根据腹部、耳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I式:腹部垂鼓,器耳宽大。
II式:腹部垂瘪,器耳较小。
鬲 均为蹄形足跟的扉棱鬲。根据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I式:器形较宽矮,弧裆,袋足较深。
II式:器形较瘦高,弧裆,袋足较深。
III式:器形较瘦高,弧裆近平,袋足较浅。
甗 根据器形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方体甗。根据鬲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I式:鬲部腹、袋足较深,足跟较细。
II式:鬲部腹、袋足较浅,足跟较细。
III式:鬲部腹、袋足较浅,足跟较粗。
B型:圆体甗。有连体甗、分体甗各1件。
方壶 根据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I式:器形较瘦高,盖顶捉手宽度不超过盖宽。
II式:器形较宽矮,盖顶捉手宽度超过盖宽。
匜 根据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I式:由流口至尾端的口沿呈斜弧形,转折不甚明显。
II式:流部口沿弧曲,器身口沿平直,转折明显。
依据型式演变及组合关系,可将梁带村、刘家洼遗址随葬的铜容器划分为五组,进而将随葬以上型式铜容器的墓葬归为五组(表一)。
表一 梁带村、刘家洼遗址铜器墓分组与铜容器型式统计表
铜容器的纹饰方面,各组均以窃曲纹、环带纹、垂鳞纹、重环纹、卷身龙纹为主,变化不大,但花纹由立体向扁平逐渐演变。第1组的纹饰呈浅浮雕式凸起,多数还有地纹;第2组的纹饰也比较有凹凸感,但多数无地纹;第3、4组的纹饰较为浅平,无地纹;第5组的纹饰不但较为浅平,无地纹,而且卷身龙纹分解,有向蟠虺纹演变的趋势。根据器形、纹饰的连续变化看,它们应是早晚相继的五个年代组,并以与西周晚期铜器面貌接近的第1组最早。
具体来看,第1组的M560和M586、第2组中的M300和M502出土铜容器较多,均位于梁带村墓地北区,发掘者将它们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而且认为其中的M502、M586可能属于西周晚期比较早的阶段[6]。陈小三则认为它们的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早阶段[7]。与山西曲沃北赵、羊舌晋侯墓地随葬的青铜器组比较,M300随葬的B型I式鼎(M300:33)与北赵M93:37相似,A型II式簋(M300:31)与北赵M93:33相似,盘(M300:34)与北赵M93:44相似,I式匜(M300:35)与羊舌M5出土的匜相似;M502随葬的Aa型Ⅱ式鼎(M502:96)与羊舌M5出土的鼎相似[8](图二)。一般认为,北赵M93墓主为晋文侯(卒于公元前746年),羊舌M5从属的M1墓主为晋昭侯(卒于公元前739年)或孝侯(卒于公元前724年)[9]。由此推测,将梁带村M300、M502的年代定在春秋早期早段确实比较合适。而且,梁带村M502随葬的鼎、簋、爵、觯、方彝、盘、盉等模型明器,在春秋早期偏早[10]的三门峡上村岭M2001、M2012等墓的随葬品中都能找到形制相似者,梁带村M18随葬的虢季鼎(M18:19)也见于上村岭M2001[11],年代应基本相同。综此,芮国铜器墓第2组的年代均在春秋早期早段。
图二 芮国铜器墓第2组与晋侯墓地铜器比较
第1组的M560、M586随葬的铜容器,多能在周原遗址[12]等处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铜器中找到形制相似者。M560随葬的I式鬲(M560:41)与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北赵M91:68[13]相似,B型甗(M560:44)与周原凤雏1978年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夔纹甗[14]相似;M586随葬的A型I式簋(M586:39+40)与周原召陈1960年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散车父簋[15]相似,B型I式簋(M586:38)与周原齐家村八号窖藏出土的西周中期方座簋器身[16]相似,簋盖(M586:37)与周原齐家村1960年窖藏出土的西周中期友父簋盖[17]相似,Aa型I式鼎(M586:36)与周原召陈1960年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散伯车父鼎[18]等也较为相似。如果单就这些器物看,梁带村M560、M586的年代似乎在西周晚期或稍早。
不过,梁带村M560、M586的其它一些随葬品,年代可能要更晚。M560随葬的尊(M560:43)器形较小,为复古式的模型明器,此类器物在上村岭墓地等中原地区春秋早期偏早的大型铜器墓中比较流行;器身中段所饰较为浅平的卷身龙纹,在上村岭墓地铜簠(M2017:6)等春秋早期偏早的铜器上也比较常见。M586随葬的辖、軎、銮铃、衔、镳、节约、饰件、马胄等,与上村岭墓地等春秋早期墓葬出土的车马器也很相似[19](图三)。因此,梁带村M560、M586的年代也可能晚至春秋时期。2座墓随葬的铜容器中,未见作器者相同或形制相同的成组礼器,可能是用家族中流传的器物临时拼凑的。稳妥起见,将芮国铜器墓第1组的年代定为两周之际。
图三 芮国铜器墓第1组铜器比较
第5组中,如发掘者所论,刘家洼M6随葬的附耳鼎足下方“渐显方台接地”,显示了春秋中期的时代特征,年代应在春秋早中期之际[20]。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秦灭梁、芮”[21],春秋中期早段之时芮国被秦所灭,这一时间应为芮国墓地铜器墓的年代下限,第5组的年代也应不晚于此。综合以上认识,将芮国铜器墓各组年代推定如下:
第1组:两周之际;
第2组:春秋早期早段;
第3组:春秋早期中段;
第4组:春秋早期晚段;
第5组:春秋早中期之际。
已发表的资料中,芮国墓地出土完整陶容器的墓葬仅梁带村M02、M502、M526三座,均位于梁带村墓地北区。其中的M502属于前述铜器墓第2组,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M02随葬陶鬲、罐各1件,M526随葬陶鬲1件,2件陶鬲均为红胶泥质器,折沿近平,鼓肩明显,在闻喜上郭村76M6[22]、礼县大堡子山IM32[23]等春秋前期墓中,多见有器形近似者,M02随葬的陶罐(M02:5)与大堡子山IM32:25也很相似(图四)。因此,M02、M526的年代应当也在春秋早期前后。
图四 梁带村墓地出土陶容器比较
三、芮国晚期地望及其变迁
根据以上分析,梁带村墓地埋葬了包括国君在内的芮国高等级贵族,年代从两周之际持续至春秋早期晚段。从西周至春秋时期封国的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的国君墓大都位于国都附近,例如北赵晋侯墓地位于天马—曲村晋都遗址中部[24],燕侯墓位于琉璃河燕都遗址东侧[25],上村岭虢国墓地位于李家窑虢都遗址以北2千米[26],李家楼郑公墓位于郑韩故城遗址内西南部[27],齐侯墓位于临淄齐故城内东北部[28]。因此基本可以肯定,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晚段的芮国国都应在梁带村附近。在梁带村墓地东侧的化石村至梁带村一带,曾采集到周代的陶片、瓦片等遗物,断崖上往往暴露有灰坑、文化层等迹象,其中可能就包含与墓地相关的居址性遗存[29]。
刘家洼遗址也发现有包括国君墓在内的芮国墓葬,年代从春秋早期晚段延续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而且遗址内还发现有相应的城址,如发掘者所言,其也应是一处芮国都城遗址[30]。刘家洼铜器墓与梁带村偏晚阶段的铜器墓基本同时或稍晚,表明梁带村、刘家洼遗址应是前后相继的两处芮国都城所在。也就是说,芮国都城很可能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从韩城梁带村附近迁到了澄城刘家洼一带。如此,经由考古发现,两周之际始都于韩城梁带村附近,经春秋早期晚段迁至澄城刘家洼,直到春秋中期早段亡国为止,这段时间的芮国地望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为方便表述,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芮国晚期,而将此前商末到西周时期称为芮国早期。
梁带村墓地发现以前,学界一般认为芮国地望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汉书·地理志》记载左冯翊临晋县为“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芮乡,故芮国。莽曰监晋”[31],认为汉代的临晋县即秦代的大荔县,临晋县的芮乡就是芮国故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南芮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国”[32],具体指出芮国故址位于大荔县朝邑镇南三十里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信从此说[33]。《括地志》中还提及“北芮城”也是芮国故址,但没有说明其具体地望。梁带村墓地发现后,因恰位于大荔以北,有学者即将其看作“北芮城”[34]。不过,新发现的刘家洼遗址也在大荔之北,且有城址,指认为“北芮城”亦无不可。如此看来,目前“南芮乡”尚未明确发现芮国遗物,“北芮城”究竟是指梁带村遗址还是刘家洼遗址也不能确定,有关芮国地望的考古发现与汉晋时期的著述还不能很好地对应。
由于文献中并无芮国都于梁带村附近的明确记载,有学者从文献出发,将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形成与“芮伯万出居”事件联系起来,认为梁带村附近是芮伯万的新居地[35]或芮伯万返国后芮桓公等被驱逐到的地方[36]。从时间上看,如果承认梁带村墓地各区同属芮国墓地,那么梁带村芮国贵族墓在两周之际就已出现,即使仅就西区和南区墓看,也可早到春秋早期早段。而“芮伯万出居”这一事件发生在春秋早期中晚段之交(鲁桓公三年至十年,即公元前709~前702年),经此事件的贵族去世应当还要再晚一些,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早期晚段,这与梁带村墓地形成的时间并不相符。
“芮伯万出居”这一芮国公室的动荡事件,倒是与芮国晚期迁都至刘家洼遗址的时间点相近,或许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有关“芮伯万出居”之事,《左传》[37]和《古本竹书纪年》[38]均有记载,但稍有差异(表二)。
表二 “芮伯万出居”之事的文献对比
两种文献的矛盾之处主要在于公元前708年参与王师围魏者不同,是秦师还是虢师?根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虢公任职于周王室,多次受王命出兵征伐或随同王师作战。如《左传·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记载“王命虢公伐曲沃”[39]。《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记载“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40]。《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小子侯四年(公元前706年)“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41]。反观这一时期的秦国史事,不见其参与王室活动的记载。因此,公元前708年参与王师围魏的很可能是虢师而非秦师。《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武公元年(公元前715年)“芮人乘京”[42],王师抓捕芮伯万的行动可能与先前芮国侵犯京地有关,其性质类似打压晋国曲沃小宗,都是希望维护以分封制、宗法制为具体内容的周礼。此外,《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戎人逆芮伯万于郊”,清代学者雷学淇认为这里的“戎人”指秦人,是东方国家对秦的贬称[43],其说可从。这样看《左传》中“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一条,可能是将王师、虢师围魏并执芮伯万与秦人逆芮伯万两件事混记在一起的结果。
综上分析,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似应如下:公元前709年,芮伯万被其母芮姜驱逐,流亡到魏国。公元前708年秋,秦国发兵侵芮失败。公元前708年冬~前707年,为惩戒此前芮国侵犯京地的行为,王室和虢公派兵把芮伯万从接纳他的魏国带到了更东边的某个地方。一段时间后,秦国将流亡东方的芮伯万迎入秦国。公元前703年,现任芮伯参与了虢公领导的讨伐曲沃的行动。公元前702年,秦人将芮伯万送回了芮国,芮伯万可能重新掌国。
由公元前703年新任芮伯参与虢公领导的征伐行动可见,其与芮伯万不同,与王室重臣虢公的关系良好。整个事件中的各方似可划分为两个利益阵营,一边是被逐的芮伯万和在芮伯万被逐后侵芮的秦国,另一边是不满芮伯万的王室、虢公以及芮伯万被逐后的芮国新君。而事件的发展似乎与秦国侵芮策略的转变有关。起初秦国本想趁芮国公室动荡直接发兵侵占芮国,但以失败告终,也得罪了新任芮君。因此秦国改变策略,扶植流亡的芮伯万作为代理人,间接掌控芮国。芮伯万回国后,有关芮国的记录均是其朝觐秦国[44],且最终为秦所灭。可见经由“芮伯万出居”事件,秦国逐渐增强了对芮国的影响和控制,其政治意图得以实现。从考古发现看,相较于梁带村,刘家洼遗址位置偏西。这一国都位置的变化,似乎有意靠近支持芮伯万的秦国,试图躲避与他交恶的虢国等东方诸侯。
刘家洼遗址东I区墓地内,除中字形大墓M1、M2外,以M3规模最大。M3出土了芮公有铭铜鼎,又不出青铜兵器,墓主很可能是芮公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M3墓室四壁有9个壁龛,每个壁龛内均有屈肢葬殉人[45],这种葬俗在陇西的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毛家坪和关中西部的孙家南头、八旗屯等秦文化遗址的铜器墓中多有见到,应是秦人在西戎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葬俗[46],同样采用这种葬俗的刘家洼M3的墓主人很可能来自秦国。
刘家洼东I区墓地M49随葬1件铜柄铁剑(M49:185),此类剑因柄部装饰华丽通常被称为花格剑,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中剑格底部平直的类型多出自东周秦墓,具有一定的地域风格[47]。刘家洼这把剑和陇县边家庄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形制基本一致(图五),很可能来源于秦国。
图五 刘家洼、边家庄遗址出土花格剑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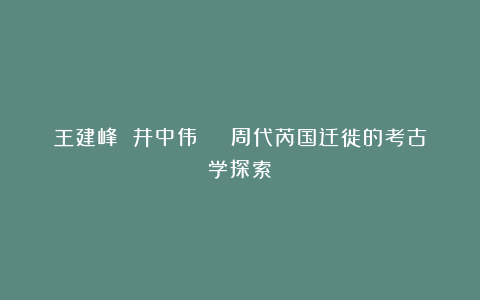
芮国晚期迁都于刘家洼遗址,可能正是秦、芮两国政治利益结合的产物。芮公迎娶秦国女子为夫人,芮国贵族使用来自秦国的兵器,应当都与这一背景有关。依附于秦国,虽然有利于芮伯依靠秦国的力量保障自身安全,但也方便了秦国对芮国的控制,使得芮国最终被秦国吞并。
四、芮国早期史事与地望探寻
史籍中芮国首见于商末的“虞芮争讼”事件,《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慙,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48]据此似可作如下推测:其一,虞、芮相邻,才会发生争执。其二,虞、芮并非周人[49],且与周相比文明程度较低。
正是考虑到虞、芮相邻,不少学者结合对虞国地望的考证,认为早期芮国的活动地大致在今宝鸡西北的汧河流域附近[50],似应比较合理。首先,汧河流域发现多批西周夨国有铭铜器[51],这一区域应是西周时期的夨国所在。李学勤指出金文中的“夨”是“虞”的本字[52],夨国很可能就是文献中的虞国。其次,夨国铜器铭文中有“夨王”的称谓,夨国应非周人族群[53],与文献“虞芮争讼”中虞国的形象相符。再次,商末的汧河流域为属于姜戎族群的刘家文化的分布区[54],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不同于周人,同样符合文献中虞国的形象。而且,相较于晋南地区等处,汧河流域靠近周原,在文王初兴之时虞、芮由此入周更合情理。因此,汧河流域很可能是早期虞国所在,而早期芮国应在其附近。《汉书·地理志》即记载右扶风汧县“芮水出西北,东入泾”[55],宝鸡地区西北部有“芮水”,芮国之名可能与之相关。
有学者结合汉代以后的记述,进一步指认芮水即现在的汭河或潶河,且两条河流经的甘肃华亭、崇信县与汧河上游的陇县相邻,因此认为早期芮国即在两县域内[56],可备一说。但将崇信于家湾墓地推定为芮国早期遗存,就已有材料看,显然不足为据。首先,于家湾墓地与梁带村、刘家洼两处芮国晚期墓地在葬俗方面存在差别,其墓向基本为西北向而非东北向,随葬陶器以实用器为主而非泥制明器[57]。其次,于家湾墓地大墓等级低于同时期诸侯国君级别的墓葬[58],与芮伯身份不符。另外,也无铭文将于家湾墓地与芮国直接联系起来。早期芮国都城遗址,似需另行探寻。
西周时期有关芮国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其作为王室公卿出现的,职位较高。如《尚书·旅巢命·序》记载武王之时“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59]。《尚书·顾命》记载成王临崩之时“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60]。《尚书·康王之诰》记载康王登基之时“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61]。《诗·桑柔·序》记载厉王之时“《桑柔》,芮伯刺厉王也”[62]。
考察西周有关芮国的铜器铭文,也可发现芮君地位较高、芮国实力较强。其一,由西周前期《芮公簋》铭文“芮公为祈宫宝簋”[63]可见,芮君以“公”为生称,应是王室重臣[64]。其二,西周早期《霸簋》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记载芮公对霸伯进行赏赐[65],芮公地位高于霸伯这样的非姬姓封君。其三,芮国青铜器不少出土地点明确,如河南洛阳市出土西周早期芮伯卣1件[66],山东黄县庄头村出土西周早期芮公叔簋2件[67],山西绛县横北村倗伯墓地M2158出土西周中期芮伯器5件[68],陕西武功县任北村出土西周晚期芮叔簋3件[69]。芮国有铭铜器见于多地,表明芮国与远近封国存在广泛联系,也应是其地位和实力的体现。
传世文献和出土铭文都显示,西周时期先后有数代芮君在王室任职,等级地位较高,芮国实力也应该比较强。比较起来,世代公卿的西周之芮与文明程度较低的商末争讼之芮似乎有别。陈槃认为:“芮本旧国,西伯之世’虞、芮质厥成’是也。武、成时已有同姓为芮伯,殆武王灭之而以封同姓矣。”[70]若此推测不误,则公卿之芮与争讼之芮的国君族系不同,很可能是西周初年重新分封的,属于芮公家族在王畿的采邑[71],其以芮为名,封地应当仍在原芮地即宝鸡地区西北部附近。梁带村、刘家洼遗址的大型墓中出土较多芮公有铭铜器,两处芮都遗址应当是西周时期公卿之芮的延续。
西周早期的芮国在关中西北部,其在两周之际迁徙到关中东部,可能与戎狄的侵扰有关。根据文献和铭文记载,西周晚期戎狄频繁内侵,“其侵暴中国,亦以厉宣之间为最甚也”[72]。在此背景下,关中西部的郑、西虢等封国由于地处与西北异族接触的前沿地带,纷纷开始东迁避祸[73],芮国可能也是其中之一,逐步向东迁徙。不过,目前早期芮都和芮伯墓地尚无明确发现,文献中对于芮国地望又有大荔“南芮乡”等不同说法,因此以上有关芮国早期地望的认识还有待更多材料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