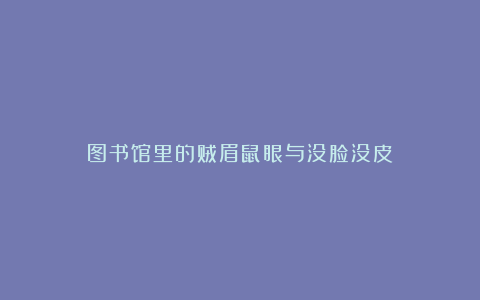|
图书馆新书上架前,需要做编目贴码等工作。新书堆放在文科二书库,那里一时成了书山书海。馆员们在山上海里劳作,我也是每天一完成手头工作就跑过去。
这几天,我就像一个惦记隔壁邻居家金银细软的贼,不去就抓心挠肝,睡不着,吃不下。
因为只去了一次,我就在其中发现了宝藏——无数本我想第一时间就能捧在手里翻开的书。你得理解差生心虚腹空,不得不求知若渴。
书海里,有对我而言宝藏中的宝藏,即全套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集和雷平阳的《云南记》。
说来对米兰·昆德拉的认识,还是理科生巫森给我完成的启蒙。1990年代,他在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一本《生活在别处》,令学中文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不免感到羞愧。从此,我迷恋上了米兰·昆德拉,也在他的小说里读懂一部分人生。
我见过两次雷平阳,坚持认为他的《亲人》和《小学校》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作。这本《云南记》里,诗中有关云南的繁复丰赡的意象令我着迷。他虽然是个诗人,但散文的语言独一无二,因此序《独有深山客,时来辨药名》写得尤为精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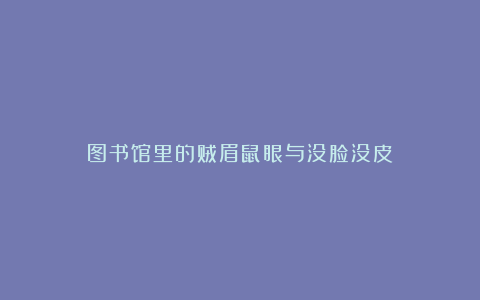
另有一本米兰·昆德拉的《不解之词》,使我夜不能寐。因为还没有上架不能借出,我就带了笔记本去,边看边摘抄。如同一个饕餮之徒,更像饿虎扑食。
而一进入米兰·昆德拉的语境,我也就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在这里,天空高远,大地辽阔,万物前来又远去……在这里,每一个语句都长驱直入,直奔我的命门。我成了心甘情愿的俘虏,被钉牢在书页间。除此之外,我简直失聪失语,听不到任何声音,说不出任何话语。
图书经销公司编目人员小零在电脑前工作,又不时站起来,指导明明、艳艳、慧慧的贴码工作。
我在翻找米兰· 昆德拉时,完全不知道小零如临大敌。因为所有的新书,都是按一定顺序摆放的,一旦弄乱,后果不堪设想。
我去第一次的时候,小零就非常紧张地跟着我走来走去,然后叮嘱我一定一定不要弄乱。
等到我第四次去,小零仍然不放心,走过来再三再四叮嘱,千万千万不要弄乱书的顺序。
我这时才后知后觉理解了她的紧张情绪。她应当早已发现了我的贼眉鼠眼,领教了我的没脸没皮。
正常点儿的人,被规劝一次早就远远躲开了,而我还一次再一次地闯入,眼睛放着贼光,赶都赶不走,实在是因为惦记这些宝藏,想要先睹为快。
小零大约没见过我这种不学无术专门看闲书的捣乱者,面对我的贼眉鼠眼和没脸没皮,有些不知所措。
其实,小零不知道的是,在翻看新书时,我都小心翼翼,不仅确保不弄脏新书,不弄乱书的顺序,而且但凡挪动一本,最后都要摆摆齐——强迫症都这样。
上海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图书馆,下班前馆员要拍书,就是把书脊拍拍齐。我对这项工作有近乎病态的喜欢,一到书架前,就喜欢把放倒的书摆正,离开前一定拍书。但是,此刻在极其敬业的小零眼中,我就是一个新书编目王国秩序的破坏者。
贼不走空。除了拍照,我还记了好几页读书笔记。离开时,觉得自己里里外外,哪哪都装满了。对米兰·昆德拉这本书《不解之词》的观感,容当后叙,不然今天就跑太远了。
我还和诗人G互通有无,向他炫耀我们馆又进了哪些诗集,这饱足的食粮。他则向我显摆他有哪些诗集,比如《云南记》他早就有了。我知道,他家的藏书,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
“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而读书声为最。”我读诗给诗人制造一些没有杂质的声音。因书海有太多美的诗句,可以信手拈来,几乎不用打捞。
是的,最后赢的人一定是我。诗人固然不停买书读书,但他到底是一个人。而因为得天独厚的幸运,我一个人的身后,是一支队伍,一座巨大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