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去延安,了解好些湖南籍革命先辈的事迹,其中包括罗荣桓。后来得知他是唯一上过大学的元帅,这大概也是他成为政工典范的原因之一。而他自己,听说对授予元帅头衔颇感不安,尽管一直辗转于战火,连给子女取名也是诸如南下、东进、北屯、北捷之类。
不论如今的红色旅游存在多少形式主义,仅仅穿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信仰,在变幻莫测的风浪面前,都是不变的、穿透时代的力量;
也不论如今的鸡汤多么被人所诟病,很多革命先辈的自律和无私奉献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一个人,有谁敢说不曾被一种东西滋养着,鼓舞着,哪怕铁骨铮铮的汉子?
所以,参观罗荣桓故居,使本次山野徒步拥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罗荣桓是个老实人”,“罗荣桓是个厚道人”,“罗荣桓家风严谨”是新中国第一、二、三代领导人给予他的评价。这个汲汲营营的时代,老实与厚道应该是被嘲笑的代名词,如果真是这样,“富不过三代”就是自取灭亡。
先哲有云,“反者道之动”,每件事都藏着“祸福相依”的道理,飞黄腾达之时能谨记,或许能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罗荣桓的女儿罗玉英认为父亲在北京做了大官,发了大财,自己当然有了依靠,这是作为子女的人之常情。罗荣桓却回信“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终身的职业,物质方面除了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除了帮助**入校读书外,明确告诉女儿不能对自己有其它任何依靠。
中国人都知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1950年去北京小住时支使警卫和通信员干这干那,罗荣桓便动员二哥回湖南接受群众教育。
看到这些记录,我一直想:法治的执行者最终是人,如果没有德治的配合,如何能保证依法执法呢?就算提高违法成本,不还是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难道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惩治违法者?当然不是。
可是德治的约束力又在哪?如果除了底线道德,社会还需要崇高道德,那么又如何把握崇高道德的分寸以避免生产伪君子?或许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My Walking
鹤岭不高,大家奔着它的山脊而来,而我,还喜欢它的名字。
沿着小道,眨眼功夫,山脚的彩虹公路成了眼底弯曲的绸带,顺着山脉安静地朝两头延伸。
抬眼远眺,隐隐绰绰的灰白散落在对面的山坳,那是星星落落的山里人家。
登上山脊,山的那一边传来缓缓的吟唱,听不清唱词,唱调只有绵长的哀伤在猎猎的秋风中摇曳。
朝山脚望去,阡陌纵横,楼房聚集,是很有规模的小山村。声音是山村的,为送别落叶归根的山里老人而起。
小时候我的家,拥有十几亩水稻田,农忙时节插不完的秧苗割不完的稻禾,那时候唱“妈妈的吻”,很羡慕作者长在“遥远的小山村”,在旱地干活比在水田舒服多了。长大了又一直想为什么没有一首歌唱“遥远的稻田村”的歌呢?
山脊上几乎都是石头,有的巨大到一截山岭就是一块石头,有的嶙峋如刀削,有的斜着身躯要冲上云霄的样子,有的横亘在前不容置疑,有的见缝插针把唯一可以通行的缝隙挡住,我们要么绕道,要么颇费一番功夫爬过去,有的干脆完全堵住去路,只在旁边留一条一次只能踩一只脚的窄道,虽然不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但要落下去很可能不是轻伤,好在石头斜仰,我们也可以靠在石面上放心地摸爬过去。
这里的岩石都是无数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黏在一起形成,表面非常粗糙。它们越是东倒西歪,越是增加我们攀爬的乐趣,甚至用不着手脚并用,踩在上面稳妥得很。
看着斑驳的石头表面,我疑心鹤岭几千甚至上万年前还是一片河床,由于地下深处炽热的岩浆向上奔突,河床被高高隆起,河床里的鹅卵石与喷薄而出的岩浆一起,冷凝成坚硬的物质,再阅尽沧桑,饱经风雨,成了这些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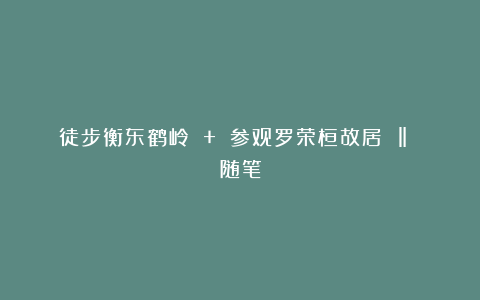
走在鹤岭山脊,我们似乎与浩远的时间有了连接。有些石头趴在山坡的灌木丛,在阴天沉沉的暮霭里,如同一只只古老的巨兽,等待一个年轻的未来。
AUTUMN
石头之间,是风雪雨剥蚀下来的砂土,砂土里生出许多纤细的野草,它有好听的名字——粉黛乱子草。乱子草年轻的时候,想必妩媚了整条山脊,现在的一身枯黄,依然在秋风里婀娜绰约,与石头一起,成就了一场雄壮而婉丽的秋色。
按照巴门尼德的逻辑,秋天的乱子草不是衰老,而是青春活力的暂时隐藏。因为野草经历一年四季,我们目睹它们从萌芽到枯萎,感叹生命的短暂与美丽。
而石头呢?因其经历久远,我们便以为是永恒。
实际上,海会枯石会烂,石头的存在也不是永恒的。
让鹤岭山脊的秋色风情万种的,除了乱子草,换了行装的马尾松,一身磅礴的铁锈色,大有老骥伏枥的豪迈;远观,在淡灰色天空里,马尾松又变得娇艳动人。
落叶的松树似乎都是这种颜色,有一段山脊两旁的树枝在路的上空交叉,天光从枝间洒落,地面是厚厚的针状松叶,我们如同在童话中行走。小王子和狐狸也是在这样的色彩里促膝相谈的。
还有几棵矮小的盐麸木,我似乎看到它的叶子正在由绿到黄再到红,有的叶子三种颜色并存却纯粹不染纤尘:绿色渗透到明艳的黄里,含蓄内敛,黄又在红色里流动,让红色也委婉起来。
我还发现了一种紫色的小花,它的名字也像花一样惹人喜爱——兰香草,在一片比它高大很多的野草丛中默默地盛开。
不仅仅是花和叶,就连果实,这个季节也在奋力为鹤岭增添几分姿色,红得,黑的,紫的,坚硬的,浆质的,圆球形的,椭圆,长的,大的小的……
看吧!叶子扎人的枸骨,它的果实竟然红彤彤地挂满枝头。尽管枸骨叶是治疗皮肤瘙痒的能手,要不是它红得可人的种子,谁不是避之唯恐不及呢?
传说中的冬青,除了满树绿叶,果实跟枸骨长得一个模样,只是呈稍微的椭圆,同样因一树嫣红让人久看不厌。
菝葜的种子也是可爱的小粒球形,表皮一层薄薄的霜色仍然遮不住里面成熟的红。
一路好多橙黄的金樱子,比去年买来泡酒的大很多漂亮很多。路上碰到一个山里人,采摘了一背篓的茶籽。
这次多亏了几位喜欢拍照的小姐姐,她们在后面给自己“咔嚓”美照,我也就可以毫无愧疚地慢悠悠拍下路旁的花花草草。
我们下午两点才开始上山,沿着山脊从东北向西南,不知不觉暮色渐合,天空低垂,高高矮矮的山峦粗犷起伏,由近及远渐次隐身于苍茫的雾里。雾的那一边,是一线红黄的云,太阳在云的深处努力地发着光。
我倒退着走完最后一节下坡的路,大巴在路旁等待,此时已是万家灯火。
最后必须备忘的是:中午吃的麸子肉,又是外酥里嫩的佳肴,制作方法与粉蒸晒干肉差不多。如果麸子肉因它的颜色有“东方红云”的美誉,我夏天制作的粉蒸晒干肉就是黑暗料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