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最先察觉了动静。
它裹着槐花香从巷口溜来,掠过老墙根那丛野菊,又掀起晾衣绳上半干的蓝布衫,是母亲晒了一整天的被面,此刻正扑簌簌抖落碎金。
我站在河堤上,看夕阳把最后一捧光揉进浪尖,波纹便成了流动的琥珀。
渔船归港了。
竹篙点破镜面的刹那,碎金溅成千万尾红鲤,又很快被暮色重新熔铸。
船老大站在船头收网,影子被拉得老长,像一根系在时光里的绳,一头拴着今天的鱼汛,一头拴着二十年前,他也是这样站在船头,送我父亲去县城读书的模样。
要落了,有人轻声说。
我抬头,太阳已滑到山坳背后,只剩半张脸浸在霞光里,像块化不开的糖。远处的电视塔、电线杆、晾衣竿,都成了它的剪影,连麻雀的翅膀都沾了蜜色。归鸟的啼鸣忽然密了,它们急着赶在黑暗前回到巢里,衔走最后一缕天光。
河堤下的石凳还温着。
那是我和阿婆常坐的地方。
小时候总嫌她唠叨,嫌她纳的千层底磨脚,嫌她往我书包里塞的烤红薯太烫。可此刻望着夕阳,我忽然想起她最后一次送我上学,也是这样的黄昏。她站在门口挥手,白发被风吹得蓬乱,像团没梳开的云。
放学早点回啊,她的声音轻得像片叶子,我却嫌烦,头也不回地跑了。
后来她走了,我再没听过那样的再见。
石凳旁的野蔷薇谢了,藤蔓却爬得更疯,缠上了那面老墙。墙皮剥落处,能看见从前刷的白灰,还有我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的早字,大概是小学时,为了不被阿婆揪着耳朵催起床,天没亮就爬起来补的作业。
如今粉笔痕淡得几乎看不见,像段被岁月泡软的旧胶片。
有人在河边洗菜。
竹篮里的青菜滴着水,砸出小小的涟漪。
大妈的围裙沾了草屑,她和隔壁阿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明儿该转凉了。
可不,你看这夕阳,红得跟血似的。他们的声音混着水声,飘得很远,又很近。原来最浓的烟火气,都藏在这些明天的念叨里。
最后一缕光从山尖跌落。
天地像被谁按下了慢放键:归鸟的翅膀变得沉重,炊烟升得愈发缓慢,连晚风都屏住了呼吸。我望着逐渐暗下去的天际线,那里还残留着一抹紫,像谁不小心打翻的墨水瓶,正慢慢洇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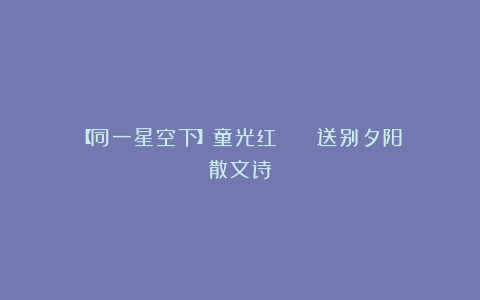
路灯次第亮了。
暖黄的光漫出来,把影子拉得更长。
有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追着泡泡跑过,肥皂泡在光里炸开,每一个都闪着微型的彩虹。她仰着头笑,发梢沾着夕阳最后的馈赠,原来告别不全是灰色的,它也会把温柔揉碎了,撒在新的开始里。
我想起阿婆的相册。
最后一页是她年轻时的照片,站在夕阳下的麦田里,辫子上扎着红绸,笑得比身后的晚霞还灿烂。
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不同的夕阳告别:童年的、青春的、亲人的、自己的。可那些被夕阳吻过的温度,早就渗进了骨血里,变成回忆里的暖炉,冬天一烤,就又亮堂起来。
夜色漫上来了。
星星开始试探着露头,一轮淡月悬在东天,像枚未干的银箔。河堤上的虫鸣渐次响起,它们在庆祝黑夜的降临,也在等待下一个黎明。
我转身往家走。
身后是彻底沉落的夕阳,身前是亮起的万家灯火。
原来送别,不是失去,是把今天的光收进行囊,好照亮明天的路。就像阿婆当年送我上学,就像船老大收网回家,就像小女孩追着泡泡跑远,所有结束,都是另一种开始的前奏。
晚风又起了。
它捎来远处教堂的钟声,捎来厨房里飘来的饭香,捎来记忆里阿婆的呼唤:回来吃饭啦。
我忽然明白,所谓送别夕阳,不过是我们借由一片光的落下,和自己、和过去、和所有温柔的旧时光,好好道一声:辛苦了,明天见。
2025.10.20
广东诗人(gdsr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