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春节回西昌,车子路过川兴中学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车速。那座熟悉的老校门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锈迹斑驳却依然挺拔,仿佛被时光遗忘,一如记忆中九十年代的模样。我多少次想过要进去看看,却始终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怕惊扰了青春,怕物是人非。
1995年秋天刚入学时,13岁的我背着军绿色的书包站在校门口,望着校门内右边那间小小的小卖部。那时还不知道,这里将成为人生中三年里抹不去的印记。
每当下课铃响,这里便瞬间被人潮淹没。学生们攥着皱巴巴的毛票,争先恐后地挤在柜台前,老板和老板娘忙得面无表情,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
小卖部边上,是阶梯教室和图书馆大楼,可惜那时很少有人去图书馆。老师从未告诉我们如何借书,它仿佛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我的初中教室,就在那栋两层高老教学楼一楼的最右边。
班主任葛老师,他总是穿着白衬衣和一件灰色夹克衫,印象中三年都没换过其他款式的衣服。
他总喜欢在其他老师上课时,偷偷在教室的木窗外弯着腰眯着眼,轻手轻脚,像一只狩猎的豹,观察哪个同学不认真,虽然近视,却挡不住那双能洞察一切的眼睛。
哪个少年没有在课堂上偷看过小说呢?我就曾因此被叫到老师家,挨过他的巴掌。当年觉得委屈,如今只剩感激与愧疚。如今我才懂得,那巴掌里藏着怎样深沉的期待。
川中的学习氛围很浓厚。
我们班调皮的学生不多,晚自习时整个教室都是背书的声音,人人都是捂着自己的双耳在背,因为如果不捂着耳朵就会很吵。而像我,在课本底下流动的小说书页,则承载着我对美好世界的想象。当葛老师猫着腰在窗外张望时,我们几个看小说的同学立即正襟危坐,等他走远又相视偷笑。
学校虽以农村学生为主,但也有好几个城里同学。记得有一年,有个男生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了老师们那两年教育我们的榜样。
我是走读生,每天穿梭于学校和家之间。
学校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小吃,唯一的“美食”是食堂早餐的米粉汤泡饭——去食堂窗口排队打二两饭,然后再去旁边的棚子里买一份米粉加上,用米粉汤泡饭。不要以为有肉,就是一点清汤,里面可能有几根洋芋丝。当时棚子里卖早餐的,基本都是老师的家属。
食堂只有窗口没有座位,大家都是自己找地方站着吃。
就是吃这样的“美食”,你下课都还要跑得很快,否则到最后可能已经卖完了,或者前面排很长的队,你要等很久。所以铃声一响,所有同学都以苏炳添百米冲速的速度,狂奔向食堂。
经常看到,有脚步跟不上思想的同学,“噗”地一声往前摔个大跤,手上拿着的饭盒摔出五六米远。却又不知道疼痛,马上站起来拍拍膝盖,捡起饭盒继续向前冲!
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重要的仪式,是从家里用自行车驮半袋米去学校换饭票,一斤米换一斤饭票。
食堂里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个子不高,负责给我们换饭票,他把所有同学运来的米,全部倒在一个房间里。什么品种的米都有,所以注定了食堂的饭自然不好吃。
他称完米的重量后,会给你十几张面值1两2两或3两不等的饭票。饭票3X6厘米见方,黄的、红的、蓝的都有,是塑胶做成的,有新有旧。
这时我就小心翼翼地把所有饭票卷在一起,用橡皮筋扎起来,放在书包最底部最安全的地方。每次使用是,都是把最旧的那张先用掉,新的往往留到最后。
那时,一天要从学校到家往返三个来回:早上上学,中午放学,下午上学,傍晚放学,去上晚自习,下晚自习回家。最开始是走路,单程20分钟左右。
只记得冬天天还在很黑,天空中还可以看到最亮的那颗北极星。父母还在熟睡,我起来洗漱完毕,轻轻关上家门,缩着头,双手插兜,向学校方向走去。
晚上下晚自习,如果遇到雨季,家门口那段300多米长的路,泥泞不堪,全是稀泥和积水。也没有路灯,只能把鞋脱下来用手提着,摸黑慢慢向前探索着走。
后来学会了骑自行车,大人也觉得安全后,就骑车去学校了。自行车停在高中生那一栋教学楼和操场中间的区域,有单车棚,有人值守,停一次一毛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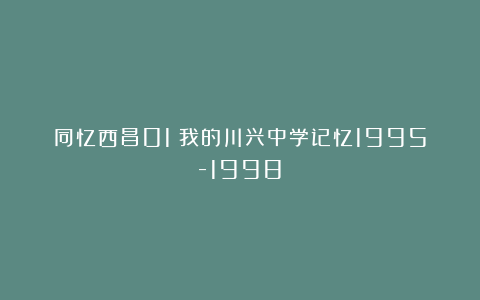
那时的老师各有特色。
思想政治是个男老师,浓眉大眼,被班上学生取外号“畸形”,不过课讲得很好;美术老师崔涛,头发有点长,康定师专毕业,由于我爱好美术,业余时间周末还在他那里学过绘画,就在食堂楼上的二楼,好像是他的宿舍;地理老师超级近视,却不戴眼镜,学生在下面玩闹他也不管,当时以为是近视看不见,现在才知道是不想管;英语老师蒙佐德,英语很厉害,头发有点卷,戴副眼镜;物理老师姓马,长得帅,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的父亲。
班上每个学期都会来实习老师,一个班大概会有3个左右,跟我们关系挺好。有个实习老师每次考试就只说一句话:“我们曾经也是学生,你们现在心里想什么,我们都知道,把不应该出现的东西不要拿出来!”。
由于平时跟他关系挺好,他这样说我们时,也不知道是真的严厉还是吓唬我们。一听到这话,像我这样胆小的,就只能把事先准备好的小抄,放在课本夹页里。也有胆子大的同学,老师一转身,立马用两秒钟时间扫过自己的小抄,那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同学关系单纯却也有隔阂。我小学的一个好朋友,升入初中也是一个班,因为一句话闹矛盾,三年形同陌路,直到毕业都没说话。那时通讯不发达,毕业后同学都没有联系了。
葛老师时常对我们说:“多喝水,少生病。”
他提倡生病只要多喝水,不用吃药,病也好得快。那时他买了两个大水壶,让学生轮流下早读后去开水房打开水,每个同学带一个杯子,打开水的同学还要负责把每个杯子装满水。开水房最开始不挤,后来各班都学习我们班,下早读课也都去打开水,就很挤了。
那时大家用的都是那种蓝色的塑料杯子,热水一倒进去,一股恶臭。现在才知道有毒不环保,当初也不知道喝下了多少毒水。
校外的租书店,开在川兴派出所旁农业银行大楼的一楼。
男生看陈青云、金庸、古龙,女生看琼瑶、席娟。一个班至少有10多个看小说的,都是晚自习看。
那时的娱乐就是看小说和听随身听,租书店的灯光总是昏黄得像旧时光。
我们在书架间穿梭,手指拂过金庸的豪情和琼瑶的柔肠。任贤齐的歌声从随身听里漏出来,飘散在太平洋的风里。
那些藏在课桌下被传阅得卷边的小说,如今都成了记忆里的经典。
初中三年的时光恍惚如梦,当时只道是寻常。
如今回首,才发现那些站在操场边吃饭的日子、那些骑着单车驮米换票的周末、那些在租书店门口徘徊的傍晚,已经成为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对那个驮着米袋的少年说:慢些走,多闻闻路上的稻香;对那个挨巴掌的少年说:抬起头,看看老师眼里的光;对那个站在教室窗外偷看我们的老人说一声:谢谢您。虽然您可能已经不记得那个被您打过巴掌的调皮学生,但您的教诲却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珍贵。
那段用一斤米换一斤饭票的岁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在朴素中成长的力量——那种虽然清苦却从不抱怨的豁达,那种纯粹而执着的坚持。
葛老师应该已经老得认不出我了,那个挨过巴掌的少年,长成了懂得感恩的大人。老校门还在那里,米香依旧飘在记忆里。而我们,都成了带着川中印记的大人,在各自的人生里,续写着那本永远不愿合上的青春之书。
本文系原创来稿
作者/雨润风和
2025年9月22日
写于昆明
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一首诗,
不如,我们一起把西昌系列写下去,
看看我们的记忆,最终是否汇成大河!
如果你有强烈表达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