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人总有些话,像刻在骨头里的印记。比如那句:“乌鸦、小燕子是万万不能掏的,那可是有灵性的鸟儿!”这话伴着乡风,从小吹进我心里,成了不敢逾越的界线。
掏鸟窝实在是门学问。没有懂行的领着,任你仰得脖子发酸,眼睛瞪得流泪,也寻不着鸟窝的半点踪迹。那些精灵,最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家藏进枝叶的迷宫里。
村南的蔡河岸边,便是我们的天堂。河水悠悠地淌,两岸树木蓊郁,藏着无数秘密。这里是鸟的王国,也是我们童年的宝库。麻雀、喜鹊、斑鸠,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都在这儿安家。而我们最惦记的,还是那肥嘟嘟的老斑鸠。
我的“老师”,其实是发小小峰。他小我两岁,瘦瘦的身材,却有着令我望尘莫及的本事——那双眼睛像是能穿透层层绿叶,精准地捕捉到每一个鸟窝的踪迹。我常常是望眼欲穿,他却总能嘴角一翘,随手一指:“瞧见没?那根歪脖子柳树第三个杈,往左,对,就那儿。”
顺着他手指,我总要费好大劲儿才能分辨出那团与枝叶几乎融为一体的灰褐色。这时,小峰会得意地搓搓手,朝掌心啐一口,像极了准备大干一场的工匠。
他攀树的身手最是让我羡慕。双手一抱,两脚一蹬,身子便轻盈地离了地。那不像爬,倒像是一尾鱼游上了树干。遇到横生的枝桠,他只稍一顿,身子一扭便过去了,灵巧得让树下的我看得痴了。
记得那个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杨树叶筛下斑驳的光影。小峰发现了一个尤其隐蔽的斑鸠窝,高高地悬在树梢。“这个够肥。”他朝我眨眨眼,开始向上攀。越往上,树枝越细,他的动作也越轻,像一片羽毛缓缓飘升。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既盼他成功,又怕他摔着。终于,他够着了那个窝。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的手刚探进去,便猛地缩了回来,整个人差点失去平衡。
“怎么了?”我急急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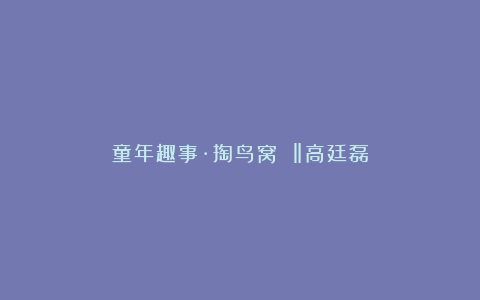
他稳住身子,脸上露出奇异的神情:“你自己上来看。”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去,凑近那个简陋的用枯枝垒成的窝。里面没有预想中的鸟蛋,而是三只刚孵出的雏鸟。它们光秃秃的皮肤透着粉红,眼睛还蒙着一层蓝膜,听到动静,便本能地张开嫩黄的喙,发出细弱的啾鸣。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老人为什么说不能掏某些鸟。看着这些毫无防备的小生命,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我们相视无言,默默地退了下来。
从树上下来后,小峰罕见地沉默了很久。河风吹过,带着泥土和水草的气息。忽然,一只灰斑鸠扑棱着翅膀落回枝头,嘴里衔着一条青虫。它警惕地看了看树下的我们,才飞回窝中。随即,那细弱的啾鸣变成了急切的啁啾。
“走吧。”小峰拍拍身上的树皮,“以后……少掏点。”
我懂他的意思。那个下午,我们坐在河岸上,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黄,看归巢的鸟儿划过天空。第一次,我们不再搜寻鸟窝的踪迹,而是静静地看它们回家。
许多年过去了,蔡河水还在流淌着,那些树更高更茂了。我不知道小峰是否还记得那个下午,但我始终记得那三只张着嫩黄小嘴的雏鸟,记得当我们从掠夺者变成守护者时,心里那种奇异的、温暖的触动。
童年的许多趣事都淡了,唯有那个掏鸟窝的下午,在记忆里愈发清晰。那不仅是关于冒险的趣事,更是一堂无声的课——关于生命,关于敬畏,关于我们与这世间万物该如何的温柔相待。
作者简介:
高廷磊,河南省淮阳区大连乡人氏,现为《宛丘文学》主编,《百度》之百家号责任编辑,烟台市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签约作家,大西北文学纸刊签约作家,曾多次获得金奖,优秀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