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泉与蜷叶初逢之际,便有前世今生在青瓷里流转。
所谓茶道,原是要将浮世嚣尘镇在壶底,待得碧烟袅作篆香,方知澄明不过是将往事沏成琥珀光景。昔年读《陶庵梦忆》,见张宗子雪夜煨茶,炭火映得冰裂纹盏如宋画残卷,而今想来,茶汤里的留白最是妙绝——譬如墨分五彩,茶亦分七韵,最浓酽处竟在余波。
建盏深处结着文明的痂,釉泪凝成茶山。
吃茶人总爱说陆羽遗风,我倒觉得《茶经》不过是个楔子,真正的茶史藏在老紫砂的包浆里。前岁在京都某寺,见茶杓柄端镌着“无”字,忽忆起寒山诗“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茶道中的禅机,原不必说破,像六安瓜片在龙泉青瓷里舒展腰肢,风骨自现。
《洛神赋图》
茶席铺展如《诗经》里的鹿鸣宴,温杯时听得见商周青铜的回响。
某次见茶人注水,弧线竟与《洛神赋图》中曹衣出水暗合,方知茶艺原是流动的汉碑。最喜看老普洱在沸泉中翻身,褶皱里渗出光绪年间的梅雨,恍惚有戴望舒彳亍雨巷的跫音。茶垢积成建窑兔毫纹,倒比博物院橱窗里的钧瓷更见性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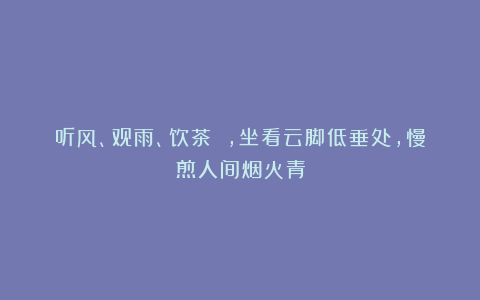
吃茶须学宋人点茶,持筅击拂如写瘦金体。昔年在乌镇老宅,见佣妇用粗陶罐焖野茶,茶沫浮沉竟似赵孟頫《鹊华秋色图》中的汀渚。忽悟茶道本无雅俗,如《楚辞》与山歌同属楚声,不过隔了层湘帘。
而今茶艺师多效东瀛仪轨,殊不知唐宋茶宴本有胡旋舞助兴,茶香混着龟兹乐,比寂寥侘寂更近汉唐魂魄。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茶汤三沸最见世相。初如少年涉世,翻滚着要溢出建盏;再沸便似中年沉凝,白沫聚作终南山雾;待三沸水老,竟生出“行到水穷处”的澹泊。某夜读《洛阳伽蓝记》,以六堡茶佐北魏旧事,茶味愈陈愈见荒寒,恍若伽蓝雨落满铜驼荆棘。茶之妙,原在让人在七碗通仙后,仍能尝出第一泡的草木清欢。
老茶客皆知第七泡最值玩味。头道如惊鸿照影,二巡似快雪时晴,至茶味将尽未尽时,倒显出倪云林画中的萧散。曾见潮州老叟泡凤凰单枞,十八道犹存岩韵,令我想起敦煌壁画里菩萨的第十八重衣纹——最淡处反见本真。这道理,与八大山人晚年画鱼,独眼向天同一机杼。
茶渣沉底最堪观想。幼时见母亲倾尽残茶,叶片在粗陶碗底站成黄山群峰,始信《山海经》地理非虚。某年秋深,在奈良唐招提寺见鉴真旧物,茶筅已朽如焦尾琴,唯茶渍在经卷边缘洇成雁阵,恰似王摩诘“大漠孤烟直”的平远构图。原来茶事终究要归向“空”字,如怀素狂草写完最后一笔,满纸云烟忽化雪泥鸿爪。
煮水候汤时最宜冥想。电壶嗤嗤如现代性谵语,铁釜松涛才是茶道本味。记得在纽约寓所烧水,窗外帝国大厦刺破云层,竟与陆羽“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之论暗通款曲。忽觉茶道如《文心雕龙》,既要雕缛成体,又须自然会妙。这悖论,倒应了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可怖而绝美。
茶香氤氲处,总浮着文明的倒影。英伦贵妇往祁红添奶,让我想起马可·波罗往西湖掺葡萄酒;土耳其人煮茶加松仁,又似赵佶往贡茶撒龙脑香。最妙是摩洛哥薄荷茶,滚烫甜腻中透着《一千零一夜》的余韵,比之日本抹茶道,倒更近盛唐气象——毕竟长安西市,本就列肆着波斯邸与大秦寺。
茶事终了,建盏底部的残叶总让我想起吴镇《墨菜图》。那些被沸泉拷问过的青叶,最后在陶土里站成倪瓒笔下的孤亭,倒比新茶时更见风骨。这道理,与木心先生所言“不知该原谅什么,但觉世事皆可原谅”同理——茶道原是要人在第七泡淡如月色时,懂得与宿命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