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朗月 不期而遇
关注江月之声
阅读原创文章
【特约专栏·唐兴顺研究】
刘颜涛 诗/书
笔锋如刃破苍茫,七岸洪流泻太行。
立传偏怜蒿莱痛,构图长寄黍离伤。
千层世相凝斧削,一卷民魂铸石章。
莫道山深湮炬火,云开天地自辉光。
拙句读《奔腾的七岸河》呈唐兄兴顺先生,僅此志贺大著出版。岁次乙巳初秋月,涤心草堂主人刘颜涛并书。
陈才生
唐兴顺的长篇小说《奔腾的七岸河》,讲述的是山中女子邢林子的悲剧命运。作品通过她与四个男性之间奇特的情感经历,写出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农村特有的社会风貌。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情感是人物形象的焦点。邢林子的情感历程与她生存的环境相关,与她坎坷的命运相关。如果说她与四个男性之间的情感可以称作“爱情”的话,那么用“身不由己,情不自禁”来形容更为确切。是卑微的社会地位和不可掌控的个人命运导致她情感投放的无奈、错位与迷茫。
彭随明是最早闯入邢林子情感世界的异性。那时的邢林子,刚出深山,进入中学。她爱好朗诵和唱歌,大胆地追求着精神上的自由,理想的天空一片纯净。当她在校园受到霸凌时,是彭随明出手相助,她甚至不知道这位男生的名字。当她受到流言伤害时,是彭随明给了她充分的理解和维护,她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动。然而,当彭随明面对人群宣告要和她“自由恋爱”时,无异于在播放马路广告,等于坐实了两人的关系。她只能随波逐流,上了彭随明“爱情”的小船。于是才有了甘愿忍辱负重去给彭母守灵的举动。但两人之间实属萍水相逢,究竟有多少心灵的契合,值得怀疑。包括小说的叙述者也为主人公担忧:“在还没有染上生活的常规尘埃之前,就先被彭随明占位了,被爱情占位了,而且经过闹腾和折磨,这种占有得到了强化和膨胀。换句话说,她还没有来得及接触生活的真相,就被捷足先登的事件给绑架了。”后来的故事表明,邢林子尽管认可彭随明的真诚,但他的平庸无能,对她工作的“拖后腿”,让她感觉“遥远而陌生”,尤其是他为老板周奎跑腿因工致残后,无异于生活中的“废人”:
他也是真心对我好的,他是没有恁大能力。现在废了,人不人鬼不鬼了,说实话,有时候夜里看他的身体,作为男人的一切他都没有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此时,在邢林子眼里,彭随明顶多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一个需要自己付出责任和义务的家人。这种生存的困境和爱的无奈,奠定了她情感生活的悲剧基调。
邢林子当选上村里的“计生专干”后,遇到了好大喜功且“好色”的副乡长陈云鹏。对陈云鹏而言,美女如同社会中一种稀缺资源,获取它的唯一方式便是占有。邢林子充其量只是他宣泄性欲的一件工具,两人的邂逅,很难用“爱情”二字来评价。为达目的,他不惜利用特权,把她调到身边。而邢林子呢,起初是进入权力圈的恐惧和迷茫,继而在陈云鹏的权威里,她似乎看到了改变自身现状的希望,由无奈顺从到主动配合,到“疯狂地向他贡献自己”。直至陈云鹏被免职,她灰溜溜地逃回村庄。情感的越轨给她带来的,除了难言的羞耻和负罪感,便是周围人的鄙视与嘲笑。
邢林子遇到的第三个男性是石钟鸣。两人之间产生纠葛,完全是打官司中的“副产品”。面对冷酷无情的沙石厂老板,她感到孤单无助,是石钟鸣挺身而出,帮其维权。她自然心生感激,但并无非分之想。直到石钟鸣向她倾吐多年以来的爱慕,才如梦初醒,被真情打动。正如她后来投入曲流歌怀抱时所说:“他为了我,竟然长期留在七岸村,心是在我身上的。”尽管如此,石钟鸣并不是完美的,她补充说:
他当时就明白告诉我,对我好,会千好万好,对女儿也能视同己出,对父母也应该没问题。但是把彭随明带上,一家人包起来管,特别是还可能要在一起生活,他说他做不到。当时我没怎么吭声,但心里就想以后得疏远这个人了。
她所理解的爱,就是要对方能负责她的家庭,因为她要生存。石钟鸣虽然有工资,但作为一个普通职工,哪有如此经济实力?又哪有这种惊世骇俗的勇气?也许这只是邢林子移情别恋的一个理由:不是妹妹不爱你,是你爱的不彻底。为了生存,实出无奈。或者是在委婉地向曲流歌提条件:生存是爱的前提。事实上,石钟鸣很有自知之明,面对情敌曲流歌的慷慨与豪横,他很快撤出了爱情的“阵地”。
邢林子与曲流歌,最初只是师生关系。在少女时代,如果说有情感的波动,也只是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当曲流歌因为与她的交往而被调走时,她只是觉得“难受”和“羞愧”,谈不上什么爱情。对我行我素的曲流歌来说,也压根没把它当回事,“自然也无从关心和了解到给邢林子带来的遭遇”。在后来的日子里,两人未曾有过任何交集。因此,在与石钟鸣相爱时,邢林子能果断转身,毫不犹豫地投入曲流歌的怀抱,除了对这位“救世主”的报恩,别无其他。她对曲流歌的表白,颇能说明这一心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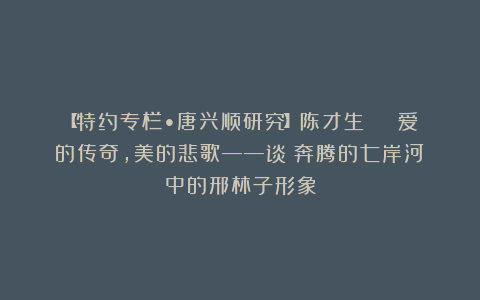
你把我从地狱从坑里捞上来,捞成人上人,这世上除了我,谁有这福气。……你只要觉得好,就我这全身,里边的外边的都给你,完完全全,永永远远都给你,曲老师你想怎么使就怎么使。
曲流歌“稍动弹簧”,便把她从劫难中救出,并使她全家都掉进了“福窝里”,这让她彻底折服于资本的威力,心甘情愿地以身体作交换,成为其“专属副产品”,过着被“包养”的生活,“每天化妆,喝下午茶,吃夜宵,与县城头面人物们玩台球,与一些贵妇人阔太太打麻将玩扑克牌……”如果说她离开石钟鸣是迫于生存的无奈,那么,对曲流歌“以身相许”不也是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选择吗?
爱情是平等的,无私的,有尊严的,而在邢林子的情感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在难以掌控的命运中的性爱选择,犹如一叶漂泊不定的小舟,身不由己,在满足生存的欲求时又情不自禁。身体的物化与性爱的交易,与爱情毫不相干。这是邢林子的悲哀,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所有“小人物”的悲哀。美丽、善良、懦弱、无奈、可怜、可悲,是邢林子形象的重要特征。
在曲流歌入狱后,邢林子无枝可依,回到了生养她的深山老屋,靠着自己的积蓄、美貌和歌喉,开起小酒店。尽管她把发型又一次“放纵了一把”,“更加另类,开放,迷人而招摇”,尽管她“借助身段和眼神把某一些男欢女爱的情境演绎得动人心弦”,但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她是怅惘的,迷茫的,失落的,伤感的。如她歌中所唱: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
爱我的人她还没有来到。
这是爱的无奈,还是情感的解脱?是看破红尘的放纵,还是生存困境中的选择?总之,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作家唐兴顺
文章至此,我们该讨论这个人物的文学价值了。
西方学者布鲁克斯曾经说过:“无主题便无小说。”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仅在于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或重现一段生活,而是要告诉读者自己的独特发现,即在感性世界中所蕴含着的丰富意蕴。那么,作家在《奔腾的七岸河》里,通过邢林子的故事究竟发现了什么?
作者曾经说过,小说最初的灵感起源于他青年时期所听到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却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深水区。是什么因素给原本美好的邢林子带来如此坎坷的命运和心理扭曲?是她的美貌吗?显然不是,美是无罪的。是她的贫穷吗?如小说中所言,“这个人天生的模样本不该在底层人中的”,似乎也不全是。虽然在底层社会的生存链里,她是一个被鄙视者,被忽视者,但在任“计生专干”时,她表现得认真负责,铁面无私。这种耿直、敬业、积极、上进,也不应该成为其坎坷命运的原因。那么,导致其灵魂的妥协与异化的罪恶渊薮究竟在哪里?那便是生存环境中不可扼制的人性欲望,自私、贪婪、虚荣、依赖、幻想……它给人们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心理的满足,同时也像熊熊烈火,吞噬着人的淳朴、善良、真诚以及所有的美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排挤、攫取和占有左右着彼此的命运,带来了生存的困境。正如叙述者所感慨的:“人间的烟火,世俗中的启迪、诱惑、光荣与梦想等看上去与身体无关的东西,有时候才正是打开生命重重神秘之门的钥匙……”从陈云鹏到熊主任到冷良玉到周奎到曲流歌,从校园的流言到工地的伪证到官场的觥筹交错,无处不体现出人性欲望的作祟。小说中,邢秋木对火的幻觉,大洪水对“淘金者”的“清零”,不就是颇具象征意味的兆示吗?
太行即景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邢林子是欣赏的,同情的,怜爱的,如小说中所说,“她美着、纯洁着、特异着”,“我们美丽的主人公”,“她本来就是个聪慧的人”,她“比原来更贵气更美丽”等等,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显然,在作者笔下,邢林子已经成为美的象征。但她的品行随着故事的发展与我们的期待愈来愈远。她先后成为三个男人的情人,或被动,或主动,不是为了满足其“身份感”和“被尊重感”,就是为了感激或报恩,这种以身体为代价谋求生存利益的“交换”,没有底线,没有尊严,难怪会成为村民的笑谈。小说艺术的自律性展示给我们的是人性的痼疾与悲观。如此形质相悖的反差,固然是邢林子人生的无奈,对她而言,生活难以为继,爱就成为奢望;又何尝不是作者的无奈,活生生的现实证明,美与善难得两全。这种主观意图与文本效果的龊龌,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如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等等,赞美中蕴含着反省,同情中渗透着批判。如金圣叹所说,“褒贬固在笔墨之外”。初读时,怜其孤苦无依,再读时,叹其软弱无骨;又读时,则惊见一个弱肉强食、人性异化的世界。看似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故事本身的思想张力与艺术魅力。
因此,邢林子这一形象,不仅反映出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和爱的艰难,同时也是对美的绽放与凋零的一曲悲歌。作者通过人物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感经历,真实地再现了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美被欲望所绑架、凌辱、异化、吞噬的过程。其中渗透着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思辨,对社会丑恶的大胆揭露和尖锐批判。
然而,在商业化的环境中,人性的痼疾不可能彻底消除。猫脸峰下,七岸河畔,虽然波涛不再,但却日益喧哗。鳞次栉比的农家乐,邢林子的小酒店,搔首弄姿的招徕,轻歌曼舞的挑逗,“怀着各种心事”的食客,慕名而来的酒徒,于“灯光明灭”的黄昏,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
《奔腾的七岸河》
选摘
身着绿色羽绒服的邢林子站在小饭店门口,浓密的黑发在脑后轻松地拢着,发挥约束作用的是一枚黄色塑料发卡,它的结构像一个微小的弓弩,除了弧形的互相配合的两个销片之外,还有一根斜插上去的短棒。正是红轮西坠时刻,太阳骑在太行山的脊背上,用尽余力把玫瑰色的看似强劲实则柔弱的光辉洒下来。在照射邢林子之前,它先经过村委会堆放杂物的那个西屋的屋脊,照射邢林子时只能照着她的上半身。如此,这位已经发育丰满的少妇,膝盖以下便处在阴影中,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全部涂满了光辉,使她像立在浅水里的花朵。
作者简介
陈才生,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 《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地摊上的诗行》《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朱德润集校注》《朱德润文学研究》《自在文录》《离天最近的地方》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