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秋,洛阳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中。75岁的白居易病逝于自宅,这位写下《长恨歌》《琵琶行》的“诗王”结束了他的六十年创作生涯。
消息传至长安,刚登基五个月的唐宣宗李忱悲痛难抑。
他追赠白居易为尚书右仆射,赐谥号“文”更以一首《吊白居易》道尽哀思,
诗云: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首帝王诗,不仅成为了悼亡诗之中的绝唱,更让后人得以窥见大唐文坛“君与臣”之间那一份惺惺相惜。
白居易的诗歌旅程从困苦开启,772年,其降生于河南新郑。
在童年时期,由于战乱的波及,他颠沛流离。
在求学之时,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至“口舌生疮,手肘起茧”之态。
16岁那年,他凭《赋得古原草送别》这一作品声名大噪,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诗直至如今仍被大众广为传颂。
29岁考上进士之后,白居易将“兼济天下”视为个人的理想,创作了《卖炭翁》《秦中吟》等作品这些诗作,充满讽刺意味,把社会问题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但这种较为直接的处事方式致使他多次遭受贬官。
815年,宰相武元衡遭人杀害,白居易上书请求严厉惩处凶手,却不成想因这个被安上“越职言事”的罪名随后被降职为江州司马。
此变化让他从起初的“为民请命”渐渐转变为后来的“独善其身”。
白居易在晚年时前往洛阳隐居,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了佛道以及诗酒这些方面。
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一首《杨柳枝词》竟然触动了新帝李忱的内心情绪。
在这首诗中“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所描绘的那株孤独的柳树,被李忱当作了诗人自己的写照。
他命令手下把永丰柳移栽到了宫中,并且传话给白居易说:“这棵树能够遇到天子,就如同你遇到了英明的君主一样。(此树得遇天子,犹卿之遇明主)”。
此时正生病的白居易深受感动,回复了一首诗说道:“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
此时的李忱,正是那位,曾装疯36年,以“痴傻”骗过宦官,最终逆袭登基的“小太宗”。
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诗歌,更是将其视为未曾谋面的知己。
不过造化弄人,李忱登基仅仅五月,白居易就突然离世,二人终究未能得见一面。
《吊白居易》的珍贵,在于它不仅是帝王诗中的翘楚,更以精妙笔法将白居易的“名”与“志”融于诗中。
首联“缀玉联珠六十年”,赞其诗作如珠玉璀璨,创作生涯跨越甲子,
颔联“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巧妙嵌入白居易的名与字,既叹其如浮云漂泊,又赞其顺应天命、豁达洒脱的性情。
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点明白诗“老妪能解”的通俗性,以及跨越民族与阶层的传播力,
尾联“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帝王之尊道出文人相惜的锥心之痛,真挚动人。
李忱的深情,不只限于诗文这一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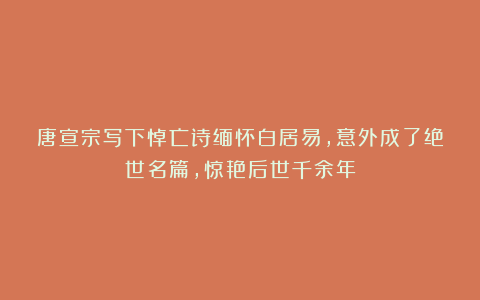
在他掌管大权之时,他主动去整顿吏治,把宦官的权力给成功地压制住了,由此开创了“大中之治”,并且被后世称作“小太宗”。
另外他特别推崇文化,使得晚唐文坛绽放出了短暂但耀眼的光芒。
白居易的诗集被认真地编纂成了《白氏长庆集》,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还传到了日本,变成了当地贵族争着去诵读的经典之作。
《吊白居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帝王诗歌长久以来那种固定的、模式化的框架,以更平等的状态,向文人李忱传达了敬重之意,在此处没提及白居易的官职身份,而是把焦点,集中在他的诗歌水平以及精神品格上。
这种表达手法,在大唐王朝,乃至整个古代历史进程里,都显得特别独特,并且比较少见。
更令人唏嘘的是,诗中竟然将白居易称为“诗仙”,这比后世对李白的这一称号早了数百年。
如果说不是明清文人重新评定诗坛地位,今日“诗仙”之名或许就属于白乐天了。
白居易与李忱一个乃是“惟歌生民病”之诗坛巨擘;一个却是“隐忍谋天下”之中兴之主。
二人交集虽短暂,不过却因一首诗造就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传奇。
千年后当我们再度读起“一度思卿一怆然”,依然能够触摸到大唐盛世最后的温度——那实则是一个帝王对诗人的致敬,更是一个时代对文化的挽歌。
————
人声鼎沸的长安街头,窄巷深院里流淌着新鲜的故事,只是谁也没料到,一位老诗人的离去会让皇帝夜不能寐。白居易去世的噩耗像一阵风,穿过御苑深深的槐树,把唐宣宗的思绪搅得乱七八糟。这年头,朝堂变动频频,宫闱风雨、江湖起伏,各路人马都在打着算盘,唯独白居易,他把心留给了诗,也留给了普通百姓。这样的气氛下,一句悼亡诗从宫里流传出来,不是宣纸上冷冰冰的规矩,而是皇帝送给另一个“诗界天子”的情深,一座王朝的温度,就在那一行行字句里站了起来。
要说盛唐的“繁华”,外面人以为只是高楼大厦,长安夜不闭户。其实更曼妙的,是那个时代谁都能写诗。外交使臣挤满了麟德门,市井百姓路边吟唱新词,胡人小孩会背长恨歌,和尚也能和大官打擂台。大唐的自信,温柔中带点浪荡,就是那种不怕你来,不怕你走,生活烦闷、诗歌作伴。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但是城市烟火下的忧愁,细水长流,没谁能躲开。一些书生在灯下苦读,也盼着有朝一日为国分忧,仿佛济世安天下是一种“正常”的人生规划。可现实嘛,总比理想拧巴那么一些。白居易三十余岁方中进士,兜兜转转官场浮沉,这种兜底的低落和自持,恰恰成就了那一首首与众不同的诗章。
大家都记得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可白居易,他偏是别样的。拿什么与前人比?不是天生才气,也不是自小顺遂。小时候家就颠沛流离、战火飘摇,勉强让人活着,谈不上安稳。书桌前头发尽白,人生如逆旅。偏偏心还没变硬,是不是有点犯傻?其实那些书生读他的诗,会发现,他写的都是真的。他不写虚词,不故作姿态,讽政诗里有百姓家的愁苦,也有堂上的冷漠。一次次被贬,从京城到地方,无非是自信碰了钉子,良心被权力搁置,本事用错了地方,但诗,不是。
节奏变化很快。宰相死于非命,白居易上书求查,转头被贬出京。朝堂冷漠,白居易自知无法左右结局,便拿起自己的长笔,把现实写进韵脚,把词借给普通百姓。反过来看那些治世的大员,有谁比他更关心柴米油盐?哪里还有一丝文人的锐气?老了之后,他心里的牵挂彻底松动,遂依禅理、信佛法,自号香山居士。朝廷变天时,他已是两鬓苍苍,病困洛阳,像老树一样等到叶落。告别这个世界时,留给人的便只有那“文章满行人耳”。
轮到唐宣宗登基。这位新皇不比寻常,年纪已大,上台没有几分天真。他懂诗,也懂权力。和许多前朝帝王不同,唐宣宗没有自以为是地抬高自己,反倒欣赏那些民间来的声音。说起来唐宣宗和白居易,也算陌生知己一个坐在龙椅上体察万象,一个游走官场写尽沧桑。同样的旧唐书,新唐书,两人故事依稀相互映衬。唐宣宗喜欢白居易的诗,并不因其文采,更因那一股子实意。宫里的人背《长恨歌》,市井百姓唱《琵琶行》。宣宗的世界,天子与诗人,既远又近。这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知音,却有种莫名的惺惺相惜。
奇怪的是,这首悼亡诗的分量反倒重了。皇帝给大臣写诗,本是应景之举。可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有点儿不舍。不是敷衍,也不是陪衬,像是一位老朋友的倾诉。“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既入骨、又平白,看似随手,实则言有尽,意无穷。小孩会吟唱,胡人能和。这样的日常细节,反衬了诗人在民间的分量。不是“高高在上”的钦定,而是一种流动着的归属。“一度思卿一怆然”,句尾收起哀思,藏不住感慨。诗读罢,仿佛看到那个繁花盛开的旧时长安,既厚重也轻盈。
由上观之,白居易以普通百姓的目光写诗,正是大唐文化底气里最温柔的部分。他的成功,不在才华横溢,而在能把景换成情。唐诗是书写,也是安慰,是那个动荡世道中彼此温柔相待的见证。皇帝所叹之“文章满行人耳”,哪里是普通的诗名,其实是认可诗歌能穿越时代、跨越身份,成为全民的精神粮食。几百年后,当后人复诵这些诗,或许已经忘记诗人的窘困与荣耀,但那种坦荡温厚的情怀却能一代代传下来。
有些人盛唐是大气与开放的代名词,那些诗篇高山仰止,可白居易恰恰以平易近人打开另一个角度。他不装腔、不故作清高,而是把目光投到弱者、老百姓身上。对于后人的影响,无需雕琢。可以如果盛唐诗歌是条江河,李白是浪花奔腾、杜甫是波涛暗涌,那么白居易就是河水静流,包裹泥土。没有他,这条大河只怕少了点温度,少了种生活的光芒。
再看唐宣宗,他的悼诗倒像是一面镜子。权力与文化、个人与时代,彼此映照。白居易已逝,诗歌犹存。唐宣宗用诗作寄托哀思,也是他自己的孤独与不舍。那些身居高位者,看似无情,其实也在意失去的人与事。悼诗里的惜别,既是对白居易的缅怀,也是唐宣宗自我情绪的出口。就像盛世余晖里那一抹柔光,不耀眼,却温暖。两个人在诗歌空间里完成一次真正的会面,也让旁观之人嗅到了唐代最后的那个温柔时刻。
有意思的转折在于,正当盛唐歌舞升平,人们总以为繁华不会终结。可是,动乱、变故、短暂的安宁,层层叠加,连王朝的尾声都写得极具诗意。白居易看破红尘,唐宣宗依然为长生苦苦追索,终究免不了一死。政治与艺术,现实和理想,既分割又交融。甚至诗人与帝王,在生命终点,居然有了同样的不安与寄托。世事无常,写到这里,不觉莞尔。
几百年后,长安归空,诗人姓名早已风化在碑石。可《长恨歌》、《琵琶行》、《吊白居易》,这些词句还在流淌,普通人的日常里总见得唐诗的影子。以一首悼亡诗,小至一人哀怀,大至一个时代的温情,这是大唐留给后人的不灭印章。白居易的温和与执拗,唐宣宗的坦率与孤独,全都印在字里行间,不需要更多修辞。
很多时候,人们渴望盛世,钟意名士,却仍得回归质朴那些穿透千秋的诗句,是来自人心最柔软的部分。白居易的存在,证明了一个诗人可以温暖一代人,甚至让一国之君低头哀思。唐宣宗这一首悼亡诗,是他与白居易,也是他与自己的和解与告别。这才是盛唐精神里最珍贵的一笔。
追问盛唐已无意义,再去小心翼翼地分析诗句,不如记住人世间的繁华,终究会过去。而温厚、真诚、懂得悲悯的人和诗,才是活得最久的风景。这才是真实的遗产,也是一个大国气度下的深情。
白居易已归尘土,他的诗流传下来,活在每个人的嘴边。大唐不死,只要还有人愿意唱歌、写诗、为苦难之人落泪。谁还不懂这个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