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汤晶,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艺报》等发表多篇文章。
作为精神史转折点的1923年——鲁迅杂文视野中的“兄弟失和”
摘要:1923年的周氏兄弟失和事件不仅是鲁迅人生的转变,更构成其精神史与文学创作的转换期。从鲁迅杂文创作的历程看,鲁迅在此事件中遭受的精神创伤直接导致其杂文创作陷入滞缓期:1923年至1924年,其杂文数量锐减,显露出对现实回应的回避与内心秩序的失衡。本文通过钩沉鲁迅杂文创作脉络与精神轨迹,揭示1923年兄弟失和事件如何以“断裂”与“突围”的张力,推动鲁迅完成从随感录创作到杂文自觉的转型,并最终奠定其作为现代中国批判性写作的典范地位。
关键词:精神史转折;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杂文
1923年7月14日的鲁迅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里周作人送来的便是绝交信,鲁迅日记中表明曾想分说问辩,但周作人拒绝沟通。七天后,鲁迅“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这延宕的一周,兄弟二人毫无沟通,由此,兄弟二人决裂,鲁迅开始筹备搬离八道湾。
学界关于“兄弟失和”事件的研究,主要从历史考证入手,探寻失和原因,主要有“经济矛盾说”“伦理冲突说”等。再者便是据此分析这一时期鲁迅文学创作中对兄弟之情破裂的暗喻。其中,吴俊认为鲁迅在1923年经历兄弟失和事件后,写作了以“牺牲者的被弃与愤怒”为主题的系列文字,包括《野草》中的《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风筝》。刘彬、朱崇科等则是将鲁迅小说《伤逝》《在酒楼上》阐释为对兄弟失和的隐喻。无论何种,都可以看到学界关注1923年鲁迅的精神状态与此间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并且认为1923年确对鲁迅文学创作的主题、风格,甚至是道路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但相较于阐释《野草》及《彷徨》中的部分篇目,从鲁迅杂文创作的脉络上系统呈现1923年的特殊之处尚有阐发空间。一方面,1923年的痛感和沉淀,正是介于“随感录”时期的练笔与1925年陆续编订杂文集之间,形成了鲁迅杂文创作史上的低谷期;另一方面,《语丝》的创刊与鲁迅的供稿,又逐渐催生杂文的写作,为1925年鲁迅杂文自觉奠定了重要基础。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的变化与鲁迅杂文道路的明晰复杂地纠葛在一起。
一
兄弟失和后鲁迅杂文创作的滞缓期
回顾1923年鲁迅的文学活动,包括1月11日作《关于〈小说世界〉》,1月13日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说明》,为1923年6月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作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10月整理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初稿,并作200余字的短序《〈中国小说史略〉序言》。11月完成学术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此外就是翻译了三篇爱罗先珂作品《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爱字的疮》《红的花》。12月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演讲稿于1924年6月发表。
《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6年版
确切地说,1923年兄弟绝交后,鲁迅仅有《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发表,这还得益于这一时期正在整理讲义《中国小说史略》,这与论战或是抒感的鲁迅式杂文有明显不同。鲁迅回避了对时事的应变和讨论,1923年科玄论战及由此而来的“人生观”大讨论、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等,鲁迅并未及时回应。“1924年的前8个月中,他只在1月里连续写了三篇小杂文《对于’笑话’的笑话》《奇怪的日历》《望勿’纠正’》,2月至4月间,他完成了四篇短篇小说《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在酒楼上》,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此外还有三篇与《嵇康集》有关的’序’、’佚文考’和’著录考’的学术作品。由此可见,在长达20个月的时间中,不算翻译和学术著作,鲁迅的写作其实只有四篇杂文和四篇短篇小说,加起来大概两三万字而已。”[1]
兄弟失和事件直接导致了鲁迅精神受挫,写作滞缓,并为其离京埋下伏笔,以至于鲁迅此后文学道路的变化,都由此发生了转折。在此,将鲁迅杂文创作的数量和时间做粗略统计,创作趋势如图1所示:
注:各杂文集中收录的鲁迅留日时期的论文、科学说明文等不计入。
《且介亭附集》中许广平作《后记》不计入。
《集外集》中创作于1912年的诗歌不计入。
《集外集拾遗》中收入的小说《怀旧》与发表在1938年的诗歌不计入。
《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按语、广告说明、摘自周作人日记中的篇目等不计入。
鲁迅去世后另行发表的杂文,根据落款的写作时间,归入写作的年份计算。
将瞿秋白托名鲁迅发表的杂文也计入其中。
根据统计数据和图表,1920年和1923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两个低谷期。1920年鲁迅未曾创作杂文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当年是鲁迅举家从绍兴搬到北京八道湾后的第一年,1920年初鲁迅还在为房契税奔忙,5月,周建人不到一岁的次子周丰二患上肺炎,住院近两月,鲁迅为此多次来往于医院和家,颇费心力。1920年下半年,鲁迅又要准备在北大国文系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加之五四落潮,为了《新青年》“随感录”而写作的杂感告一段落。1920年,鲁迅的家事及文学创作初期的摸索和协调,使得1920年稍显“动力不足”。而1923年受到兄弟失和的影响和牵绊,鲁迅在失和后“一两年”中“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2]当年10月,在鲁迅致孙伏园信中,鲁迅请孙伏园代为辞谢与自己交好的川岛夫妇来访,只因声明定例“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3]。足见鲁迅此时心境之寂凉,不愿为世务所累,宁愿“销声匿迹”。
兄弟失和事件给鲁迅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刺激和心理创伤,鲁迅再次被孤寂、悲苦的负面情感所缠住,此后兄弟二人的交往更是恶劣相向。鲁迅搬离八道湾时,留下了此前收集的砖石拓片,后来回八道湾取收集的拓片时,鲁迅一方记载周作人夫妇对他十分不敬。周作人则记录为“下午L来闹”[4]。鲁迅在1924年9月21日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里说自己“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5]鲁迅非常愤怒地称周作人为“寇”。这篇文章中鲁迅第一次使用“宴之敖者”的笔名。根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生活日常》中的解释,“’宴’从门、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即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6]。兄弟失和严重的打击也导致鲁迅身体健康的崩溃。1923年9月,鲁迅肺病复发,这次漫长的生病直到次年4月才转愈,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是鲁迅最早的一次、严重的、历时长的肺病发病记录。
二
绝交前后两次记录“风筝事件”
在鲁迅回忆童年的记述中,“风筝事件”因其伴随着强烈的内心不安和忏悔自责,已经成为一次精神事件。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风筝事件”有过两次记述,两次记述的中间,鲁迅经历了1923年兄弟绝交。在此暂且搁置讨论《风筝》中的原型人物,即小兄弟的原型是周作人还是周建人?要明晰的是两次“风筝事件”记录中鲁迅精神状态的差异。旧事重提的鲁迅在祈求宽恕的心绪中,有何情感的深层意味?对于搬出八道湾之后的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结构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或者无意识流露?
1919年,鲁迅在《自言自语·我的兄弟》中首次写下了自己实行精神虐杀的“风筝事件”,这篇杂文发表在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后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由一组短小文章连缀而成,其中包含《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最后一则便是写风筝事件的《我的兄弟》。这一组文章中既有小说的故事笔法,又有散文写作的心流,充满象征的手法,短小精悍但又颇有意味。其中《我的兄弟》写得简明清晰,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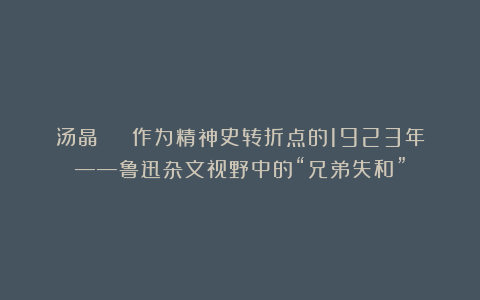
《风筝》载《语丝》1925年第12期
到了1925年1月24日,鲁迅再次写到“风筝事件”。此时正值春节期间,在北京冬天的肃杀和周围合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中,鲁迅独自一人显然感到异常的悲哀和落寞。这篇《风筝》发表在当时周作人主编的1925年2月2日的《语丝》上。鲁迅为何反复提及此事?他的内疚感怎么这么强烈?将《风筝》与此前的《自言自语》对读,会发现在叙述内容相同的情况下,细节处鲁迅心境的差异,其中差别最大的是两篇文章结尾鲁迅的心绪,从“还是请你原谅罢”到“无可把握的悲哀”。《风筝》中增加的篇幅和内容,所见与《自言自语》的差异之处如下:
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8]
同样的虐杀小兄弟童年游戏精神的事件,两次出现在鲁迅的记述中。除却叙述内容完全一致,《我的兄弟》是对这件错事的线条勾勒,还原了此事的关键性节点,而《风筝》的叙述连贯性更强,情感更为细腻、波澜和曲折。如果说《我的兄弟》是为了记录和致歉,那么《风筝》则是呈现永陷感伤情绪,遗忘让宽恕永远不得,犯错之人永久桎梏的无限悲哀。
在1925年的叙述中,鲁迅为“风筝事件”设置了一个事实与情感双重意义上的背景——“久经诀别的故乡”。在时空的距离之下,鲁迅所念及的风筝,存在于已经失去的时空之内,这当中不免有对同样逝去的人、逝去的关系的慨叹。在1919年的叙述中,鲁迅同样感到懊悔并且寻求原谅,在1925年的叙述中,结局相同,但是鲁迅在寻求原谅中心境的沉浮有了变化。鲁迅认为偶然看到关于儿童游戏正当性的书是一种“惩罚”,因为它揭露了鲁迅曾经的行为具有不可消除的伤害性,因而这份新的认知却成了不幸的惩罚,这样的表述显示出鲁迅深重的负罪感,这是1919年的语境中所没有的。
最后一处差异的地方在于,小兄弟已经忘记“风筝事件”,原谅无从谈起,而1919年的表述仍在希求原谅,于是结尾是“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9]但在1925年的记述中,鲁迅袒露“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10]。获得原谅只是一种形式,是减轻内心负担的方法,但不是结果,于是鲁迅只能接受永不再有的真正的原谅和恒久、永远的罪感。从“还是请你原谅罢”到“我的心只得沉重着”,鲁迅终于明白了“风筝事件”绝没有一个可能的精神解脱,无论是宽恕还是被宽恕,在个体精神的真实创伤上,都无法做到删除和磨平,这或许隐约暗示着兄弟二人关系的现实结局。于是,结尾便有了深长的意味:“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11]“风筝事件”最后成为真正的“无可把握的悲哀”,因为这是一件处于过去时空的伤害,伴随着事件一方的遗忘和事件另一方的持久回想,是无法弥补和寻求原谅的“无果的忏悔”。
从1919年的叙述中继续寻求原谅到1925年的叙述中确定“宽恕”虚妄,“无可把握的悲哀”的真实,同一事件的两次记述,无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在情感深度上都有了差异,“风筝”已经是悲哀的象征,它一方面是鲁迅在反思自己的行动给儿童精神造成伤害的“证据”,另一方面是兄弟二人关系的象征化、结局性呈现。
有学者认为,《风筝》“以旧作重写的方式创作于周氏兄弟失和不过两年时间,很可能是鲁迅借此向周作人发出的深情忏悔”[12],这样的观点不免带有猜测的意味,因为它指向无法得知的兄弟失和的真相,它预设了鲁迅在失和一事上属于过错方。相较而言,“风筝事件”更可能是对兄弟关系成为“无可把握的悲哀”的伤痛,与其说是代表深情的忏悔,不如说代表着真实的悲哀。悲哀是真实而一定的,但这悲哀是无可把握造成,“无可把握”是因为“无怨的恕不成为恕”。从鲁迅的忏悔心理并不能直接指向它的表述对象是周作人,但是这件事未尝不能视作鲁迅经历1923年兄弟决裂事件后,对兄弟之情由衷的悲叹、哀痛和苦涩。
鲁迅与周作人的绝交信无须再赘述,兄弟二人失和的真相至今也无实证性的结论,尽管学界有诸多猜想以及附在猜想上的似有似无的证据,但更值得关注的,或者说更值得追问的不仅仅是真相如何,而是兄弟二人为何闭口不谈失和的真正原因,为何不做是非对错上的澄清?
在周作人一方,他的绝交信如此决绝,似乎鲁迅犯了滔天大错,在鲁迅一方则是出走八道湾,保持沉默。鲁迅为何不解释?是性情使然,还是真的有一些所谓的“过错”?从周作人的反应和这件事的发酵程度来看,不会是一件单纯的小事。兄弟二人的情绪处境,一方愤怒,一方漠然承受,正义一定站在“愤怒”的一方吗?做一番猜测,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根本解释不清,在一件当时就无法做调查取证的事件上,选择相信何种真实,取决于太多复杂的因素了,这其中有一直以来对一个人的直观感受,有自己的理性分析,有旁人的七嘴八舌,甚至还有无法解释的自己也不完全清楚的内心隐秘。周作人的日记似乎记载了真实的情况,但是那部分日记被毁掉了,所言是否真实,所毁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无从定论。
在鲁迅一方,周作人对他的态度自然打击巨大。鲁迅面对周作人不留余地的绝交信,他作何解释其实都显得苍白无力。周作人在提出绝交的时候,已经在兄弟之情上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已经作出了对鲁迅的价值判断,甚至是道德判断。再论另一种可能,兄弟二人的论辩、澄清,非要争个是非对错,其实比共同沉默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兄弟二人对当时情况都不再解释。但需要承认的是,“兄弟失和”确然发生,1923年下半年鲁迅大病一场,1924年创作《野草》所呈现的精神失序,以及鲁迅杂文创作连续性上的断裂都显示出绝交事件对鲁迅而言是个延宕一生的精神创伤。
三
《语丝》对兄弟二人的链接
与文学道路的分化
《语丝》的创立与周氏兄弟在文学发表阵地上的聚合,带有象征意义,在决裂和分家之后的这一年,兄弟二人竟然在此后各自长期创作的文体上再度聚合,并且随着为《语丝》撰文,二人的文学风格和创作观念又走向分野,显示出耐人寻味的命运感。
周氏兄弟在《语丝》之前一直依托《晨报副刊》作为发表平台。1924年下半年出现的一些变化诱发了《语丝》的诞生,鲁迅《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被新任《晨报》代理总编辑的蒲伯英撤稿,孙伏园与蒲伯英发生冲突,孙伏园不得不另谋新处。于是,孙伏园先去找鲁迅,然后去找周作人,进而联合起北京文化界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决定创办新刊。在1924年10月至11月鲁迅的日记中,记载了孙伏园多次来访的情况,这其中不免包括向鲁迅表达重新开办杂志的想法。周作人在《语丝的回忆》中如是记录:“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13]在顾颉刚、章川岛、孙伏园等人的记述中也说明了当时大家决意一起创办新刊。“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14]尽管第一次聚餐会没有鲁迅,但是鲁迅对于《语丝》的创办,其实也是一个先导的角色。章川岛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一点,也可以证明鲁迅与《语丝》创办之间的联系,并非简单的供稿人:
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在那年(一九二四年)的十一月二日正好是星期天,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次日即由伏园去报告鲁迅先生,他表示都同意。后来又由伏园去联系了几位,就写了一张石印的广告,说这个周刊将在何时出版,是由某某十六人长期撰稿,到各处张贴、发散。[15]
“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人分担”,“次日即由伏园去报告鲁迅先生”,均可看出鲁迅在《语丝》创办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尽管鲁迅说他是一次交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但其实是因为《语丝》之后一纸风行、销路大增,已有盈利,因此不再需要同人出资。在鲁迅的回忆中,有颇具画面感的一幕:“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16]虽然鲁迅从未参加聚餐会,但《语丝》社多位发起人与鲁迅在1924年末往来密切,他对《语丝》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的想法和具体意见,自然会通过孙伏园等人传到周作人那里。鲁迅仍然是语丝社的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周氏兄弟二人在决裂之后,文学上的合作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场景。
《语丝》第一期
在《语丝》第一期的目录中,周氏兄弟二人的名目在决裂之后,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刊物上。《语丝》发刊词后随文第一篇便是周作人的《生活的艺术》、第三篇为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第一期的七位作者中,独有周氏兄弟二人贡献两篇正文。鲁迅此时挣扎在《野草》诸多篇目显示的精神状态中,同时要迈开步子在杂文场中铺展。在《语丝》二百多期的运作中,周作人撰文三百余篇,鲁迅一百余篇;周氏兄弟两人创作的数量远超《语丝》其他同人。尽管此时兄弟二人已“分席而坐”,但在支持、打造《语丝》方面,在与时局做斗争,与现代评论派、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中,两人又是隔空配合,显示出文学意见的一致性。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国内的爱国情绪高涨。周作人以《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讲演传习所》《文明与野蛮》《吃烈士》等文章痛批帝国主义;鲁迅则写下《忽然想到(十)》、《忽然想到(十一)》,以“民力论”和“民气论”来证增长国民实力更为重要。二人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但同时又警醒民族情绪之下的盲目排外。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污蔑攻击女学生和支持她们的教员的“闲话”之后,鲁迅写了《并非闲话(三则)》《我的“籍”和“系”》《“碰壁”之余》《“公理”的把戏》等多篇文章予以回击;周作人则有《京兆人》《与友人论章杨书》《答张崧年先生书》等回应相关言论,行文言辞激烈,直言陈西滢是无耻之尤。“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以《对于大残杀的感想》《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告国民军》《可哀与可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死法》等文反映学生运动之惨烈。而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更是重要的杂文篇目,对军阀政府的残暴行为进行了控诉。当狂飙社的高长虹攻击鲁迅时,周作人写成《南北》矛头直指高长虹。虽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在《语丝》时期文章上的密切配合和观念一致,但二人系列的发声,的确呈现出一种行动上的共同性,尽管这也可以视为文人对时政的应有批判和揭露之态度,但这种撰文和发声的景象,结合兄弟两人刚刚经历的一场重大风波来看,仍给人唏嘘、叹惋的感受。若是放在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的同路“作战”了。
《语丝》时期,周作人的言论仍然表现出了相当的战斗性,但也可以说是最后一点战斗性。对鲁迅而言,《语丝》成为接续《新青年》“随感录”和《晨报副刊》后,鲁迅杂文自觉时期的重要依托阵地,通过《野草》的释放后,开始走向一个杂文的鲁迅。《语丝》北京时期刊登的周氏兄弟的文章,给这段1923年之后的短暂岁月,增加了些许“温情”,兄弟失和的真正缘由无从定论,但是《语丝》上兄弟二人心照不宣的配合,似乎又可以推论,在1923年的事发现场,是否那个失和的原因,根本不涉及道德伦理,仅仅是家庭多年矛盾的累积?但无论如何,《语丝》北京时期的几年,对于周氏兄弟二人,都是一段“隔空”又“并肩”的创作阶段。
1923年,兄弟绝交,二人在生活意义上划清界限,《语丝》北京期间,鲁迅杂文与周作人小品文分野开始。周氏兄弟失和使得在政见、立场、性情、趣味等方面本就不太一样的二人,最终分别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文”的代表。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称:“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17]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颇能看出兄弟二人观念的分歧,周作人等人提倡“费厄泼赖”,而鲁迅则主张“痛打落水狗”。周作人在《谈虎集(后记)》曾表明自己归根结底乃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愿意平凡,主张宽容”,便从十字街头退回书斋。而鲁迅则是头顶“华盖运”,深陷流言和荆棘中寻出杂文写作道路,刻下风沙中的瘢痕。周建人曾回忆鲁迅在上海时期,对八道湾人事的说法: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
他还时常惦念着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是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18]
“万分感慨”“为他担忧”“焦急万分”,在上海时期的鲁迅不免也多次遥望北京,回想八道湾的生活。1923年的是非对错很难分说,但鲁迅与周作人自1923年之后的特殊关系,及两人人生道路的参差,已成文学史上的特殊材料。鲁迅突围到杂文的写作中越发峻急,周作人躲进书斋的文字越发疏世。在杂文视野中观照鲁迅的精神史转折,既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停滞与突围,更可在杂文针锋相对的外在之下,摸索鲁迅潜在的心流,对杂文战场的选择实则有着鲁迅深切人生经验的处理与吸收。
注释
[1]张洁宇:《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2]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
[3]鲁迅:《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4]转引自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5]鲁迅:《<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生活日常》,《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7]鲁迅:《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页。
[8]鲁迅:《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9]鲁迅:《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20页。
[10][11]鲁迅:《风筝》,《鲁迅全集》第2卷,第189页。
[12]王兵:《<风筝>:兄弟失和的哀悼与忏悔》,《西北大学报》2016年第3期。
[13]止庵编:《周作人晚期散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4][15]章川岛:《说说语丝》,《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
[16]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1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18]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项目)“’情感转向’与鲁迅杂文精神主体的重建研究”(2024BS026)的阶段性成果,并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GZB20250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