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墓
江苏 南通
洛宾王墓 江苏南通
来来来,做个小调查,有谁小时候没有背过骆宾王的《咏鹅》?我相信没有。这首朗朗上口的古诗象儿歌一样被大江南北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吟唱,长期“霸占”语文教科书第一首古诗的宝座。
经久不衰的诗句往往用最直白浅显的表达方式,就像现在流行的那句“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法”一样的道理。越是着力于文采用典的诗句,因佶屈聱牙反而不会成为经典。比如白居易写诗就力求平实,把诗写得自然、生活、有趣,一读便懂,走“平民化”路线。
在宋朝有一个才华极高的人叫杨亿,他当时跟一些文人创立了诗歌的流派叫“西昆体”,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西昆体的诗句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多用典故,总之怎么复杂的让你读不懂,就怎么写。后来呢?这么一个大文豪,对现代人来说,好陌生啊!
管家也常常感叹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等,这些诗写得真正好呀,都是嘴边的语言,为什么我就写不出来呢?
说回正题,七岁成诗的神童骆宾王,在他46岁的时候摊上了大事。也许怀才不遇,也许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参与了一场对武则天的讨伐。
话说公元684年,武则天废了儿子李显自立为女皇。这时候一个叫徐敬业(李勣的孙子)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徐敬业曾结识了一个名叫王实甫的道士,王实甫具有较高的道行,且对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在王实甫的鼓励支持下,徐敬业开始策划一场谋反,打着匡复李唐基业为名,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徐敬业请求骆宾王写一篇檄文,于是一篇极具文采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文章写出来了,洋洋洒洒的对起兵的正义性加以阐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二句,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连武则天看了檄文都发出“如此人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的感叹。
结果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三个月就被铁腕女皇平定了,徐敬业与多数逆臣的人生剧本雷同,惨遭杀害。王实甫终不似姚广孝,而骆宾王却像建文帝一样,不知所踪,下落不明,成为历史解不开的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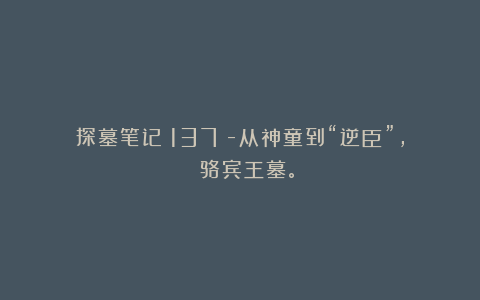
历史上关于骆宾王的最终结局说法很多,大概进行了一些梳理,有以下这几种说法:
1、被杀,《旧唐书》记载的。
2、逃亡,《新唐书》记载的。
3、投水而死,《朝野佥载》,唐代的笔记小说里记载的。
4、灵隐寺为僧,唐《本事诗》,记录唐朝诗人的逸事,记载中还说被宋之问撞见。
5、终老义乌,出自义乌的《骆氏宗谱》。
6、终老南通。源自明末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中。
目前研究骆宾王最权威的是浙师大的老校长骆祥发教授,他不仅是学者,也是骆宾王的后人。据他考证,以上几种说法难以定论,只能说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骆教授认为“南通说”的可能性最大。
“终迹南通说”源于明朝朱国桢在《涌幢小品》里的记载,朱国桢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内阁首辅。他的《涌幢小品》很多篇幅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他在书中记载当地一个农民,姓曹,在黄泥口挖地时发现一个墓碑,刻着“唐骆宾王之墓”的字样,打开棺盖,衣冠如新…..
历史的齿轮又转到了清朝末年,还是那位敛葬金应的名士刘名芳,他在编写《五山志》中无意中读到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里的记载,便去黄泥口寻找,还真找到了一个半字的断石,“唐”字完整,“骆”字只有上半截。
刘名芳请求新知州董权文,效仿前知州彭士圣移金应墓一样,将骆宾王葬于狼山的金应墓旁。也就是说曹姓农民发现墓碑确实存在,并且刘名芳又访得断碑也是事实,这多少为“终老南通说”提供了一些依据,毕竟从扬州逃到南通在地理位置上也符合情理。
这位哙炙人口的大诗人的结局注定为千古之谜。不管如何,骆宾王的文人风骨与金应的忠义刚烈在狼山碧树间交织成坐标,只要有人仍愿为一方残碑驻足,精神便永不寂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