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第一山”,为什么是太行山?
“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地中。”即使你不曾亲临,也定在诗行里听过它的名。
太行山,横亘华北,自洪荒以来,便是屏障,亦是通道。它北接燕赵,南衔河洛,西望黄土,东瞰平原。千年的烽火与生计,在太行的层峦叠嶂间交织沉淀,垒石为阶,凿崖为路,让这座山不再只是一道地理的分野,而成了北方大地的骨骼与魂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部电影《红旗渠》震撼了国人。那劈开太行、引漳入林的故事,戏里是战天斗地的豪情,戏外那悬挂在绝壁上的“人工天河”,便成了民族精神的巍峨坐标。
电影的开篇,是干裂的土地与仰望高山的焦渴目光。随着镐钎与岩石碰撞的火星,太行山险峻的褶皱——鸻鹉崖、青年洞、老虎嘴、分水闸……如史诗的章节,一页页展现在观众眼前。林州石板岩镇的影院里,《红旗渠》的黑白影像反复投射,那锤声与号子,早已刻进太行山的记忆年轮。
太行,古称大形、五行,纵跨京、冀、晋、豫。它耸立于华北平原西侧,如一座陡然升起的、巨大而苍青的城垣。山体多由厚层石灰岩构成,壁立万仞,峡谷深切,因雄、险、朴、拙而闻名于世,素有“天下之脊”之称。它是地理的阶梯,也是无数人用脚步丈量生存与希望的“人生天路”。电影《红旗渠》的编剧,便是被这种“重新安排河山”的壮举所震撼,将太行山人骨子里的坚韧,化作了银幕上不朽的誓言。
影片中,太行山一步一坎,处处是崖壁、深谷、旱塬谱出的生存壮歌。我想,没有哪个人,能不在这种人类意志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感到灵魂的震颤。
走进太行,便走进了石头的国度。群山如怒涛凝固,峰岭如刀斧劈成。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在这里留下最深刻的擦痕。山谷往往是唯一的路,路旁散落着先民开垦的梯田,像给巨人的身躯披上了鳞甲。
在太行山苍莽的腹地,寻一处崖下的村庄,石屋层叠,炊烟袅袅。此刻,生存本身便是最庄严的诗。林州太行大峡谷中的“太行天路”,便是现代人解读这山、致敬这山的精神通道。
坚韧的生存,需要太行沉静又充满张力的自然之景做背景。“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是魏武帝曹操对这山行军艰险的深沉慨叹。太行境内绝壁纵横,水流切出深峡,遇断层则成瀑。虽不及南方瀑布的丰沛,却自有北地旱季的沉静与雨季的奔放。壶关太行山大峡谷的八泉峡,水流在赤壁丹崖间蜿蜒,汇聚成潭,色如碧玉,人称“抬头如峡,低头如沟,一步一景,如梦似幻”。
太行山间的溪泉,在低洼处汇成少而珍贵的湖。平顺县的通天峡景区,一池碧水嵌于赤壁环抱之中,犹如大山珍藏的一滴眼泪。
而太行最为人称道的“胜景”,往往与“关”相连。河北涞源与山西灵丘交界处的驿马岭,山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人们驻足于此,既能感受太行如铜墙铁壁的屏障之险,又能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烽烟传讯的岁月流光。
太行山巅的板山,是观赏太行群峰“胜似海洋”的绝佳之处。俯瞰下去,千峰竞秀,万壑深藏,云雾来时,山峦如岛礁浮沉,确能体验陈毅元帅笔下“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地中”的浩瀚气象。
与雄险相映的,是太行秋日的暖色。涉县娲皇宫旁的核桃林,柿子林,在秋天挂满果实,一片金黄赭红。梯田上的庄稼已收,留下整齐的田垄,像大地的五线谱。
昔阳大寨的虎头山上,秋叶斑斓,松柏苍翠。山坡上那一层层用石头垒起的田埂,不仅是土地的保障,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邢川前南峪的漫山苹果树、板栗树,秋实累累。那红艳与棕褐,是秋天太行最丰腴的馈赠。这些果实不仅点缀了山野,更是山里人生活的滋味,捧一把栗子,便能嚼出大山的厚实与甘甜。
这么一个镌刻着生存史诗的地方,早就是千百年来历史车轮反复碾过的“雄关漫道”。
《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其精神源头,或许便来自太行、王屋二山的巍峨与不可撼动。关于它的命名,“太”者,大也,“行”者,山脉成行。它横空出世,分割东西,行走其上,何其艰难,故曰“太行”。
帝王将相对这战略要冲无比重视,历代征战、迁徙、商旅的足迹,深印其间。
东汉末年,曹操北征高干,行军太行,留下《苦寒行》的苍凉诗篇。两晋南北朝,天下纷乱,太行山因其闭塞险峻,成为坞堡自守、流民避乱的天然城池。其中,“扼太行之麓,据天下之肩”的井陉关,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衰更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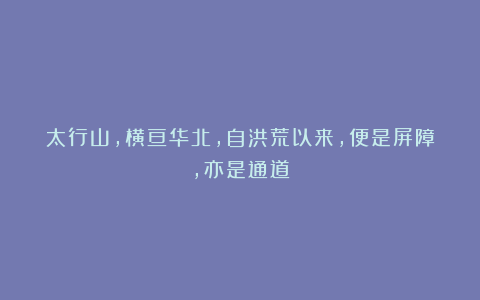
山石虽无言,却记下了最深重的车辙与蹄印。唐代,郭子仪、李光弼曾藉此山之势,东出平定安史之乱。太行,是沉默的卫士,也是历史的通道。
山崖之下,不仅有兵戈,也有香火。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信徒们看中了太行山崖的坚固与清静,凿石为窟,礼佛修行。
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浚县大伾山摩崖,便开凿于这个时期。一时间,晨钟暮鼓在峡谷间回荡,与兵营的号角此起彼伏。多样的信仰在岩壁间生根,太行开始不仅是军事天堑,也成了儒将戍边、僧侣修行、百姓祈福的混杂之地。那些石窟中的造像,历经风霜,面容静穆,仿佛山魂的另一种呈现。
唐宋以降,无数文人墨客行经太行,留下的多是行路难的嗟叹与对雄浑山色的震撼。李白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是仕途坎坷的隐喻;白居易的“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是世路艰难的感慨。
他们将人生的行路难,与地理的太行之难交织,赋予了这山深厚的人文情怀。
终极的行者,或许是那些无名的商旅。他们牵着驼马,组成“驮帮”,沿着隋唐以来开辟的“太行八陉”,在仅容一车的羊肠坂道上往复,沟通了高原与平原的脉搏,运去了煤炭、山货,带来了布匹、食盐。他们才是太行山真正流动的血液。
然而,太行山最深刻、最悲壮也最辉煌的篇章,书写在近现代。
当烽烟再起,它又一次成为庇护所与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因其地势,成为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天然堡垒。不是别墅,而是窑洞、石屋、山崖下的兵工厂,散落在它的千沟万壑之中。
一场艰苦卓绝的“山地生存与抗争”拉开了帷幕。八路军总部曾长期转战于太行山区,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这里运筹帷幄。太行山,从历史的通道,一跃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脊梁。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到过太行山区,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记录了这里军民的顽强。她的笔下,太行山不仅是地理存在,更是中国人民不屈精神的象征。
“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这首诞生于此的战歌,响彻山谷,其激扬的旋律,便是那个时代太行山的“最强音”。
如今,在太行山深处,仍可见到八路军兵工厂、医院、银行(冀南银行)的旧址。黄崖洞兵工厂遗址,位于黎城县赤壁千仞的峡谷中,地势之险,一夫当关。这里的建筑依崖而建,石墙犹存,默默诉说着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创业史诗。
武乡县的王家峪、砖壁村,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朴素的农家院落里,陈列着粗糙的马灯、泛黄的地图、简易的电台。正是在这些石桌土炕上,决定了华北战场的许多重大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太行人那种“劈开太行山”的精神并未褪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伟大的工程莫过于“红旗渠”。为结束十年九旱的苦难,林县人民用十年时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硬是开出了一条生命之渠。
青年洞,是其中最为艰巨的工程之一。三百名青年突击队员,用一年零五个月,在坚硬的石英岩上凿出了这条长达616米的隧洞。洞内岩壁上的凿痕,至今清晰如新,那是意志战胜岩石的铭文。
如今,行走在红旗渠的岸上,脚下是滔滔清水,身旁是万仞绝壁。你会看到“老炮眼”、“铁姑娘打钎”的纪念点,看到那简陋的工具展览。纪录片《红旗渠》在纪念馆里循环放映,那黝黑而坚定的面孔,那震天的号子,依然能让今日的瞻仰者心潮澎湃。
为什么是太行?
它可不止是“人工天河”创造的世界奇迹所带来的光环。太行,能让你体会“我在太行深处等你,看那星河垂落于峡谷”的苍茫,但你真正走进它,它的内核是石头般坚韧的生存意志,一探究竟则是回荡千年的金戈铁马与改天换地的呐喊。
千百年來,人们经过太行,铭记太行,不仅是因为它定义了北方山河的雄浑气象,更是因为它骨子里镌刻的“生生不息、刚毅不屈”的生命信条。这信条,比山石更古老,比渠水更绵长。
寄长风而叩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