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小时候没听过“泰伯让国”的故事——兄弟三人,老大老二看出父亲偏心小弟,于是俩人一合计,干脆远走他乡,成就了千古一段“至德”美谈。可年纪渐长,读了几本闲书,也见过几场家长里短,人难免要犯嘀咕:泰伯他真是在让位,只为弟弟好吗?还是那一大家子,其实水比咱们想象的要深?
翻回到三千年前,西北那片地,古公亶父带着家族一路折腾。他们从豳地赶到岐山周原——当时的天气据说挺凄凉,哪里不是风沙满天。你说古公一家怎么这么有本事,能在周原扎下根?这不是随便一块净地,哪能轮着让他进来耕个田建城。这地方早被别的势力盘踞着呢。外头看着像自个儿“移民创业”,其实更像搅进了一锅粥。谁动谁,谁让谁,明面上没人说得清。
最有意思的还得数家族里的“联姻大戏”。古公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一个老婆。老大泰伯是正妻生的,仲雍也是,可季历呢?弟弟季历的妈妈太姜,身份比别人高半头,羌人来的,不是泛泛之辈。甲骨文上姜字,专指那边的女人。想来,为了周人的安危,古公娶了太姜,就是想拉着羌人做靠山,家族更稳。
呐,还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季历娶的太任,出身商朝,家里背景硬到没朋友。换句话说,古公这步联姻棋,把羌族、商朝全揽进自己阵营。一句“你家亲家就是我家后盾”,周原这块地说不定早已有说不清的关系网。你说人家能在乱世立得脚?还真不是单凭“德”那么简单。
史书上老写古公宠爱季历,“因为他贤”,都一副尊贤让能的调调。可你真信当权老头选继承人只看“能耐”?在那年月,母亲的来头,老婆的身份,才是真正决定下一步往哪走的硬道理。季历母亲在羌族说话,老婆在商朝脸上有光,古公选他继位,说白了也是逼上梁山:你有这背景,不选你,家族哪还有安生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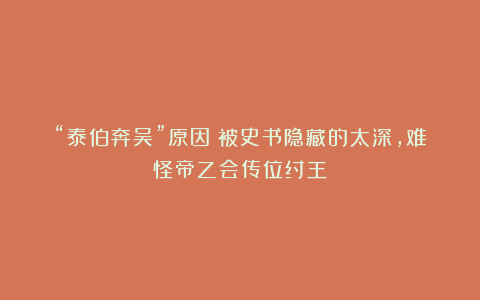
而老大泰伯呢——听着风光,其实同样有点无奈。要是不肯走,兄弟间非搅成乱麻,家门口都不消停;一转头,远走江南,算是自认下场。一边是“大德让贤”的赞歌,一边是权势之下的温情无奈。后世的孔夫子把泰伯夸成“至德”,可能也是说,他心里能承一段“割舍”,不是谁都做得来的。
这些家事还就带点时代的意味。到了季历,也算是家族势力攀到顶尖。季历取了商贵太任,生下了姬昌,就是那个后来名垂青史的周文王。要说这孩子有出息,靠的不是个人努力——不如说,是因为身上血脉里藏着羌人、周人,商人三家名份。周族想出头,得先圈定自家在名门望族里的份量。季历加太任,生姬昌,这搭配怕是周人前后谋划的结果。
至于“传位”这事,也不全让人那么唏嘘。所谓“子凭母贵”,后头可有讲头。姬昌往下再传,前妻太早去世,后娶了太姒,连着生了伯邑考、姬发、周公那一代。结果,嫡长子伯邑考没等接班就早早撒手人寰,传位姬发,又成一桩子凭母贵的故事。再下一代,姬发的儿子周成王,母亲还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都是“门当户对”设的套,传嫡不传庶已经成了规矩。到这一步,家族大事不靠贤良,就靠母家后台。“贤”是真是假,留给后人作史诗,现实只认势力和出身。
再跳到商朝,也都差不多套路。史书上说帝乙选微子启和辛的时候,为啥微子启没戏?因为他娘家寒碜,身份不够硬。辛(也就是纣王)生母正后,才捞到皇位,“子凭母贵”变成硬道理。表面看纣王像是钻了空子,其实哪有侥幸。在那个年代,传位哪个不是照着嫡母来的?这规矩早就被商朝定下,还轮不到谁说“贤者居之”。周人向商朝低头,传位也照搬了这规矩。季历能接班,纣王能作王,一切都在“母家”的权重里暗自安排。
那么,“至德让天下”,到底是真是假?人说泰伯避贤走吴,怎么看都像美谈,可你真细想,谁家兄弟不是绕不开父母、外家那点羁绊。风雨飘摇的时代,太伯或仲雍,只是朝代转折下的一角。能不能继位,无非是家族权势、联姻安排的折射。也许有一刻,他们自己也在问:这一切,到底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裹进大势、无力挣扎?
所以历史小说里那些“千古道德”,多半写给后人看的。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可那时候的家,兴衰成败,早就不是一家几口说了算。母贵、妻贵、联姻、权衡,都在一点点把家族推向另一个时代。至于贤德与否,也许只有当事人才分得清。
讲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多说一句。泰伯让国,季历得位,这些故事被写成典范,也让我们想象历史里每一句赞美都是真心。可你要是坐在周人当年的泥地房里,恐怕会更关心明天能不能活下去,儿女是不是能有个安稳。褒贬也好,传说也罢,权势之下,人心自有苦乐。留下的道德名声,也许只是无数个家庭风雨里最温柔的谅解与退让吧。
至于“子凭母贵”,是不是最好的做法?换做你我,未必会有更好的选择。转头再想,当年那些兄弟们,谁不是在权势裹挟下,悄悄地问过一句:“这一生,我能为家族做些什么?又能为自己留下什么?”故事说到这,留下一点未尽的话头,也许正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