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钟摆停下,时光已经掠过了八十年的厚度。她姓鲍,名蕙荞,虽然谈不上人尽皆知,可钢琴圈里无人不识。她的名字,从五十年代的课桌传到了2024年的琴键。她被叫过天才,也被呼作受难者,又成了坚韧母亲,还一度成为名人轶事中的配角。这一生,简直像被时代拉着跑,没让她歇过气!
纵然这样,有人记得她和庄则栋曾经是最被看好的“金童玉女”?文体圈顶流的爱情,又怎么落到如此平常?她和庄则栋结婚的时候,婚房只有十几个平方。钢琴女神和乒坛新星,白纸黑字高调联姻,舆论场上风头一时无两。可没多久,疾风骤雨随之到来。鲍蕙荞的家庭出身太“洋”,钢琴太“西”,丈夫被卷进浪潮成阶下囚。她自己差点被打倒。那些年,外人看不到的苦日子,是她捱过去了。也许运气有点意思,总在最不想要惊喜的时候出现哟。
鲍蕙荞1940年生在四川犍为县,家里学问气息浓:父亲鲍国宝是搞电力的专家,母亲也读过不少书。光看这个家庭,孩子至少也要学一样特长。家里搬来搬去,最后母亲一咬牙给家里买了架德国旧钢琴,家境算不上多宽裕,倒是胆子挺大。她还没满十岁,琴键边杵着的不是糖,而是一根小木棍。老先生教琴严厉,弹错就敲一下。她不服气,弹得越发努力。三年下来挨了两下,谁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呢?
不凑巧也不巧,鲍蕙荞学艺很快就小有名气。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她赶上末班车,批条、政审、考试全给免了。这种特殊待遇,要搁今天网络上说就是“开挂”,可她那阵只觉得自己幸运。进了学院读书,早晨天还没亮和同学跑步去练琴。家庭负担不轻,钢琴也不是她唯一的兴趣,本来画画、滑冰都不错,公司都想揽她。但她咬牙坚持,音符成了唯一出口。
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推荐她去维也纳参赛。钢琴背后的故事没那么美好——飞机票报销,生活费紧巴巴,衣裳还是母亲临时缝的。只要能把琴拉出去就行。结果,人还真不怯场。现场,她弹的《致爱丽丝》、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曲子,三十年后还有乐迷在回忆。谁当时能想到,这一场比赛会跟乒乓球扯上关系?代表团里那一年没多少人认识庄则栋,他那会是个一身阳刚气的小伙儿。两人坐飞机时隔着过道聊天,彼此没什么火花。谁会料到,后来风风雨雨牵扯这么深?
回北京后没交集,各忙各的。庄则栋几年后才彻底打出名堂。196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一出,他一夜成名。那一年,也是鲍蕙荞在乔治·埃涅斯库国际赛拿奖回来,内心有些说不出的得意劲。这样看来,两人算同龄同成名?又不太像,也许只能说命运碰巧。
1962年冬天,上海一场文体联欢,鲍蕙荞遇到庄则栋——不是正式场合,更不是设局的相亲。庄则栋在一旁玩闹赢了个玩具小汽车,不知怎么就送给了鲍蕙荞。没多久鲍蕙荞反写信给他,信里没告白,全是家常。关系是这样一封封信写出来的。写信总是慢热,她其实不太能搞清自己的依赖从哪来。
1964年,庄则栋的球队不同意主力结婚。事业大于一切,这在体育圈很正常。鲍蕙荞忍了下来,直到特殊时代全来临,钢琴也不能弹了,丈夫也受打压。那段时间,鲍蕙荞成了众矢之的,钢琴曲只许弹《红旗颂》。庄则栋被批修正主义,她挺着孕肚挨批斗。她没撂下丈夫,哪怕一屋子人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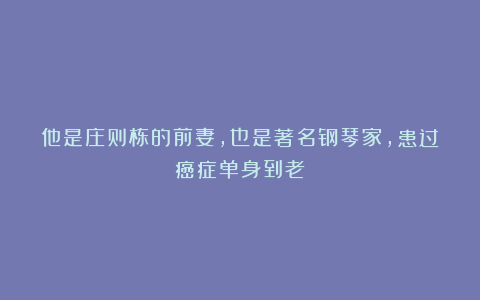
生活也没什么传奇。1968年生下儿子,身边全是家人帮忙。七零年丈夫解禁后恢复比赛,她才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日子。1974年庄则栋被提拔成了国家体委负责人,全家浮出水面。鲍蕙荞没见过这么大的官架子,反而觉得不自在,只渴望安稳生活。两个人理念不一样?也不是,就那样臭味相投又多少不对劲。
生活并不会因为他们著名就回避摧残。几年后庄则栋又陷入风波,进了看守区。鲍蕙荞不离不弃。有人劝她快离婚,她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给丈夫寄吃穿,还得顾着缠足老太太——谁想过有一天苦难这么密集?丈夫偶尔自杀,她连见面机会都没。一次又一次站在邮局窗口,她把安慰藏在小纸条里。那阵工资不高,孩子都靠她。
1978年父亲离世,鲍蕙荞一夜白了头。她也没软下来,到1980年重登舞台。所有情绪一夜迸发,是演出结束后独自的崩溃哭泣。你说世界公平不—没了家庭,有了舞台;事业有起色,婚姻破裂。
两人复合过几次,不冷不热。丈夫出狱后调去外地,她留北京,一切都很清淡。职场内部,流言四起,多少年过去还是觉得委屈。不过忍也就忍了吧。到1985年两人彻底分开。鲍蕙荞带一双儿女,工作忙得没空抬头。说到底也怪现实,离婚后的她受冷遇,带孩子再婚难。而庄则栋再娶,娶了个日本女人。全国好事者都在等后续,她却没什么可说。
鲍蕙荞拼命抓住每个露面的舞台。手腕骨折刚拆石膏就登台——有人说她拼命,其实没别的法子,守不住名声守住饭碗也行。她出书、搞乐团、教琴、组织活动。随便一件事拿出来也得多年积累。
2006年查出乳腺癌,儿女抱着她哭成一团。她没慌乱,也许被噩耗劈怕了,倒没那么绝望。手术拿命硬抗,医院里七个小时,她自己也记不清多少次昏睡过去。等到病愈,她跑去西班牙当评委——外国钢琴比赛,她就仿佛又活一次。七十岁比年轻时更忙:巡回演奏、学画画、跑各地参加讲座评审。有人说她折腾自己,有人觉得是真正的释放。2020年鲍蕙荞在北京享清福,儿女事业稳定,房子、资金不缺。她自己阳光、安静、能吃能睡。
但回过头想,鲍蕙荞不是那种一味坚强的人。她很多次也后悔过、犹豫过,外人看不见。庄则栋临终,儿女送别父亲回来,她眼泪也止不住哗哗往下掉。半生恩怨,很多已经忘了,说原谅,那是假的,说不放下,也不可能。她和庄则栋这段关系,说到底更像一场合作社,不是哪种小说里的宿命。谁都没撑过天大的风浪,但却各自站起来了。这算不算人生赢家?也许,鲍蕙荞自己根本就不关心。
晚年鲍蕙荞身体硬朗,常跟朋友聊家长里短,偶尔指点琴童弹琴走音。她没再婚,她没解释过理由。她说,儿女都很好,够了。
都说苦难砸来之后的平凡才最金贵,对鲍蕙荞来说,大约就是如今这样:家人在侧,手边还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日子一直往前。什么时代留下的后遗症,也就让它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