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届冬日,亚热带气候令台北依然温暖宜人。钻石结构般环抱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之中,一股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正在蔓延。几位年轻女演员担任“最佳剪辑”奖的颁奖嘉宾,她们缓缓念出了获奖者姓名:“《隐迹之书:重写自我》,雪美莲。”雪美莲一身长裙、丝巾飞扬,潇洒地走上台,接过了她的第一座奖座。她先是用国语感谢评委对她的肯定,“此次回到亚洲来领取这个奖,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年过七十还能够在华语世界获得大奖”,然后用母语广东话感谢了老师、合作伙伴和家人。并没有动情落泪或激动语塞,正如《隐迹之书》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一般,这位已经在电影行业成为教母级人物的女性创作者在不同语言中跳跃,始终保持着一种轻快的节奏。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仅仅二十分钟后,她便再度上台,领取了“最佳纪录片”奖。当《隐迹之书:重写自我》脱颖而出时,雪美莲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平静,甚至幽默地讲起俏皮话:“实在没想到又是我得奖。我刚才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监制多说几句吧。”
这种轻盈自如的气质在我们与她相约采访时就已经显露无疑。颁奖礼当天的下午,我紧张局促地在电梯口等待雪美莲导演,她却在见到我的第一刻就与我热情握手,又在我主动提出可以用广东话进行访谈时开朗大笑,说十分感谢我让她能够在母语里更自在地表达。一时间,我好像忘却了这是一位从影四十年、经验老到的前辈,反而感受到一种慈爱的、祖母般的亲切。
也正是这种轻盈与亲切,让《隐迹之书:重写自我》这个私人家族史的故事如此动人而普世。这部电影从作为一个华人却拥有“Mary Stephen”这样的外文名,自己到底是姓“雪”、姓“陈”还是姓“Stephen”的疑惑出发,将大量家庭私人影像与日记手稿的材料组织起来,以挑逗而反叛的女性主义口吻,探索了纪录片中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完成了对中国近代殖民史的一次极具个人色彩和价值的重述。正如她的其中一个姓氏“陈”的中文含义一般——可以是“old and past”,也可以是“tell a story”,这个移民故事完全没有落入血缘主义家族寻根的老套叙事,而是通过真诚而深刻的自我剖析,最终实现了对自我认同的审慎回归。
以下是凹凸镜DOC记者同泽专访《隐迹之书:重写自我》导演雪美莲的内容:
摄影:张万利
她是侯麦御用剪辑师,最新纪录片作品斩获两项大奖
采访、校对:同泽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在介绍您时,许多人会使用“侯麦御用剪辑师”的头衔,您怎么看待这种描述?有没有哪些特质被您从与侯麦的长期合作中带到了新作品《隐迹之书:重写自我》(以下简称《隐迹之书》)里?
雪美莲:我觉得这个头衔是一种荣幸,毕竟能有几个亚洲人有机会与这样伟大的法国新浪潮导演合作?对于当时初入电影行业的我,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在我与侯麦的长期合作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如何把握电影的节奏。我与侯麦都很喜欢音乐,我也参与过一些电影的音乐制作,因此在电影后期制作时,我们常心有灵犀地觉得,在这里停下来节奏最好。曾有人评价过我的剪辑风格非常果断(cut),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种风格可能也正是由此而来。
凹凸镜DOC:剪辑师、音乐制作人、导演,这三重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作用的?会互相影响吗?
雪美莲:首先我想澄清一点,可能因为受到实验电影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影响较深,我一直以来都更喜欢用“filmmaker(电影制作人)”来描述自己,而不太喜欢使用“导演”这个概念。我认为完成一部电影不单止依靠导演个人的努力,而filmmaker这个概念可以涵盖摄影师、剪辑师、配乐师等等,更强调电影的集体工作成果属性。例如,作曲家Suzuki桑为《隐迹之书》创造了非常动人的配乐,并且全然信任我来把这些作品重新剪辑成更实验性的样态,我认为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巨大牺牲,非常感动,所以觉得需要着重强调每个创作者对电影的参与和贡献。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以前在做剪辑师的时候认为,剪辑能够揭露导演在创作中自我审查、不愿暴露的事情。但当我的主要工作从剪辑变成导演后,我也陷入了一种很典型的自我审查,不敢表达太多观点,仿佛要把自己隐藏在前人观点和文学表述之后。因此我聘请了一位剪辑顾问(editing consultant)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他重审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给我提了很多建议,在我自我质疑的时候鼓励我,并且逼着我直面自己的内心——这个过程与我当初教别人要直面内心完全反过来了,我自己也变成了与自我审查作斗争的人。
凹凸镜DOC:在法国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近二十年的工作重心又转回了香港和中国内陆,在这几个不同的地方工作,您会感觉到电影产业和文化的差异吗?
雪美莲:我在香港主要是做娱乐性较强的剧情片的剪辑,而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北京开始与杜海滨导演合作,主要是做纪录片的剪辑。这两种工作有非常大的差异,纪录片剪辑工作相对独立,而香港的工作则更多是在电影的工业体系里发挥作用。但我认为我非常幸运,在香港与许鞍华等诸多名导合作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尊重我工作的独立性,并不会对我施加商业电影一定要挣钱的压力,所以始终我的工作都是相对独立的。
凹凸镜DOC:游走在法语和华语之间进行电影创作,您有什么感受?
雪美莲:其实我非常喜欢把语言作为电影的一个创作元素。我曾在九十年代制作过一部关于南非作家Breytenbach的纪录片,电影名字叫《Vision from the Edge: Breyten Breytenbach Painting the Lines》,中文名叫《边瞳》。在这部电影中,我将这位作家所有翻译过的诗歌的不同语言版本织成了一个音乐一般的文本,这更让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并且同一个概念用法语和华语讲述出来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有的内容你在这种语言里可以表达,但是换了一种语言就不知道怎么讲述。法国人表达感情比较直接,所以法语相对比较外露;但是亚洲人则不太会用语言表达感情,所以华语就相对比较内敛。
凹凸镜DOC:让我们说回电影本身。《隐迹之书》是一个关于名字(name)和身份认同的故事,您在影片开头使用了梁秉钧《我们带着许多东西旅行》里的诗句作为题记:“我们带着种种奇怪的东西前行。我们带着白天来到黑夜,带着东方来到西方,带着自己来到他人。”为何选择这句诗?
雪美莲:这个选择的过程非常有趣。其实我尝试过许多外国文学的句子,但最终都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就有人和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回自己的语言、听听华人的声音?梁秉钧其实是我的朋友,他送过我很多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纪念他的好机会。并且,我真的觉得这几句诗非常贴合我的心情,也很契合电影的主题,所以最终决定用这几句诗作为题记。
凹凸镜DOC:英文片名“Palimpsest”的原意是古代石板上被刮去然后又重新刻下的文字,后来也被延伸为“历史被重新讲述”。您是怎么选中这样一个极富文学性的词汇作为片名的呢?
雪美莲:“Palimpsest”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法国去过的一个书店的名字,当时我也不认识这个词,有个朋友给我解释了这个词的含义我才明白。其实我也考虑过要不要在电影中做一下名词解释,但后来我觉得,只要观众有兴趣自然会去搜寻这个词的意思,所以无须多言。我觉得我爸爸改名完全就是一个“Palimpsest”,他把自己原本的名字改掉,然后再重新书写自己的故事。此外,还有一重含义在于,我有一半的人生都在与Éric Rohmer共事,但其实Éric Rohmer也并非他的真名,所以我觉得使用这个词汇作为片名有一种命运的感觉。
凹凸镜DOC:中文片名“隐迹之书”又是如何决定的呢?是您自己的翻译吗?
凹凸镜DOC:在电影中,您将个人名字渊源的探寻与Virginia Woolf、凌叔华等知名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联系了起来。在您意识到自己的家族历史居然可以和这些名人、甚至是整个中国近代殖民史产生勾连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
雪美莲:其实从产生这个电影构思,到最终完成制作,中间经过了二十多年。最初开始这个构思的时候,我只是当成一件好玩的事。在我发现Virginia Woolf的本姓是Stephen(而Woolf只是她的夫姓)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怎么能够把这个故事和我自己也姓Stephen连起来。实话说,一开始发现自己的家族与 Virginia Woolf有关系时,我相信所有华人——可能尤其是香港人,都会有一种非常崇拜的心情,因为当时我们都特别喜欢英国文学,而Virginia Woolf又是那么举世知名的英国文学家。
然而,在四年前法国的24 Image公司开始参与制作的时候,这个故事就越来越大,不再只是Virginia Woolf的奇闻趣事,更变成了一个外国人与中国人如何交流、产生误解的故事。我阅读Virginia Woolf与她的外甥的书信,看到里面的口吻非常高高在上,甚至有一些种族歧视的字眼,其实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即便如此,在我最后回到法国南部她的故居时,依然还是觉得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人性就是这么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都讲得太过干净、非黑即白,其实与人性是矛盾的。
凹凸镜DOC:《隐迹之书》这部电影是基于您父母留下的大量手稿、影像资料完成的,以个人家族史的角度讲述国家近代史,这种形式让我联想到齐邦媛的《巨流河》。有一种文化批评认为:只有掌握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人才有能力保存和书写自己家族的历史,能够重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特权。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雪美莲:其实我爸爸的日记一共有一百多本,我只看了很少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些材料最宝贵的特质在于它们写得非常详细,而且他每天都写,如同连载一本小说一般。我觉得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职业,他们那一代人对于建构原始材料(building materials)有一种别样的关怀,而我作为下一代人就没有这种经历了,只能进行一些整理工作。所以我觉得这种记录并不是一个孤例或者特权,每个经过岁月生涯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故事书写下来。归根结底,我觉得和那个时代有关系,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历史的动荡,而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所以写不出这样的内容。不过如果我们要写,有没有自己的故事可以书写呢?我觉得也是有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故事,也可以让自己的故事成为读者的阅读对象。我一直都对别人的故事很有兴趣,因为每个人的故事有值得观看的部分。
凹凸镜DOC:除了整理、组织这些真实材料,您在电影中也有一些使用虚构材料的小巧思,例如最后Virginia Woolf的故事和您的家族故事的连接,其实是用一封伪造的书信来完成的。您如何理解纪录片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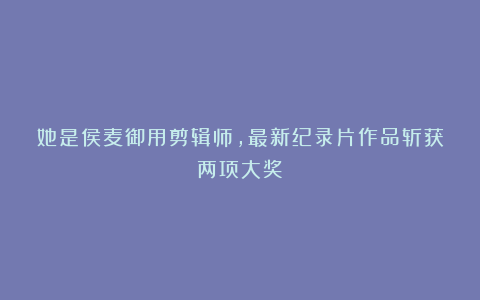
雪美莲:在法国巴黎有个纪录片电影节,叫“Cinéma du Réel”(Cinema of the Real,真实电影节)。这个电影节里的纪录片有许多是实验电影,甚至有很多材料是直接虚构的。我认为在当下,真实与虚构的极限本身就越来越模糊,如果材料都是真实的,但是讲述时经过了编排加工,这样的电影还能不能算作real cinema?real cinema又是否是纪录片(documentary)呢?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也在做这样的研究,而我也在故事片(fiction)和纪录片(documentary)之间不断进行探索。
在我没有开始制作纪录片时,我以为“纪录片”这个概念是很封闭的,甚至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自己也曾见识过“拍纪录片的人觉得拍故事片的人很俗气”的事情。但是后来我慢慢觉得,纪录片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其实每个纪录片都有自己的观点表达,许多材料也是可以被篡改(manipulate)的。所以我觉得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始终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研究的问题。
凹凸镜DOC:在电影中,您也自己揭露了,这封您妈妈与凌叔华的通信其实是您那擅长书法的儿媳伪造的。这个设计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吗?
雪美莲:虽然早就想好了要把这两个故事连接起来,但是这个连接方法是最后才想到的。其实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是一边做一边才发现的。例如Julian和凌叔华最后的约会在香港,这个事实是近年的研究才发现的,我二十多年前开始研究家族史的时候,这个史实还没有被发现。当然,现在在互联网上你几乎可以发现任何事情,但是这种曾被历史掩埋最后又重见天日的情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于是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把我妈妈的故事连接进去,最后想到这个伪造一封书信的方法。我的儿媳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也会自己写诗,我想到这个方法后和她一拍即合,就完成了这个设计。这封信的内容是她自己创作的。
凹凸镜DOC:这个设计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表达吗?您在电影里提到历史上很多女性的名字是被隐去的,所以要用一个反叛的手法来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女性的名字被看到。
雪美莲:我觉得确实是女性主义的,不过女性主义内部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部分,所以我倾向于做一种更含蓄的表达。在电影中有一次场戏是我妈妈去沙滩上散步,我在旁白中对她提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疑问:你自称是新女性,但是你和Virginia Woolf两个新女性,一个将石头装入衣服口袋中投河自杀,且无论是生前身后都一直被世人用夫姓称呼,而你一辈子都未能发扬自己的写作天赋、写出想写的作品。许多如此天才的女性,希望追寻女性主义的生活,但是却始终未能达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深切的遗憾。
凹凸镜DOC:您在电影里提到了红皮书和黑皮书两个版本的故事,前者是因为看到祖国破碎、人民流离,愤而放弃国籍的历史创痛叙事,后者则是寻宝书一般的存在,包含了很多暧昧情愫和美丽故事。在这两个版本的叙事中选择的时候,您做了什么设计?
雪美莲:其实在这两个版本之间,我也做了一些叙事的编排,把它们砌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个关于民族历史创痛的故事,在我早年回南京探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反而武汉部分的探索是后来才发生的。但是在电影中我把这个叙事顺序调转了,先讲述了武汉的故事,然后才是回南京探亲时五叔给我讲述爸爸改名的真实原因。我觉得在叙事上,更戏剧化的部分应该要放在最后面,这样才会更打动观众。这种讲法在感情上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个好奇的人一路探寻历史,最后发现真相和民族的历史创痛有关。不过说到底,五叔的故事版本也是我爸爸讲给他听的,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其实也永远无从得知了。
凹凸镜DOC:如果只看电影简介,许多观众会本能觉得这是一个老套的移民寻根故事。对于这部分没看过电影的观众,您会怎么样和他们澄清这并不是一个老套的寻根故事?
雪美莲: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在大众面前放映,我以为只是像和一个好朋友一边喝酒一天聊天的小众放映,可能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我设计了许多旁枝叙事(side track)。如果要让我和观众介绍,我想我会和他们说,请你们和我一起忍受一下(bear with me),慢慢看下去吧,看到最后你就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凹凸镜DOC: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觉得姓氏(family name)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
雪美莲: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生。一开始我以为Stephen是假名,本来都想弃之不用了,但没想到我女儿却真的去市政厅把自己的孩子改姓为Stephen,所以这个姓氏就被沿用下去。而关于“陈”这个姓,我在故事最后找回这个姓氏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而我的前夫是柬埔寨的华人,他竟然真的姓陈!所以我的孩子又确实早已成为陈家人。
所以最后的最后,如果你问我姓氏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会说姓氏对我是不重要的。我哥哥在世的时候,对自己姓什么这件事非常耿耿于怀,但是我现在完成这部电影以后,最想和他说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安息,姓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凹凸镜DOC:这部电影有八成以上的旁白是用英语讲述的,只有部分原始材料使用对应语言进行旁白,这是怎样的语言选择?
雪美莲:其实一开始我就想好了要用英语写这个故事。我的母语是广东话和英语,我小时候确实是说广东话比较多,不过后来我说英语更多,写作也是用英语。这部电影我们也有想过要不要做法语版和广东话版,但后来发现故事里有很多文学的部分是没有办法翻译的,所以最后就没有制作其他语言的版本。
凹凸镜DOC:用哪种语言来讲述是否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选择?
雪美莲:是的。有很多人会问我用什么语言来做梦,我觉得取决于我睡觉之前和谁在讲什么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的是一个有多重身份认同的人(multi-identity)。
凹凸镜DOC:《隐迹之书》已经在多伦多和台北完成了多轮放映,您觉得这个关于华人移民的故事,在多伦多的英语环境里和在台北的华语环境里,观众的反应有区别吗?
雪美莲:我只来了台北几天,目前为止我的感受是台北的观众看得更明白。第一轮放映的时候我还没到台北,但是已经看到有很多影评文章对我们的电影分析得非常透彻,多伦多的观众相对而言就理解得没有那么深刻。虽然多伦多也有很多华人观众,但是可能他们已经与加拿大的白人社群融合得太紧密了,所以就没有太注重这部电影里更深层的东西。我很好奇和期待如果这部电影到香港和内陆去放映,观众会有怎样的反应,也希望明年有机会带着这部电影去香港和内陆。
凹凸镜DOC:最后请您用一句话向大陆观众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吧!
雪美莲: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故事,我希望观众们也会有好奇来看看我这个很不寻常、但又很普通的故事。
《隐迹之书:重写自我》
导演: 雪美莲
类型: 纪录片 / 传记 / 历史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 法国 / 中国香港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英语 / 法语
上映日期: 2025(中国香港) / 2025-09(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片长: 108分钟
又名: Palimpsest: the Story of a Name
影片介绍:资深剪辑师雪美莲,总纳闷自己到底姓史蒂芬,还是姓雪、姓陈?明明亚洲脸,又非混血,怎取洋人姓?一查不得了,父亲竟来自澳洲!母亲曾有文学梦,似还牵涉弗吉尼亚·伍尔夫侄子的中国恋情?她化身侦探亲自执导,翻找父亲传记、家庭电影、老照片,以“史蒂芬”为圆心,拼出一幅与世纪风云、名人交织的私密家族史,追问殖民与身份认同。血缘缠如网,个体仍能重写自我,乘故事翱翔。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