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这位开国上将,一个被称为“山东双雄”的硬汉,在1980年7月25日离世了。整个走的过程,可以说是低调到家了,家里悄无声息地办了身后事,连那些曾经肝胆相照、刀山火海一起闯过的老战友都没露面。
你说奇怪不奇怪?一个在战场上号令风云、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怎么到了世界另一端就变得这么冷清呢?
想当年王建安带兵打仗,那可是声势浩大,风风火火,敌人还没摆好架势,他的部队就已经攻城掠地了。到了1956年,人家还特意给他单独授衔,这足见他在军中的地位有多高。
可谁知道,这位一生戎马的硬汉,到头来却是孤零零地走了,连个送行的都寥寥无几。原来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01
在那个狂风巨浪般的年代里,王建安和许世友可谓是农村出身的两位英雄。王建安原名王见安,他与时代的贫苦农民一样,日子过得跟放牛的老黄差不多。有一天,王见安再也受不了地主的欺负,心想,反正是牛,不如来个牛犇犇地犇出条活路。于是,他趁着黑夜把地主家的老宅给点了,火光冲天,他心里那叫一个畅快,随后改名王建安,拿起枪杆子,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许世友的故事也不简单。他八岁就离家出走,跑去少林寺学了一身武艺。
两位山东大汉后来都参加了黄麻起义,虽然不在一个连队,但命运似乎特别喜欢捉弄人,总在某个烟硝弥漫的角落里让他们偶遇。王建安一次在战场上救了许世友,拉着他说:“老许,你那一身武功,怎么还差点让人给削了?”
许世友嘿嘿一笑,拍了拍身上的土:“你不懂,这叫佯输,为的是下次能赢得更漂亮。但话说回来,今天要不是你,老子可能真得给写进阵亡报告了。”
王建安摇摇头:“咱俩还是少来这些虚的,既然是兄弟,那就得互相罩着。今晚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说不定明天又得上战场。”
02
1936年,红四军的顶梁柱,也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默契得就像是锅里的饺子和醋碟一样,不得不说,这配合简直是天作之合。然而,就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一场许世友的“出走”像是掀起了一块石头,砸出了一群蛤蟆,局面顿时变得有点尴尬。
在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批判会议上,本来大家是围着张国焘来一场正义的炮轰,结果有人一激动,顺带把一堆干部都拉出来晾在风里。会议上的一席话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某人大放厥词说许世友的行为和张国焘类似,许大将军那火气可没那么好压。
他一拍桌子站起来,面对全体会议的人高声喊道:“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自己没看清自己的能力。”
王建安坐在一旁,听着许世友这一番话,心里不由得笑了。他知道这位老搭档虽然脾气如雷,但说的却是大实话。会议结束后,王建安拉着许世友一起出去,边走边说:“老许,你这嘴,真是没谁了。今天这么一闹,估计会议记录员得加班加点写记录了。”
许世友那会儿在延安可是把人气憋坏了。谁让他话痨呢,一个劲儿的和别人辩论,结果别人一句顶他一句,弄得他心气儿上不来,直接就住院了。可就在医院,他又闲不住,捣鼓出个想法:干嘛在这里受人家的欺负?哪里不能闯出天地?
这想法一出,就像是扔了个炸弹,搞得周围人都挺兴奋的。王建安,这小子,平日里就跟许世友是一唱一和的,听说要回老家搞革命,两眼都亮了。
03
话说许世友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带着人溜之大吉,结果王建安突然间良心发现,跳出来吼一嗓子:“这能行吗?我们还是军人呢,哪有随便撤的道理!”
于是,一通电话报了上头,大伙儿紧急集合,开始点名,三十多个人立马就变成了行动不便的粽子。
许世友他一听到自己名字念出来,身手矫健,上了房顶。底下的人开始劝他:“世友,别闹了。”
事到如今,许世友从屋顶上被劝下来,还是刘伯承出马,看到王建安站在旁边,许世友一时气不打一处来,指着王建安就是一顿痛骂。王建安那时候也是够郁闷的,挠挠头,无奈回应:“老许,我这也是为你好啊,你这性子,再不收敛,迟早得出事。”
许世友那时候已经被开除了党籍,整个人气得跟个充了气的球一样,随时都可能爆炸。不过,毛主席了解许世友,知道这人就是脾气直,心眼儿其实不坏。
“毛主席,我这人就是脾气急了点,做事没过脑子。”
毛主席笑笑,摆摆手,“你这火气大是小毛病,改得了。关键是别把心眼用错地方。”
许世友想了想,点点头,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但也知道自己这一出确实闹大了。只是对于王建安的事,他怎么也翻不过这一页,心里那根刺就是拔不掉。
“王建安那家伙,我这辈子是不指望他来送暖了,哼,我离他远点,算他走运。”
04
毛主席看着这两个曾经肩并肩打天下的老兄弟,如今却像是隔了条银河系,实在是心疼。他想,得让这两个硬骨头弯弯腰,不然这帐篷里怎么装得下两只硬撅撅的老虎啊?
毛主席想了想,决定来个小聚会,许世友和王建安被邀请到一个窑洞,里面摆满了酒菜。
王建安进门看到许世友,试图破冰:“许大哥,好久不见,身体可好?”
许世友斜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但还是坐下了。毛主席微笑着观察,然后开始他的和事佬大业。
“你俩啊,我看着都着急。王建安,许世友,你们俩这么多年的兄弟,就因为一次小误会就玩完?这不像你们的风格。”
王建安点点头,看着许世友:“那天我确实是有点过了,但你知道我的脾气,冲动是魔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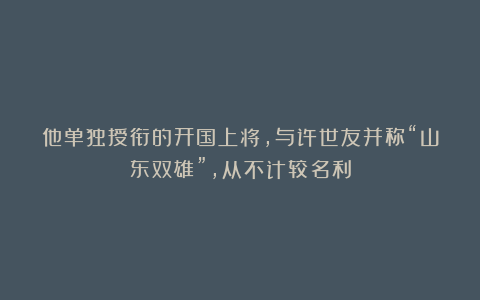
许世友冷冷地回应:“你的冲动差点把兄弟往火坑里推。”
毛主席趁热打铁:“看看,你们俩不还是一样嘛,都这么直爽。许世友,你也别往心里去,王建安,这事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今天就好好喝一杯,以后互相监督,互相帮助。”
王建安举杯:“对,来,这杯酒,我敬你,以酒消愁。”
许世友看着王建安,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举起酒杯,碰了一下:“行,今天的事,就翻篇了。”
05
就在许世友正打算用热水袋治疗他那因气愤过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时,一封电报打断了他的治疗时光。电报来自毛主席,命令他立刻前往指挥攻下济南。这下,许世友可不得不把热水袋扔一边,穿上他那件有点皱的军装。
另一边,王建安已经得到命令,准备与许世友并肩作战。他擦了擦自己的军靴。
毛主席的安排真是高明,用战场来化解个人恩怨,真是一箭双雕。两人汇合后,王建安一看许世友那满面春风的模样,心里那个乐啊,简直像看到了久违的老相好。两人一见面,许世友就拉着他的手,笑嘻嘻地说:“老王,你看这济南城墙高不高?咱们今晚可得想个办法怎么爬过去。”
王建安回他一笑,搭腔道:“许大师傅,要不咱们先别急着爬城墙,晚上先爬酒桌怎么样?”
许世友一拍大腿:“说得好!晚饭时咱们不喝点什么,岂不辜负了这千里迢迢的重逢。”
晚饭时分,两人终于坐到了一起。许世友先是端起酒杯,然后像是要发表个长篇大论似的,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老王,记得咱们在延安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
王建安一愣,想了想:“那不还是烧刀子嘛?辣得很。”
许世友点头:“对!那酒虽辣,人和人的心却是暖的。今天,咱们也是,酒辣心暖。过去的事就让它随风去吧,今天咱们这杯,不谈什么复杂的东西,只谈兄弟情,只谈打赢这场仗。”
说完,许世友一饮而尽,脸上满是坦荡的笑容。王建安看着许世友那副你看我多诚恳的表情,也是感动不已,心想这老兄终于还是回来了。他也举杯笑道:“许大师傅,你说的对,今天咱们只喝兄弟酒!”
两人碰杯,酒过三巡,话也多了起来。王建安忍不住调侃许世友:“说起来,你跳那房顶的本事还真不是盖的,那天要不是你跳得快,我还真追不上你呢。”
许世友也不甘示弱:“那是,我这’飞檐走壁’的功夫,可是训练多年的。”
王建安笑得前仰后合:“说得好,下回咱俩如果真掰了,就直接来场酒桌上的较量,看谁先倒。”
酒桌上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两位老兄弟的心结就这样在笑声和酒香中,慢慢解开了。而济南的战役,也在两人的团结合作下,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建安来某地巡查,期间有场电影放映,王建安一到现场,看着这首长专座,真是哭笑不得。他直接走到团里的领导面前,一脸懵:“老兄,这是咱们看电影呢,还是准备给皇帝爷接风洗尘?这桌子这椅子的,难不成还得有人伺候着扇扇子、捶捶背?”
团里的领导也是一头汗,“王首长,这是咱们想让您舒舒服服看电影。”
王建安摆摆手,“舒服?你看看这些战士,都坐在背包上,我倒坐在这首长专座上,舒服个头啊!这不是显得我特立独行么?咱们解放军什么时候这么讲究了?”
领导一听这话,也觉得有点过了,“那,那这首长座…”
“行了,行了,”王建安一挥手,“把这桌子椅子撤了,茶水点心什么的也不用了。咱们跟战士们一样,坐地上看,这才叫团结!”
团领导赶紧吩咐下去,将首长专座这一套全撤了,王建安找了个空地,和战士们一起坐下。他拍拍旁边战士的背包,笑着说:“这才对嘛,咱们平等看电影,谁也别装大爷。”
战士们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热络了不少。
06
王建安这次真是彻底看清了部队的“戏精”本色,从集中展示精锐到借猪充数,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建安在写报告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这份报告得写得文艺点儿,不然直说这些,谁信啊?”于是,他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他在报告中写道:“在某部队的’养猪场’,我见到了这样一幕——一头刚从别处借来的猪,正被两个士兵小心翼翼地擦拭,以便在检查中展示其’养猪效益’。我不禁思考,这猪是来参加美容大赛的吗?”
王建安继续描述他的观察:“当我来到训练场,看到的是一群士兵正在进行所谓的’特训’,可这特训的场面,和我以往见过的训练不太一样,更像是某种仪式的排练。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还是准备上干别的事情。”
对于领导层的态度,王建安也有话要说:“部队的表现赞不绝口,然而在赞美的背后,是一种’你演我看’的默契。领导们对这种行为视而不见,仿佛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模范’。”
最后,王建安在报告中呼吁:“我们的军队需要的不是表演者,而是真正的战士。我们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检查,而是为了战场。让我们拿掉这些虚假的面具,还军队以真实。”
报告完成后,王建安叹了口气,把它递给了上级。虽然他知道这可能会引起一些波澜,但他相信,为了军队的长远发展,这是必要的。
“如果这报告能让部队回归本色,那么我写这一场’大戏’也值了。”
07
王建安生前总是个淡泊名利的人,连死都不愿意给人添麻烦。那天看电视,外国某首脑的葬礼,仪式一个接一个,就像没完没了的电视连续剧,弄得他直摇头。转头对着坐在旁边的妻子牛玉清说:“看看人家这排场,我要是死了,你可别这么整,简简单单的,把我撒回家乡的土地上,让我也体会体会那什么大自然的怀抱。”牛玉清听了,点点头,虽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也知道他这人一向如此,从不喜欢折腾。
到了1980年7月,王建安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候他又叫来家人,坚持要简单处理后事。王建安去世后,牛玉清真的照他的意思办了,甚至连老战友和朋友都没有通知,就这么静悄悄地把他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