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的老皂角树又落了一层叶时,小豆蹲在玉米地埂上,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没入金黄的穗浪里。晨露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同样沾着露水的清晨——那时他刚上初中,揣着母亲给的五块钱早饭钱,偷偷买了游戏机币,在镇上的游戏厅耗到日头偏西,回家时正撞见父母扛着玉米秆从地里出来,父亲的草帽沿滴着汗,在晒场上砸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那时的小豆是村里有名的”野小子”。村部的公告栏换了新通知,他会趁夜里用粉笔在”禁止焚烧秸秆”后面画个小乌龟;二伯家的玉米先黄了尖,他嘴馋,带着邻家狗蛋钻进地里掰了两个,剥开皮啃得满嘴金黄,被二伯追到晒场,他抱着头蹲在麦秸堆里,听见父亲给二伯赔笑:”孩子不懂事,我赔你十斤新米。”
父亲很少动怒。每次闯了祸,父亲总是先沉默地抽袋烟,烟锅在鞋底上磕了又磕,才说:”地里的活计,一分力气一分收成。你现在偷的懒,将来都得补回来。”小豆那时听不懂,只觉得父亲的话像玉米叶上的绒毛,刺刺的却不顶用。他梗着脖子跑开,衣角扫过堆在院角的玉米棒子,哗啦啦滚了一地,像撒了串没穿线的珠子。
十五岁那年的秋收,是小豆第一次正经下地。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他从被窝里拽起来。灶台上温着玉米糊糊,母亲往他手里塞了个煮玉米,”吃完跟你爸去掰玉米。”他捏着滚烫的玉米,皮被烫得通红也不肯撒手——不是舍不得,是实在不想下地。
玉米地里像个巨大的蒸笼。刚灌浆的玉米穗沉甸甸地坠着,叶片边缘的锯齿割得胳膊生疼。父亲教他”一手扶秆,一手掰穗”,他学了两下就嫌麻烦,抓住穗子使劲一拧,连带着半截秸秆都拽了下来。父亲回头看见,眉头拧成个疙瘩,却没骂他,只是弯腰把断秆拾起来,捆在胳膊上:”秆子还能当柴烧,别糟践了。”
日头爬到头顶时,小豆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他瞅着父亲把玉米穗扔进竹筐,筐子满了就弓着腰背到地头,一趟又一趟,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他蹲在树荫下啃玉米,听见母亲在地那头喊:”小豆,把水壶递过来。”他应了声,却懒得动,直到母亲自己提着水壶走过来,他才发现母亲的手背上划了道血口子,渗出来的血珠被汗水冲得淡红,像串没干透的红玛瑙。
“咋弄的?”他下意识问。
“被玉米叶划的,不碍事。”母亲用衣角擦了擦,笑着往他嘴里塞了块冰糖,”你爸说让你先回家歇着,下午不用来了。”
他捏着那块冰糖,含在嘴里甜得发齁,却忽然觉得喉咙发紧。那天下午他没去游戏厅,坐在自家门槛上,看着晒场上堆起的玉米山,父亲正用木锨把散开的玉米粒归拢,每扬起一锨,金色的颗粒就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弧线,落在场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时光在悄悄计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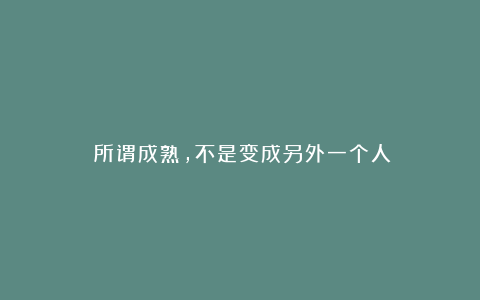
小豆那天从学校回来,刚进院门就看见母亲坐在灶台前抹眼泪,锅里的玉米粥溢出来,糊了锅底。他放下书包,没像往常那样喊饿,径直走到墙角拿起镰刀:”妈,我去割玉米。”
母亲愣住了,抬头看他,眼里的泪还没干:”你会啥?”
“看爸做过几百回了。”他把镰刀往腰里一别,抓起墙角的竹筐就往外走。
玉米地比记忆里更辽阔。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左手扶住秸秆,右手握紧镰刀,刀刃贴着地皮割下去,却没掌握好力道,镰刀”哐当”一声砍在石头上,震得虎口发麻。他咬着牙重新再来,割到第三垄时,手掌磨出了水泡,玉米叶扫过脸颊,火辣辣地疼。日头偏西时,他回头看,割倒的玉米秆歪歪扭扭地躺在地里,像条没铺直的路,而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风一吹,凉得刺骨。
傍晚收工时,他背着半筐玉米穗往回走,远远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皂角树下张望,手里攥着块干净的布。走到近前,母亲拉过他的手,用布轻轻擦去上面的泥污,摸到水泡时,指尖顿了顿,又继续往下擦:”明天别割了,妈请隔壁三婶来帮忙。”
“不用。”他低头看着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最大的煮玉米剥好递给他,自己啃那半拉没长饱满的;想起父亲每次从镇上回来,布袋里总藏着块水果糖,塞进他手里时,掌心的老茧蹭得他手心疼。他喉结动了动,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说:”我能行。”
那半个月,小豆每天天不亮就下地。他学会了用巧劲割秸秆,知道哪片玉米穗长得瓷实,懂得把割好的秸秆码成整齐的垛,方便母亲抱回家当柴烧。有天夜里他起夜,看见父母屋里还亮着灯,听见父亲低声说:”孩子胳膊都肿了…”母亲叹口气:”懂事了,懂事了…”他站在窗根下,直到灯灭了,才轻轻回了自己屋,被窝里像揣着块热玉米,暖得人眼眶发烫。
二十岁那年,小豆考上了省城的大专,学的是农业技术。每年秋收,他都会请假回家,带着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教父母怎么选玉米种,怎么用无人机打药。有次村部的公告栏贴了新政策,说种粮有补贴,他仔细读了三遍,拉着村支书去家里,给父母讲清楚怎么申请,怎么填表。支书拍着他的肩膀笑:”这小子,比他爸还会琢磨事。”
今年的玉米收得格外顺。小豆买了台小型玉米脱粒机,接在拖拉机上,玉米粒顺着出口哗哗往下流,比人工剥快了十倍。父亲坐在地头的小马扎上,看着机器转得欢,胳膊上的旧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浅白,他忽然说:”当年你爸我总说,力气不会骗人。现在看,你这读书学来的本事,也不会骗人。”
小豆笑着递过去一瓶水,目光掠过晒场上的玉米山。金黄的玉米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无数个被点亮的日子。他想起十岁那年偷掰的玉米,甜得张扬;想起十七岁割玉米时磨出的水泡,疼得真切;想起此刻掌心握着的水瓶,凉得踏实。原来成长就像这玉米地,春天要耐得住返青的慢,夏天要经得住暴雨的猛,秋天才能结出饱满的穗——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子,那些流过的汗、受过的疼、咽下的话,终究会在时光里沉淀成沉甸甸的收获。
傍晚的风掠过晒场,带着玉米的清香。小豆帮母亲把最后一袋玉米粒扛进仓房,转身看见父亲正用布擦那台脱粒机,动作慢悠悠的,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宝贝。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金黄的玉米堆上,像一圈圈慢慢生长的年轮,刻着岁月,也刻着成长。
他忽然明白,所谓成熟,不是变成另一个人,而是终于看懂了父母弯腰的弧度里藏着的爱,终于学会了把年少的莽撞变成沉稳的担当,就像这玉米,从青涩到饱满,从张扬到内敛,最终把根扎在土地里,把甜藏在芯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