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管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主办
来稿请以纸质稿寄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本刊唯一收稿邮箱)。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北京,10087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出简牍与秦汉基层治理体系再研究”(24AZS001)阶段性成果。
摘 要:秦为诸侯不仅是秦的建国之始,而且是两周之际的重要事件。秦之兴起与“周二王并立”、平王东迁关联密切。通过对《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一则关键史料的重新复原,有助于我们揭示相关历史史实。据此,幽王死后,平王始立于申,与携王开启“周二王并立”之局。秦为诸侯,源于救周有功,而非护送东徙。秦获得诸侯身份的时间应定于公元前771年,实为周室东迁之前,且为平王所封而非携王。受封秦君当为襄公。《史记》呈现“周衰秦兴”的框架性解释,然而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洛的著名历史叙事并不可信。秦受封之地,仅为岐山以西,而非传统理解的岐、丰之地。随后,秦文公东伐至岐,晋文侯西杀携惠王,秦、晋在关中首次形成并峙之势。至文公“营岐雍之间”,秦已突破封域,背后源于晋陷曲沃、翼二系内争,无暇西顾。在伐戎之外,周室、晋侯的地域政策变动,也是认知早期秦国东进的线索。探析二王并立与秦为诸侯的历史脉络,不仅有助于重审东周史的开启与周秦变革,而且可为厘清《左传》注疏、《史记》撰作等历史叙事、年代学的基本问题,提供理论方法上的启示。
关键词:二王并立;秦为诸侯;平王东迁;《左传正义》;《史记》叙事
文章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条复原与“周二王并立”
三、救周、送王与《史记》“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的历史叙事
四、也说秦始封之地与文公“营岐雍之间”
五、关于《左传》《史记》的史料、叙事与年代学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秦为诸侯,是先秦历史上的大事件,对理解“周秦变革”、把握秦统一与秦王朝形成史有着重要意义。襄公始封为诸侯,秦也由此开启东征进取之途。作为探讨秦之建国史的重要起点,围绕这一史实的考察内容已经比较丰富。 相较于其他主要诸侯,秦的受封时间明显偏晚,具体发生于西周覆亡、平王东迁之时,实则与东周历史的展开同步。《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云: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
这则史料本意是言及秦在始封之初已具有政治雄心,然而其对“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三件历史大事的并列交代,却暗含史学撰述深意。有意思的是,或因《秦记》叙事之强调,或因太史公作为史家之裁断,这一“周—秦”叙事模式不独见于《六国年表》,在《史记》其他篇卷中也不避冗繁而多次出现。由此言之,秦为诸侯也被后世视作两周交替时期的重大事件,可置于这一历史变动的大背景下作更加全面的考察。
两周之际,世事纷纭。与《史记》涉及幽王、平王的历史叙事不同,其他传世及出土文献多对平王、携王的“周二王并立”之局有所记载。近年来,伴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的刊布,学界对此问题讨论更趋热烈,并尝试重订历史、调整系年,但在具体史料解读及历史过程梳理方面,尚有分歧。不过,围绕“周二王并立”的问题,相关研究很少将其与“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一事联系起来,也较少关注此事会对秦之建国史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阐说。一方面,对“周二王并立”史事的重新考辨,是理解秦为诸侯得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二者应当结合起来思考;另一方面,两周之际大事系年的调整,直接影响秦国君主在位编年的年代学研究,进而促使我们对过去深信不疑的《史记》有关秦国早期的历史叙事,重加审辨。在此背景下,一些基础而关键性问题应运而生:幽王被灭、“周二王并立”的历史过程究竟为何?秦被封为诸侯于何年,初侯为何君,受封于何王,究竟源于何种功勋,与周室东迁是何种关系?秦受封之地的空间范围究竟为何,秦文公“营岐雍之间”的历史内涵、背景和影响是什么?
下面围绕“周二王并立”与秦为诸侯,立足文本叙事以及对政治地理的分析视角,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进一步比勘辨正,依次从背景、年代、地域三个方面加以探讨,在实证基础上提供新的历史图景,并以史实所涉及《左传》注疏、《史记》撰作为中心,提供史料学、历史叙事、年代学层面的理论方法再思考。
二、《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条复原与“周二王并立”
针对西周末年的政争,《史记》卷五《周本纪》、卷六《秦本纪》叙说较详,而且相对统一,相关叙事主要参考了《秦记》等史料。《秦记》所记,反映秦人对自身发展脉络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归纳;而《史记》所记,又反映司马迁读《秦记》后对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秦记》“文略不具”,记录的幽王之死、平王即位、东迁雒邑三事,依次对应父死、子继、东迁,也易被理解为紧密相连之事。《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便将“平王元年东徙洛邑”,系于幽王十一年被杀的下一年, 即公元前770年。
不过,两周之际的历史变动更为复杂。与作为第二手史料的《史记》不同,《左传》《国语·郑语》《竹书纪年》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等可视作第一手史料。后者不仅提到幽王之死,本有曲折,还提及平王即位之时,尚有携王在位,一度出现“周二王并立”的情况。另外,关于周平王东迁的时间,相关第一手史料也与《史记》多有不同。其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
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国语·郑语》记载:
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汲冢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记载: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系年》简五至简十记载: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上述文献所记幽王之死大致归纳为以下内容:平王原为太子,但幽王宠幸褒姒,改立褒姒子伯盘为太子,欲杀平王;平王逃至外戚家西申;幽王发兵,围平王于西申,申人拒绝交出;西申的与国缯国引来西戎,同幽王交战,在骊山下的戏地将幽王、伯盘一并攻灭。其中,学界多据《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之句认为,平王逃至西申之后,即被拥为天王,故在幽王生前,一度形成平王、幽王的另一次“二王并立”之局(或称平王、幽王、丰王[伯盘]三王并立)。这也被视作幽王兴兵伐申的重要原因。如此,“二王并立”便不止发生了一次。
关于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周之宗室立平王与立王子余,基本同时发生,并非一先一后,《竹书纪年》及语序恐有未周全之处。除此之外,“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与下文“以本非适,故称携王”也相呼应,表述格式完全相同,均作:“以本〇,故称〇王”,初看似乎也可作为一条佐证。不过,细按“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与“以本非适,故称携王”,在文义上明显不合。 因为围绕“携”字,一则强调属于地名,另一则强调源于身份。今反复斟酌前后文句及表述语气,所谓“以本非適,故称携王”,应非接续的正文,而可能是注文。值得注意的是,隋人刘焯、刘炫对汉晋诸家所作五经义疏,多有汇集考辨。 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实际是在刘炫所作《春秋左传述议》《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序注》和《春秋攻昧》等文献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进而言之,《春秋左传正义》中其实包含孔颖达对刘炫旧疏的不少摘录。以往研究普遍对刘炫疏、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的文本内容,不作太多区分。实际上,相较于杜预集解,刘炫等旧疏往往先引基本文献,再说自己的看法,侧重点不同于杜注,并时有对杜注的驳正。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则明显不同,更多体现了“疏不破注”的特征,所论往往是为支持和补充杜注,很少提出反对意见,也很少广泛征引文献,用来作为论说的依据。由此言之,《春秋左传正义》之“正”又隐含对刘炫等旧疏的规正。《春秋左传正义》此条在引《汲冢书纪年》之前,还引用了《国语》《史记》,并有“刘炫云:’如《国语》、《史记》之文,……’”的表述。
清人刘文淇撰《左传旧疏考正》,尝试从《春秋左传正义》考索进而找出刘炫等前人旧疏。他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引《春秋左传正义》后,案:“此光伯述议语,前则旧疏原文。” 其中,刘炫字光伯。通观前后,刘炫首先怀疑杜预集解关于伯服为携王之说,然后抛开携王是谁的问题,讨论携王如何被立为王。刘炫先引《汲冢书纪年》指出平王本是太子,所以是正统的“天王”;再引《汲冢书纪年》说明携王是谁,并评论他何以被称为携王;最后引束皙说以规杜氏。因此,《春秋左传正义》引《汲冢书纪年》,实际出自刘炫所引。刘炫在加以征引同时,还做了疏解。范祥雍云“’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八字,疑乃孔疏引刘炫之案语,与下文’本非适,故称携王’,相同”。 在此之前,王先谦疏解《诗·王风·扬之水》时,径称“《左昭二十六年传疏》刘炫引《汲冢纪年》”。 不过,这些观点过去很少被人注意和参考。至于“’先是’这个词,同样是后来侵入的,是孔颖达在引用《竹书纪年》古墓本时自己增加的” 的意见,较此前认识已有推进。今据《通鉴外纪》《通志》引《汲冢纪年》曰,“幽王既死”四字,应当前移,下接“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上承“与幽王俱死于戏”。进而,“先是”二字或非“后来侵入”,也不是“孔颖达在引用《竹书纪年》古墓本时自己增加的”,原来可能在“平王奔西申”之前,用于交代“周二王并立”事件发生的基本背景。而“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以本非適,故称携王”两条,表述工整,各有八字,应属刘炫案语,皆非《竹书纪年》原文。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征引《竹书纪年》,诸条正文中不曾出现类似“本注”的文字,也可为证。
综上,《春秋左传正义》所引《竹书纪年》这一习见而重要的史料,可以重新复原如下。今格式参考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的点校体例,凡释文有误,均用“()”括注误字,“〔〕”括注改释字、应作字。此外,正文使用楷体,注文使用黑体:
〔先是,〕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幽王既死,〕(先是)申侯、鲁(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刘炫云)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刘炫云)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在此基础上,《系年》与《竹书纪年》所叙内容仍有不同。《系年》在幽王被杀后,称“周乃亡”,可与《国语·郑语》“周不守”“周存亡”对应,实指西周灭亡;《系年》不称“二王并立”,而称“周亡王九年”,更强调西周、东周前后相接续的整体史观。根据《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及“邦君诸侯”的表述,“邦君”与“诸侯”“诸正”并列有别,与西周诸侯、邦伯分列类似。关于“邦君”,有学者认为此指畿内诸侯, 有人认为“西周金文中的’邦君’很可能就是管理王畿采地之官”, 还有人认为指“非周王朝分封的国家”, 另有人认为指没有“诸侯”之称的外服贵族,凡称“伯”者均属“邦君”。 韩巍分析邦伯,提到外服的邦伯地位低于诸侯,作为小邦多为当地土著,未获王命授爵,有的与周王室、畿内世族和其他诸侯国有密切的政治往来和通婚关系,具有诸侯臣、王臣双重身份。 谢能宗分析“邦君”是没有“诸侯”之称的外服封君,“邦君”外服属性没有“诸侯”强烈,多背靠王畿,外接诸侯,有一定上通下达、沟通内外的功能。 王坤鹏系统考察商、西周邦侯,倾向认为邦君作为地方原有小族邦的统治者,可分两类,一类在王畿,周王派官管理;一类在畿外,地位和重要性不及诸侯。 这里,“邦君诸正”之“邦君”,相较“诸侯”而与“诸正”的联系更密切。“诸正”多指王朝卿士、卿事寮等内服王室官员,“邦君诸正”之“邦君”指王畿(及畿外)具有王臣性质的当地小邦。相关活动当以“诸正”为核心,也即以《竹书纪年》所言“虢公翰”为代表。幽王弟携王在位二十一年,也始终居于虢国之地。又联系《国语·郑语》“王心怒矣,虢公从矣”,拥立携王的群体主要来自幽王的残余政治势力。平王、携王均未治政于镐京,一在申地,一在虢地,分处镐京以北、以西,大体以岐山为界,形成对峙。此种情况持续时间长达九年,二王没有得到普遍承认,“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故《系年》称“周亡(无)王九年”。“邦君诸侯”之“邦君”,主要指畿外臣服于周、地位低于诸侯的土著小邦。随后,一些重要的外服诸侯开始介入,晋文侯迎平王而立于京师。由“乃东徙,止于成周”反观,“京师”指镐京或丰镐。平王的合法地位开始确立,“周亡王”阶段结束。不过,经历犬戎洗劫破坏,宗周很难再现往昔荣光。囿于四周戎族势强,加之携王居于西侧,平王“晋郑焉依”,主要依靠东方诸侯,于是三年之后, 东迁成周。至迁雒之后第九年,即携王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晋文侯杀周携王于虢。还可看到,相较于《史记》卷五《周本纪》《竹书纪年》,《系年》三次言“晋”,更为突出晋国在拥立平王、推动两周之际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两周变局经过史料的重订、考证与辨析之后,可大体归纳如下。公元前771年,幽王十一年,幽王死,西周亡。公元前770年,平王即位于申,携王即位于虢,“周二王并立”,又称“周亡王”。公元前762年,晋文侯迎平王于少鄂,立于京师,“周亡王”结束,“周二王并立”名义上结束。公元前759年,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携王,“周二王并立”实质上结束。重新审视诸家所排编年,程浩所排方案最为可取。 本文考证的方案与他最为接近。按周平王得立在公元前770年,得诸侯承认在公元前762年,因为最终成为幽王之后的继任周王,故《史记》将平王即位,定于初立于申的公元前770年,与幽王积年衔接,虽与历史实情稍有距离,但在年代学上尚属可通。其中,平王积年为51年,而非66年,具体包括在申8年(公元前770—公元前763)、在京师3年(公元前762—公元前760)、在雒邑40年(公元前759—公元前720)。
三、救周、送王与《史记》“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的历史叙事
相较于《竹书纪年》《系年》等交代幽王、伯盘被灭原委,平王、携王一度“并立”。《史记》卷五《秦本纪》所记更偏重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的历史发展线索,由此形成下列叙事结构:
幽王时,犬戎攻幽王,襄公救周室;
平王时,平王避犬戎,襄公送平王。
至于携王,当时既未得到诸侯普遍承认,也与襄公封侯直接关系较小,《秦记》可能未多涉及。
在此基础上,尚存问题仍然有二。其一是叙事问题。这虽体现秦、戎的敌对关系,但在平王东迁之前,犬戎、襄公于平王似乎分别为友、为敌;至平王东迁之时,犬戎、襄公于平王又分别为敌、为友,所以会有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 其二是年代问题。如按照《系年》及《竹书纪年》而重新厘定的两周之际编年,秦襄公救周,在前771年;而秦襄公送平王东迁,应在前759年而非前770年。由于秦襄公在位只有十二年,如果秦襄公在七年参加救周,那么送平王之时已经去世;如果秦襄公在七年送平王,那么将兵救周之时尚未即位,而且秦襄公、秦文公乃至整个秦国编年皆须进行调整。 因此,两周之际史事系年重新订正后,对周王编年影响不大,但却有可能改写秦君编年。秦是在前771还是前759年被封为诸侯?所封是襄公还是文公,甚至其他秦君?这些重大而又基本的历史问题,均需要再加考释与阐明。
首先,幽王改立伯盘之后,平王出奔乃是奔西申,而非奔向西戎,双方对立关系实为:
幽王+褒姒、伯盘——申侯+申后、平王
是时,“申、吕方强”。因此,平王外逃,西申敢于接纳平王;被围之后,西申也敢于拒绝交出他。 这一阶段,幽王主要依靠“王师”力量。随后,双方加以援引的力量成为左右时局的关键,具体又可表示为:
幽王+褒姒、伯盘+诸侯(?)——申侯+申后、平王+缯、犬戎(?)
《左传》《史记》《竹书纪年》都提到幽王兴兵围申之前,发生下列事件:
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
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
盟于太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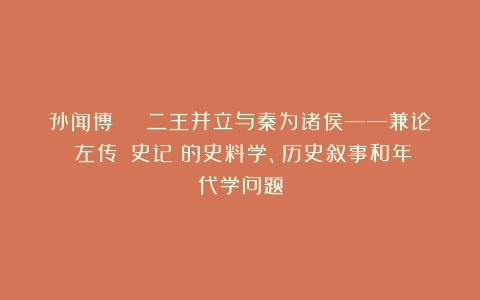
关于最后一则,整理者案“今本《纪年》云:’(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现姑从今本列此”。 司马迁参考《吕氏春秋》或类似的晚近材料,在《秦本纪》中记叙了“烽火戏诸侯”事。然而,上述引文显示周幽王曾在中原会盟诸侯。其中,《左传》所记出自椒举语,原作“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侈”,杜预《集解》作“自奢侈”。 按“侈”与下文“汏”含义相近,实皆为骄泰之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 可为例证。此指王待诸侯以礼仪,诸侯因此而听命;王示诸侯以骄纵,诸侯因此而违命。这里,周幽王的“太室之盟”与夏桀的“仍之会”、商纣的“为黎之蒐”并举,类型相近;又因自身骄纵,结果相类,恐怕不属于改行“东周”盟会形式,从而降低了身份。 由上,“太室之盟”未能起到凝聚之功,反而造成“诸侯所由弃命也”的形势。在此背景下,幽王一方失去诸侯支持,西申一方的缯国又引来犬戎,幽王因此才会被攻杀于骊山之下。
相较于《史记》卷五《周本纪》、卷六《秦本纪》所叙,《国语·郑语》言及“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缯与西戎方将德申”,以及《系年》“曾(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较为强调与幽王交战的是缯、西戎,而不及西申。至于《史记》的年表、书、世家部分,更是主要强调犬戎。如《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周”栏作“幽王为犬戎所杀”,“郑”栏作“(郑桓公)以幽王故,为犬戎所杀”;同书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云“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同书卷二八《封禅书》“而幽王为犬戎所败”。 而《史记》三十卷的世家部分涉及两周之际相关史事,更显丰富而系统,直接相关者计有十二卷。需要说明的是,吴、越偏处东南,早期缺乏纪年材料,《十二诸侯年表》没有“越”栏,“吴”栏前期一直是空白,初始为吴寿梦元年,已晚至前585年。其余十卷,主要涉及十一诸侯,而且均见于《十二诸侯年表》,相关分别为:齐、鲁、燕、蔡、曹、陈、卫、宋、晋、楚、郑。所叙十一处,皆只言犬戎,而不及申、缯。 更具体来说,称“犬戎杀幽王”,如记齐、鲁、晋、郑事;称“犬戎杀周幽王”,如记卫事;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如记蔡、曹、陈、宋事;称“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分见于记燕、楚事。
《史记·匈奴列传》表述虽与《周本纪》相近,但还提到其他内容:
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焦获亦名刳口,亦曰刳中,在雍州泾阳县城北十数里。周有焦获也”。 焦获是著名薮泽,在今陕西泾阳西北仲山西麓。 西戎已东居泾、渭之间,据有此泽,隔渭水南向威胁丰、镐,形势确属严峻。《史记》突出戎人活动,固因该群体与秦人关系密切,但也并非夸饰甚或建构。《国语·郑语》记周幽王时史伯语,已云“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又云: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
由此,两周之际政治局面与族群形势可概括为“戎逼诸夏”。 此记“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对应西周核心地区的宗周、成周及其附近。至东周初叶,这一地区“往往有戎”,《西羌传》以水系划分,涉及六个区域:渭首、泾北、洛川、渭南、伊洛间、颍首。其中,前四者均对应关中。顾炎武做过一个有趣的比附:“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 平王即位,拥戴来自西申,而非西戎。他的处境实与携王同,皆身处西戎包围之中。 鉴于西戎是攻杀幽王的主要力量,本身又属一时之借兵而非臣邦,乘势劫掠镐京,盘踞宗周而不去。今即位之后,平王应始终与西戎保持距离。
至于嬴秦,先世大骆一支原与申侯联姻,“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捍卫王室。至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由此余族与西戎为仇。自秦仲至襄公,秦嬴一支便一直伐戎。因而,当“诸侯叛之”“兵莫至”,以致周幽王、伯盘被杀,未为诸侯的秦与西戎世仇,自然会站在王室一边,“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联系《史记·匈奴列传》“秦襄公救周”上接“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而非上接“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所谓“秦襄公将兵救周”之“救周”,非指救周幽王,而指救周室。学界有意见认为:秦为诸侯,实际乃是周携王所封。秦襄公也许是《系年》所说拥立周携王的“邦君”之一。因而待周携王死后,自顾不暇的周平王也就只能承认了秦的诸侯地位。对于这一认识,尚有商榷空间。首先,“救周”一事,当时并非只有西方之秦,至少尚有东方之卫。《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记:
(卫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
此与前引《史记》卷五《秦本纪》,恰可作详细比对。具体而言,卫、秦两国君主都曾亲自“将兵”。卫武公“佐周”对应秦襄公“救周”。卫武公“平戎”对应秦襄公“战甚力”。卫武公“甚有功”呼应秦襄公“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 呼应“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可以看到,相关表述基本每一部分都可形成对读,发生时间相近,乃为同一事件的两个面相。周携王虽为幽王残余势力所立,但他是周幽王之弟而非太子,幽王生前并未指定由余臣接任,余臣也未得到外服诸侯、邦君拥护。秦、卫平戎救周,捍卫王室。相较周携王,是时周平王力量偏弱,他以王嗣身份对秦、卫开展更积极的联络,加以封赐,并不突兀。襄公如为携王所封,《秦记》记载似可对具体由何王分封做淡化处理,不必点明平王。《史记》也无必要特别将襄公与卫君并举,以叙平王奖赐之事。至于平王封秦的具体地域交代,以及“与誓,封爵之”的正式程序记载,恐怕也无法忽视。由此而言,应不存在秦公与周平王关系由为敌到为友的转变。幽王行太室之盟后,已呈现诸侯离心、戎狄反叛之象。然而,诸侯不拥戴周幽王,并不代表允许西戎灭周。周幽王死后,“二王并立”之局出现,明确拥立周平王的诸侯起初尚不算多。秦襄公坚决伐戎,忠心有功于王室,由此而被周平王争取笼络,封为诸侯,与卫君同得奖赐,符合这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政治情势。
不过,由于《史记·秦本纪》又有“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的记载,一般认为秦为诸侯与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将护送平王迁洛视作秦始立国的直接原因。 对此,唐人张守节云“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下面略作考辨。《秦本纪》虽然在“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一句下,方交代“平王封襄公为诸侯”,但是在《十二诸侯年表》“秦”栏中,“始列为诸侯”实际系于“幽王为犬戎所杀”的公元前771年,而非“平王元年东徙洛邑”的公元前770年,而且没有提及“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事。司马迁的这一处理,恐怕并非随意而为。公元前771年,在年表中具体对应幽王十一年、鲁孝公三十六年、齐庄公二十四年、晋文侯十年、秦襄公七年、楚若敖二十年、宋戴公二十九年、卫武公四十二年、陈平公七年、蔡釐侯三十九年、曹惠伯雉二十五年、郑桓公三十六年、燕顷侯二十年。所记除在卫、郑世家中主要交代本国的卫武公、郑桓公的相关参与情况外,在其他对应世家皆有反映,唯所涉鲁孝公三十六年当作二十五年, 例如:
(齐)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洛。秦始列为诸侯。
(蔡)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
(曹)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秦始列为诸侯。
(陈)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晋)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楚)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初观之下,“秦始列为诸侯”一事,多列于“周东徙”之后,次序与《秦本纪》所述相近,似乎可以印证秦为诸侯在襄公护送平王东迁之后。然若细察,情况却并非如此。上计世家五卷、六则叙述,实际皆可分作两个部分:1.周,2.秦。周的部分又顺次交代二事:1a.幽王死;1b.周东迁。因此,中华书局点校本在上述周、秦史事中间,基本使用句号点断。而周、秦史事所属诸侯纪年,全部对应周幽王十一年,而非周平王元年,也即全部系于公元前771年,而非公元前770年。所谓“周东徙”,主要因世家记事简要,顺次交代,并不反映秦被封为诸侯一事在周室东迁之后发生。《六国年表》“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系年》“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一五、一六),及《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骊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表述形式近似,实际也可作此理解。而下列各诸侯的“世家”所录,更为明显:
(鲁)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
(燕)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
(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秦始列为诸侯”,直接列于周幽王被杀之后,同属“1.周,2.秦”的叙事结构。所属诸侯纪年,同样系于公元前771年,而非公元前770年。本组与前一组在叙事上的处理,实际是一致的。这些“世家”均特别交代秦国史事,几无缺载,反映司马迁的撰作理念。他将两周之际的幽王被杀、平王东迁与秦为诸侯,视作两周变迁的重大事件。前者代表周衰,后者代表秦兴,可进一步概括为“周衰秦兴”。 在此基础上,参考《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又记“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洛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以及《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酆之地,列为诸侯”,《史记》卷五《秦本纪》中的《索隐述赞》“襄公救周,始命列国”等内容, 引出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史记》虽多次说秦为诸侯,但是除《秦本纪》之外,再无一处提及“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一事。“孤证不为定说”,如此熟知之事,原来也是其中一例。
关于“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的历史叙事是否可信呢?据前考订,平王东迁的时间是前759年,对应秦文公七年。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附别本“秦纪” 记秦襄公至二世皇帝共33位秦君的在位年数。其中,32位秦君使用了统一表述,无论称公、称王,还是称皇帝,均记作:
〇(公、王、皇帝)享国〇年。
文公子、宪公父静公(竫公)实未即位,在列入时被记作“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唯一例外是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考虑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研究者在使用涉及襄公及文公早期史事及系年的史料应审慎考量。“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在《史记》中仅见一次,作为著名的历史叙事实际并不可信。这里提供一种推断性意见:秦师护送周平王东迁,可能确曾发生,或因同为七年,系于襄公,而实由文公护送。
综上,秦襄公所救是周王室,而非周幽王。秦为诸侯,源于救周有功,而非护送东徙。秦为诸侯的时间仍应定于公元前771年,而非公元前770或公元前759年,具体对应周幽王十一年、秦襄公七年。受封秦君确是襄公,受封实在平王东迁之前。《史记》所载秦君系年,有相当依据,基本可信,不宜因新材料的发现便作全面、根本性的调整。
四、也说秦始封之地与文公“营岐雍之间”
关于秦襄公受封的具体内容,《史记》卷五《秦本纪》云: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秦后来所据关中内史地区,也即秦早期东进所涉区域,自西而东实际可以分为三个区域:1.岐以西之地;2.岐丰之地;3.河西之地。受封内容虽然同样为人熟知,但是既往认识多有分歧。目前,至少存在以下两种代表性意见:1.周封秦以岐、丰之地。此说出现很早,东汉人多已言之,如班固称“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酆之地,列为诸侯”,高诱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为诸侯”,郑玄《诗谱》曰“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 南宋王应麟等历代学人多有从之。清人顾栋高虽然加以辩驳,但是清人崔述、今人杨伯峻等普遍采用此说。 2.周封秦以岐山以西。但是,秦如能伐戎,收复岐、丰之地,还可东据这一宗周故地。
不同于这两种认识,秦受封之地,应仅为岐山以西。按西周后期,秦居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 仍在陇山以西。“赐之岐以西之地”,与之在地域空间上可相衔接。而平王封襄公时,携王尚在虢地,即今陕西宝鸡、岐山、扶风、凤翔一带,而非河南三门峡一带。周赐秦地,不可能跨越携王。平王封秦,不仅在“二王”中实现对秦的争取笼络,而且赐岐以西之地,在赏功、驱戎之外,可能还有驱携王势力的考虑在内。因为虢正在“岐以西之地”。《系年》又记平王后来东徙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此近于“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周室东迁,不仅“晋郑焉依”,而且可能一度由晋、郑分主西方、东方诸侯。当时,晋文侯因拥立之功还逐步在宗周开拓土地。“始启于京师”之“启”,即此含义。 又,《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劳而赐地”不只提到秦襄公,还涉及晋文侯。由此,秦始封“岐以西之地”,而非“岐丰之地”,更符实情。
至于第二种习见说法,也须斟酌。除前论之外,平王封秦之时尚在申地,也即宗周区域,不会将岐丰分封出去,更不会以口头随意赠予,况且是选送新晋诸侯。同时,赐地程序颇为正式,所谓“与誓,封爵之”,当对应明确而具体的地域,不应在已赐之外,复允它地。最后,岐、丰之地有戎,岐以西之地也有戎,所言不宜只称后者须“攻逐戎”,而省言前者情形。细按平王“曰”,此应就“赐之岐以西之地”一事,加以解释之辞。平王指出,当时戎族广布,世事艰难,“岐、丰之地”尚且被戎人侵夺;今赐“岐以西之地”,同样有戎,幸勿为怪,“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即有其地”之“地”,指岐山以西之地,而非岐、丰之地。这与下文“襄公于是始国……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进兵地点为“至岐”,行动方式为“伐戎”,也可对应。
襄公去世,文公即位。文公四年,秦东至汧、渭之会,并营新邑, 统治中心开始东移。《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称“文公逾陇”。 由于周携王尚在虢地,秦之活动形成对周携王的西向包围。《史记》卷五《秦本纪》又云:
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文公继续襄公事业,东征所至更远,已然越过岐山。此则习见史料可揭示问题,仍然有二。1.周行分封,原本应当授民、授疆土。所谓“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今经文公“以兵伐戎”,方始拥有(授疆土);又经文公“收周余民”,才得仿佛(授民)。秦之立国,多靠自身努力,初步完成,便在文公。而秦之获封,初始无土无民,又再次显示行封者实际无力控制封赐地域,封赐话语仍应出自平王而非携王。2.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当平王二十一年,也即携王二十一年。这一年,发生“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之事。晋国在晋文侯时期,西向攻占了河西不少土地, “是秦晋之兵合,而戎与携王皆败”。 由此而言,秦文公东伐至岐,实际是与晋国开展的东、西向行动。秦所收“周余民”,相应包括原携王统治的周民之一部。 而“岐以东献之周”,既反映秦尚谨守与周所立誓约,又在某种意义上是晋西向用兵并主导相关地域政治背景下的被迫之举。清人顾栋高云“可见平、桓之世,晋未灭虢,东、西周犹通,封畿号令犹令于西土;虢、郑遗地之在畿内者,尚无恙”,“是时周之号令犹行西土,虢、郑懿亲虽从王东迁,而其故封无恙,呼吸可通”。 其实,晋国一度在宗周地区积极行动并对峙秦国,与遏制秦越过封域东进多有关联。秦晋对峙,实际早在晋文侯时期,端倪已现,且当不晚至“晋献公-秦穆公”之时。
《史记》卷五《秦本纪》下文提到:“(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集解》引徐广曰、《正义》引《括地志》多记神异传闻及立祠情形。 如果留意具体活动区域,这实际反映的是秦渡过渭水,向渭南南山、丰水一线活动。相较于《秦本纪》所述,《六国年表》概括文公事迹,特别表述作“营岐雍之间”。 秦不仅在文公时期实现真正立国,而且此时便已开始突破封地,向外扩张了。后一重要变化,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按秦文公二十一年(公元前745),当晋文侯三十六年。是年,晋文侯去世,子晋昭侯即位,封季父成师于曲沃。至文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39),潘父杀晋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成师,由此开启晋国大宗翼城、小宗曲沃二系之间长达六十余年的君位斗争。 文公于“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反映秦国成功突破既有封域,开展“营岐雍之间”的新事业。然文公再次“东进”,又是在晋国宗室二系爆发激烈内争以至无暇顾及西土的背景下进行的。
文公去世,宪公即位,“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 “荡社”,《索隐》引徐广曰、梁玉绳皆以为在杜县界, 今西安南郊北沈家桥村遗址附近。 所记可解释如下:秦于宪公二年进攻该地,三年会战中击败亳王,攻陷据点。亳王所率奔戎亳人稍后或返故地,秦在九年后再次伐戎,并占领该地。这显示宪公于渭南继续东进,并越过了丰水。当时,周室无力控御西土,晋国又深陷持续内争,秦高举“逐戎”大帜,渐据“岐、丰之地”的渭南区域。
幽王去世后,从“周二王并立”,发展到平王东迁、退出宗周,并否认携王的政治合法性,周室在较短时期内发生相当剧烈的政治变动。这客观上为秦东向扩展,据有宗周故地以为立国基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伴随“于是乎定天子”“始启京师”“杀惠王于虢”的晋文侯去世,晋国开始陷入二宗内争的长期动荡。一度在宗周故地出现的晋、秦并峙之局,不复存在。将“岐以东献之周”的秦,审时度势,相继开始沿渭水以南东进,“营岐雍之间”,并由此渐至河西。综上言之,秦、晋在关中的对峙与抗衡,可以追溯至两周之际。秦、晋竞逐,自秦立国之始,便是外部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探析“周二王并立”与秦为诸侯史事的复杂背景及其具体经过,不仅有助于在更宏观的历史视野下厘清秦早期建国史的个中曲折,而且有益于从地缘政治层面重新审视东周史的开启。
五、关于《左传》《史记》的史料、叙事与年代学问题
先秦史料向来有限,在积极吸纳新出材料之际,学术研究仍需要立足常见的传世史料来寻求观点突破,这是由材料本身是否能反映先秦历史的基础性问题而决定的。最后,本文从《左传》注疏、《史记》撰作出发,在理论层面围绕史料学、历史叙事、年代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先说《左传》。在史料学层面,由于《史记》对先秦历史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记叙,且文字朴实简洁、平实易晓,历来被学人视作进入先秦史的便捷门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太史公广泛参考先秦典籍,但同时对《秦记》等材料也多予重视,由此形成一种自成体系且较为自洽的历史记载脉络。其中,《史记》的一些内容与《左传》《国语》存在较大差异,而《左传》《国语》可信度更高,携王之立便是显例。这提示我们,使用《史记》先秦部分时,要充分重视《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
至于《竹书纪年》,由于史料价值重要,既往与《史记》等其他材料比对时多有依据之处。 近代以降,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王修龄等学者还提供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新辑本。在充分参考同时,《竹书纪年》文字审读仍应回归引文的原始出处所在,并对引文的“具体环境”进行勘查、关注引书体例。《春秋左传注疏》的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在史学研究中常被征引,但从经学、文献学角度关注二者的基本义例,仍旧有其必要性。孔氏《春秋左传正义》涉及此前对南北朝及隋代经学研究的参考与评述,故其中不少引文并非孔氏直接征引典籍,而是来自于所引前人经学著作本身的征引,并夹带有前人注解。通过对《春秋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周二王并立”条的重新复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论断:应注意回查学术研究时所利用辑佚本的原始出处;涉及“十三经注疏”等核心类典籍时,须更细致总结经书的注疏体例,对论述结构、引书结构有更确切的把握,并细致检查可能存在的错讹,开展必要的文本复原,由此方能使史学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史料学、文献学基础之上。
在历史叙事层面,不同典籍基于材料来源与立场角度会呈现不同的叙事侧重。除了史料学层面的分析外,《史记》与《左传》等先秦文献在历史叙事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值得认真总结。而先秦典籍内部的历史叙事差异同样存在,如《系年》更偏重西周、东周的历史接续,并重视晋在两周之际的历史作用;又如《国语》《系年》记录与幽王交战是缯、西戎,而不及西申,也应当多予比对思考。
在年代学层面,两周之际所涉周王室编年,主要依靠编年类史籍,《系年》《竹书纪年》而非《史记》发挥了更重要作用。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史记》两周之际叙事及编年的再认知。
再说《史记》。在史料学层面,太史公搜集考辨大量材料,进而形成对先秦历史较为系统化的论述,是后人建立对先秦史总体图景认知的重要参考。《史记》在利用各类材料进行撰作时,有自己的考辨取舍与体例安排,加之兼存异说,以尽可能保存材料,故而《史记》与外部史料群,《史记》内部的本纪、表、世家、列传彼此之间都存在一些差异,可分称《史记》“外部文本差异”与“内部文本差异”。细致比勘并分析各类差异,恰恰是理解《史记》撰作理念、把握史事面相的路径所在。《史记》重视《秦记》等秦系史料,形成一套较为自洽的史料体系。同时,《史记》世家部分的史源既有不同,又与《左传》《竹书纪年》多有可以对照之处。即便如此,在开展历史叙事分析前,我们首先应对基本史料做好考证辨析。如“赐之岐以西之地”为人所常见熟知,但从东汉起便出现一些不确切的认识或误会,历代相沿。这种情况值得高度重视和反思。
在历史叙事层面,《史记》所载东周历史以《秦记》为主而辅以其他,《秦记》虽史料价值很高,但不仅“文略不具”,而且还存在以战国崛起及秦统一来解释甚至重构秦史、东周史的历史叙事特征。这需要参考其他新、旧史料细加审辨,才能体察。《史记》存在的历史叙事问题,实际涉及面还要更广一些,不限于秦史部分。这恐怕不能简单归于司马迁刻意为之的“制造”“书写”,而更多是受到所参考材料本身的叙事模式和史事建构的影响。太史公恰恰是区分各类史料的价值等次,并尽可能保留它们的叙事样貌,才会形成《史记》所呈现的现今形态。《史记》记两周之际,呈现“周—秦”的结构性叙述,可称“周衰秦兴”模式。这一叙事不仅见于《秦本纪》,实际横贯各世家、表、书,彼此皆有照应。此类关涉历史整体把握的结构性叙事,也应予充分重视。此外,《史记》的秦史叙事偏重于秦之内部,研究须注意“天下”秩序下“外部的结构性因素”。今日近现代史研究多留意此方面,先秦史实际也是如此。熟知的“曲沃代翼”,其实就与秦之东进有较密切联系。
在年代学层面,由于史料来源及择取倾向,《史记》记两周之际的周王室系年较为简略,然而秦君系年有较原始的材料依据而更加详细。秦君系年虽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可信,不宜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更改君主系年。
综上,揭剥出《左传》《史记》的历史叙事脉络及其旨趣,或许并非今日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指向,在史料学层面作背景、年代、地理与政治实践的多重“硬考据”,仍然有望透过历史叙事而得见史实揭示更为真切的历史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二王并立与秦为诸侯的实证探讨,不可或缺。只有始终坚持从实证出发,才能为史学理论方法的省思提供直接性的支撑与启示。
责任编辑:戚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