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晚年奉武则天敕令写的《孝经》草书,连董其昌都称“奇绝”,比张旭的狂放、怀素的瘦劲更经得住琢磨——
它没有野马般的狂乱,却有兰花般的典雅,每一笔都藏着二王的古法,每一个字都透着魏晋的气韵,堪称草书里“最有底蕴的天花板”。
武则天的“国礼订单”:孙过庭用毕生功力写《孝经》
武则天在位时,最爱收集“有二王味道”的书法。她听说孙过庭这号人物——
出身贫寒,没师傅教,自己买字帖啃了二十年,把王羲之、王献之的笔法摸得透透的,连唐高宗都夸他“小字足以迷乱羲、献”。
于是,武则天专门下了道敕令:“让孙过庭写部《孝经》,作为大周国礼。”
孙过庭接到命令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但他知道这是“给皇帝写的”,必须拿出压箱底的本事。
他每天凌晨就起来研墨,磨到墨汁发稠才动笔,每写一个字都要反复调整:“’孝’字的’土’要用中锋,这样才厚实,像父母的怀抱;’子’字用尖锋挑一下,像孩子扑进怀里,既有意义又有姿态。”
三个月后,《孝经》写成了。武则天展开卷子一看,眼睛都亮了:“这字既有二王的圆润,又有你自己的端庄,比张旭的狂草稳,比怀素的草书润,刚好当国礼!”
于是,这幅《孝经》被当作“大周国礼”送给了日本遣唐使,后来流传到明朝,祝允明补了缺损的一小段,现在藏在台北故宫。
孙过庭的“自学奇迹”:比张旭、怀素更懂“古法”
孙过庭和张旭、怀素最大的区别,在于“起点”——张旭有师傅(比如陆彦远,王羲之的七世孙),怀素有高僧指导,而孙过庭是“野生选手”:
没钱买好字帖,就去书店站着记,回家凭记忆写;没师傅教,就把二王的字帖拆成“笔画”“结构”“气韵”三部分,逐字琢磨。
就这样,他学了二十年,终于把二王的笔法“吃”透了。有人说他“比张怀(张旭、怀素)更懂二王”,不是吹的——
张旭的狂草像“酒后放歌”,怀素的草书像“瘦竹临风”,而孙过庭的草书像“月下弹琴”:
中锋运笔让字有“肉感”,尖锋挑笔让字有“动势”,侧锋调整让结构“疏密得当”,每一笔都“有来头”。
比如《孝经》里的“孝”字:上面的“土”用中锋写得敦实,像父母的肩膀;下面的“子”用尖锋轻轻挑起,像孩子扑进怀里——既有“孝”的本义,又有书法的美感。
再比如“经”字:左边的“纟”用侧锋写得流畅,像丝带飘动;右边的“京”用中锋写得端庄,像城楼稳固——动中有静,稳中有活,这就是孙过庭的“古法智慧”。
为什么说《孝经》比张旭、怀素更“高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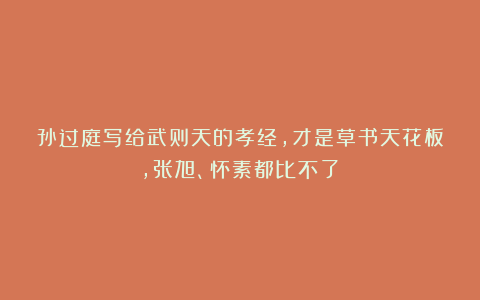
很多人觉得“狂草才是草书天花板”,但孙过庭的《孝经》恰恰相反:它不狂,却“越看越有味道”。
第一,草法“最纯正”。张旭的狂草像“即兴发挥”,怀素的草书像“刻意瘦劲”,而孙过庭的《孝经》每一个字都符合“二王草法”——比如“之”字的写法,来自王羲之的《十七帖》;
“心”字的结构,脱胎于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学它,就像学“草书的拼音”,基础打牢了,再学狂草才不会“走歪”。
第二,气韵“最典雅”。孙过庭写《孝经》时,用了“疏密开合”的技巧:有的字写得紧,像含苞待放的花;
有的字写得松,像展开的花瓣,整个卷子的气韵像“流水”一样连贯。
而张旭的狂草像“瀑布”,虽然壮观但少了“余韵”;怀素的草书像“竹竿”,虽然挺拔但少了“血肉”。
第三,经得住“时间考验”。台北故宫的《孝经》真迹,虽然有一小段缺损,但祝允明补的部分几乎看不出来——
祝允明是明代草书大家,学孙过庭学了一辈子,补笔时用的是“孙式笔法”,结构、气韵和原卷完全一致。
这说明什么?孙过庭的字“有规律可循”,连后人都能“无缝衔接”,而张旭、怀素的狂草,后人想补都补不了,因为“没规律”。
现在学草书,为什么要从《孝经》开始?
很多初学者一开始就学张旭、怀素,结果越写越乱——因为狂草需要“控笔能力”和“草法基础”,没有这些,写出来的字就是“乱涂”。而孙过庭的《孝经》不一样:
草法“有注释”:每一个字都有“现代字对照”,初学者能看懂;
笔法“有方法”:中锋、尖锋、侧锋的用法都写得明明白白,学了就能用;
结构“有规律”:疏密、开合的技巧都藏在字里,学了它,再学狂草就像“会走了再跑”,稳得很。
草书的“天花板”,从来不是“狂”,而是“稳”
其实,草书的“高级”,从来不是“写得有多狂”,而是“能不能把古法用到极致”。孙过庭的《孝经》就是这样:
它没有张旭的“野”,没有怀素的“瘦”,但它有“魏晋的雅”,有“二王的稳”,每一个字都透着“用心”,每一笔都透着“功夫”。
就像董其昌说的:“尤可宝也。”这样的字,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它不是“一时的惊艳”,而是“一辈子的耐看”。
你觉得,草书的“天花板”是狂放的张旭、怀素,还是典雅的孙过庭?为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聊聊“草书里的底蕴”。
(图文资料来自网上,侵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