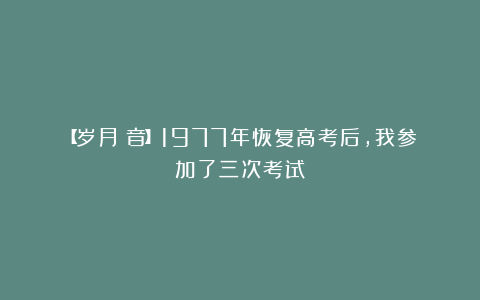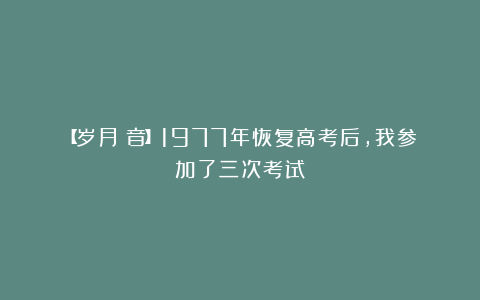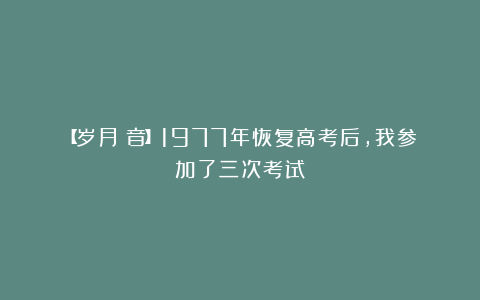|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参加了三次考试,深深感到了其中的艰难。
1976年秋,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这一决定像惊雷一样响彻神州大地,从老三届到应届生,青年男女纷纷报名参考,我也像曹操八十万大军过独木桥一样挤在其中。据说那一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投档率只有5%,而录取率为3.5%,竞争非常残酷。
当时我在村里当民办老师,教初中语文。学校有十多个青年教师,大都跃跃欲试,有报大学的,有报中专的。
报名在10月下旬,考试是12月7、8、9三天,地点在太原市南郊区北格中学,十多个教室都成了考场。
第一天上午考政治。试卷发下来浏览了一下,发现试题都会做,不由暗自高兴,很快做完举手要求交卷。监考老师说开考未过半小时不得交卷,以为我不会做呢。记得考题有大寨的经验是什么、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什么、十一大确定的路线是什么等十多道题,题量大,并不难。过了半小时,我交了卷,是所在考场第一个交卷的。
在骑车回村的路上,心想政治题这么简单,考大学也太容易了,高兴得回到学校和老师们聊了一会儿就回家吃午饭。不料饭后躺在炕上睡着了,两点多我妈进屋发现,才赶紧把我叫醒。我一骨碌爬起来骑上自行车没命往考场赶去,因为下午两点半开考,超过三点就不允许进考场了。
下午考语文。我气喘吁吁赶到考场时已接近三点,坐到位置上后,心砰砰直跳,过了好几分钟才感觉平静了些。看了看试卷,共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一部分是作文。
基础知识共三道题,一是用比喻和反问修辞各造一个句子,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言论。这个简单,几分钟就做完。二是修改病句还是改错别字,也没难度。三是文言文翻译,内容是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故事。这段文言文比较浅显,只有一个“夷”字是难点,只要懂这个字的意思,翻译就很容易。“夷”是指英国或英国人,如“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道题也几乎可以拿满分。考完后,听好多人说被“夷”字懵得头都大了,其实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知道这个知识点,面前就竖着一堵墙。
第二部分是命题作文,两篇选一。一篇题为《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一篇题为《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我选第一篇开写。但是因为迟到近半小时,别人考了半个多小时我才开始,担心时间不够用,慌乱得咋也捋不出头绪,作文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换成第二篇,仍然不顺利。于是在两篇作文之间来回转换,把两篇都写了,最后选了一篇抄好交卷,感觉很不理想。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考题大部分会做,可是有个求速度的题,看似简单却做错了,另外最后一道题只做了一部分,没做完。尽管如此,考完互相询问着比较了一番,自认为在文科考生中算考得不错。
下午考历史,第三天考地理,这两门考得都一般般。那时考试没有复习资料,史地高中没讲过,全凭考前临时准备,考得不理想也在情理之中。记得一道地理大题是,从南海出发到英国伦敦要途径哪些大洋、海湾、海峡、运河等,现在看来这么简单,但当时就是做不来,可见基础之差。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南郊区委门口对面墙上出榜了,公布了达线的名单,急匆匆骑车去看,发现榜上有我。那年我们北格中学75届高中生达线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八班的刘德喜,一个是姓韦还是姓什么的同学,一个就是我。在达线成绩未公布之前,考生已填报了志愿,因为感觉良好,我填报的是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吉林大学。
第一年高考公布的达标数,是实际录取的1.5倍多,也不控制分数线,只要达了线,录取哪个考生都可以,据说走后门现象很严重。南郊区排名第一的何耀光,也仅仅被太原师专录取,排名第四的胡成林竟没被录取。我在村里,天天听广播电台说公平公正录取,但一直等到我们村有个排名80多位的插队生也接到录取通知书了,还是没有我的音讯。
1978年高考,是四月下旬报名,七月考,我五月初就领取了准考证。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我抓紧一切时间复习,一心想今年考个好成绩。
五月上旬的一天,郝仁信校长告诉我,太原市南郊区教育局发出通知,要在全区民办教师和代缺教师中,通过考试录用60人为公办教师。郝校长让我参试,我说已领准考证准备高考,他说两者不矛盾,参加转正考试权当练兵。郝校长为了我好,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填表报了名。
没几天,通知我去小店考试,只考语文和数学。这次考试心情很放松,特别是命题作文《黄牛颂》,思路通畅,连草稿也没打,一气呵成。这次考试有1500多名民办教师和代缺教师参加,有二十来岁的,更多是三四十岁的,也有五十来岁的,都想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
一周之后,公布了考试结果,学校通知有我,要求去小店体检。
那天,北格公社考上的十来个人体检完在小店医院门口等车来接,只见小店中学的胥民生老师急匆匆走过来问带队的魏徳恒主任,谁是李文清?胥老师原是北格中学的语文老师,没带过我们的课,但我认识他。我问胥老师什么事,他问这次作文你怎么写的。考试刚过去一个多星期,情况还记在心里,我向胥老师简单说了说。
我说完,他说看来那篇作文就是你的,你的语文成绩全区第一。胥老师是语文阅卷组长,他是来核实第一名语文成绩的。
魏主任和十来个考上的人都在跟前站着,全听到了胥老师的话。我又问我总分多少,他看了看手里的名单,说我的总分是全区第九,北格公社第一。
这是我年轻时几次参加公考考得最好的名次,虽然考试范围不大,1500多人考了个全区第九,也算个高兴的事。但我参加考试是来练兵,目的不是转公办老师,所以没多在意。体检完后,我就由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变成一名挣工资的公办教师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没想到考这么好,一下子有了点小名气;不高兴的是,我直接失去了参加1978年高考的宝贵机会。
转成公办教师后,公社文教办通知学校领导,不准我再参加今年高考,而派我去当监考老师。在那个师资缺乏的年代,一是怕我考上大学离开学校,二是觉得我公考考得好,是个培养的苗苗,不愿意放我走。但现在想,当时我手里有高考准考证,谁能阻止得了我进考场呢?然而那时年轻,只听文教办安排,稀里糊涂到小店当了监考老师,没能参加当年高考,如果参加了,说不定就势考个好大学呢。
转为公办教师后,学校让我改教初中数学。正赶上公社文教办组织讲课比赛,全公社18个村的初中学校都派教师参加,我和另外两个老师代表学校去赛讲。比赛采取淘汰制,每次赛讲,教室前面坐着学生,后面坐着十几个评委。记得讲了四轮后,比赛结束,我是个新兵,参加比赛只为学习提升,得什么名次压根儿没想。
秋季开学前一天,全公社教师在北格中学集中开会传达文件,同时安排新学期工作,校园坐满各校教师,但大家基本不太熟悉,互相之间很少交流。安排完开学工作后,一位领导宣布前半年讲课比赛结果并颁奖,当三等奖、二等奖颁完,人们正眼巴巴期待一等奖是谁时,竟然听到获得一等奖的是刘晋维和李文清!
刘晋维老师是流涧学校的数学老师,48岁,正值壮年;我走上台领奖时,台下议论说:“呀!这么年轻!”那年我21岁,看上去还像个学生。从此,我成了公社文教办领导眼中的好教师,加上公转考试的成绩,现在话说位列当时的名师。我编印的复习资料成了抢手货,连公社文教办领导也向学校领导索要,给他们家或亲戚朋友的孩子使用。
不久,霍凤台副校长调到我们学校,分管教学业务。有一天,霍副校长悄悄跟随学生们走进我的教室,采取不打招呼的办法听课,连续不定期听了三次,他对我的课予以肯定。我和他逐渐熟悉后他才说,第一次听完课之后,怀疑我知道他要来听课,于是事先把教案背下来了,再听了两次之后,发现我每次都不看教案,不看课本,不仅熟练地讲完课,而且连布置作业都能随口说出第几页第几题,根本不需要翻开课本。
那时的我,记性出奇得好,晚上备完课就印在脑子里了,第二天去讲课,不需要看书和教案。霍凤台副校长是一个懂教学业务的领导,听课之后,他在学校会上表扬了我。
我带初三毕业班的数学,那时初中毕业既可考高中,也可考中专,所以,学生们都很用功。我带的毕业班,有不少同学考进当时南郊区重点高中小店中学,有五六个学生数学成绩名列前茅。
在收获这些教学成果的同时,我的第二次高考却流产了。
1979年高考报名开始我报名时,公社文教办竟不允许。后来了解到是区里的意见——去年公考转成公办教师的,不允许参加高考,要作为师资培养,以后会统一安排进修学习提高。
转为公办教师后,我每月的工资是36.5元,而当民办教师时每月可挣30个工分再加19.5元的补贴,因此总的收入是明显下降了,心里不爽。那时我们村分红值高,一个月30个工分,每个工分两块五六,后来逐年提高,1980年达到三块七毛钱。加上1977年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十来个青年教师,有几个已考上大学或中专离开了学校,这使我参加高考的愿望十分强烈。
我去区教育局找领导。领导网开一面,我于得以报了名。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一直铭记着那位领导对我的好。
1977年、1978年高考内容相对不难,考生大部分是往届生;1979年主要是应届生,试题难度也有所提高,考上的可能性比前两年小多了,对我这个老考生来讲,形势不容乐观。
我把初三带到毕业已是五月,离高考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复习时间不够用,只好白天晚上连轴转,吃住在学校。那时不像现在有老师辅导,社会上还有专门辅导班,有好多模拟题,还有海量复习资料。我当时只有两本合订本复习资料,一本理科的、一本文科的,一共不到100页,语文、历史、地理、英语等合并在一本资料书里,另外还有一本很薄的政治解答题。
在学校里,学生不会的能问我,而我不会的没地方问,只能自己琢磨着复习。早晨背政治,上午看史地,语文、数学全靠平时打下的基础。有时有人转来一些练兵题或外地往年的试题,就认真去做,思考其中的奥妙。这样复习了一个星期后,感到十分疲劳,早晨天刚亮起床背政治,背着背着就打盹。挺不住的时候,就用冷水抹一把脸继续背,如果躺下,瞬间就可以睡着,不知睡到何时。我是硬凭着意志,支撑着复习了两个月。
考试终于来临,是7月的7、8、9三天。因为我上年公考转成正式教师,就不能在北格中学考场而要去小店考场考试。6号下午骑车到小店看了考场,找见了自己的教室,晚上回到家吃完饭早早睡了。我们村到小店30多里地,平时骑车要一个多小时,我设想明天早点出发,提前到考场。
一下雨,村里村外的路上都是泥泞,根本不能骑车。怎么办?步行30里去小店,最少要两个半小时,到了考场就开考了。没有办法,只能车骑人了。吃了点饭,我挽起裤子赤着脚,扛起自行车出发了。
平时去小店,都是出村向东到南格村上柏油路骑车向北,村里到南格村八里土路,扛上自行车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再骑到小店根本赶不上考试,这显然不可行。怎么办?我扛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想。走到村口,突然想起了村北三斗渠通往西北格村,渠堰上如果长着草就可以骑车到西北格,西北格通柏油路,可骑车到小店。但是如果三斗渠堰上没长草,肯定不能骑车。
在泥泞中扛着自行车、淋着雨,从村东向北深一脚浅一脚朝三斗渠走去。三斗渠是一条较大的退水渠,是我们村与同过村和三贤村的分界,太原城里的雨水就是通过这条渠排往潇河的。村口离三斗渠两里多地,我一拐一滑走在雨地里,离村越来越远。平常我骑自行车,这回犒劳犒劳自行车,让它骑骑我吧。
到了三斗渠,雨下得越来越大,但是不到一米宽的渠堰上果然长着草,暗自庆幸老天爷关照我。
我把自行车扛到渠堰上,跨上车急匆匆朝前骑去。渠堰上的草,大部分是扁平的稗子草,有半尺来高,我有意识地在草上骑行,不让泥缠铰进轮子里。时值盛夏,两侧的玉茭子已长得很高,很多玉茭叶子横伸着挡在面前,有的被雨水淋得歪斜到渠堰上成了“拦路虎”。我一会儿猫腰低头插缝往过穿,一会儿用胳膊拨开那些“拦路虎”拼命往前蹬,上身的隐格淡白色半袖衬衫、下身的单裤,很快全都湿透,像个真正的落汤鸡。
这条渠堰平常没人走,只有汛期才有巡渠的人来。平常不下雨的天气,一个人步行或骑车在渠堰上,面对四周密匝匝望不到头的庄稼,也会感到害怕。因此我下雨天骑行在不见人影的庄稼和杂草间,说不害怕是假的,何况三斗渠里满渠洪水,稍不留神不是栽到洪水里,就是冲下斜坡,跌落渠里。
我心里只想去小店参加考试,顾不上其他,全神贯注盯着前轮胎,确保又快又稳向前冲。要不是高考这个梦想支撑着我,就是平时不下雨给我钱我也不会来这寂静得让人害怕的地方。
骑了四十多分钟,我终于冲到了西北格的柏油路上,西北格到小店全是油路,雨再大也不怕了。看看身上,全是雨水和玉茭子花粉,白白的衬衫上滚满了蚜虫,脏得不成模样。我根本不顾这些,拐个弯朝北快速向前骑去。
在泥泞的雨地里扛了两里多自行车,冒着雨在杂草丛生的渠堰中穿行了十多里,这种遭遇,我想,在当天所有考生中我应该是唯一的。还没考呢,老天爷先对我“天考”了一把。
快骑到小店时,雨停了,身上的衣服也被风吹干了。我在开考前二十来分钟赶到了考场。拍了拍衣服上的蚜虫和泥点子,等了几分钟,我进了教室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这个考场有三十多位考生,上午考语文,基础知识题记不清了,作文是根据给的几段文字材料,组织编写一篇文章。我这篇文章做得一般般。下午考数学,数学是我的强项,基本都会做,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前十几分钟做完了所有试题,等待着交卷。
监考的应该是位数学老师,在我做题的过程中,她走来走去巡视着考场,其间几次走到我跟前看我的答卷,我很反感,影响我的心情。铃声响起,我拿起卷子去讲台交卷,这位监考老师却对我说,这个考场数你做得好,可惜你少做了一道题。
她打开卷子翻到最后让我看,说这道题你没做。我一看,试卷和报纸一样是正反面印着题,我没看见最后一道题。这道题18分。顿时,我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这么倒霉呢!心情变得糟透了。心里埋怨这位监考老师怎么不提醒一下呢?就这样,我平白无故地丢了18分。
第二天上午考政治,做完等待打铃交卷。在交卷前几分钟,有个平时有影响力的和我一样在去年转为公办老师的好朋友交卷后在门口说,第三道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判断题答案应该是错的。我的座位在门口,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而我做的答案是对的。听了这句话,心里翻腾起来,一时分不清楚该判断对还是错。在打铃之后,我在答题“对”字的前面加了一个“不”字,成了“不对”。结果导致我又丢了12分。
这位仁兄也真是的,你去哪里不能说,为什么偏偏要在门口说让我听见呢?你等大家交完卷再说不行吗?为什么偏要在我交卷的时候说呢,天呐!这不是命运在作弄人吗?现在想来,还是自己判断力差所致。
过了大约一个月,高考分数出来了,我考了309分,本科是310分。我的天呐!就一分之差,让我与本科擦肩而过!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我觉得自己的数学分数有问题,提交了查分申请,回复无误,只好认命,最终被太原师专录取。
1979年9月下旬我去师专报到,开始三年政史专业的学习。一个多月后,与学校学生处长混熟了,有幸看了我的高考档案。天呐!命不可违!翻开我的数学试卷,立即惊呆了,再一次认命!第八题是一道12分的数学题,只给了我4分。
那是一道证明题,我做了也做对了,为什么只给了4分?原来这道题印在试卷页面的下部位置,我做了一部分写不下了,就做到了背页的上半部分,并且在当页下端注明“接背页”,但判卷老师只对前页答题给了4分,翻开背页看我做的答题,对照答案证明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对的,可没给我一分,明显是没判这一页。为什么没判,只有天知道。
再看,我的查分申请也在档案里,注明各小题分相加是309分。原来查分就是查小题分相加是否等于总分。
第一个学期,心里翻腾着想退学。有同学说,退了学,明年连名都不让报;就又想着转专业吧,想去数学系。我托人去说情让我见见教务长,很快他告我,说好了去见吧。一天中午,看见教务长在办公室,我就去见了说明我想转数学系的想法。教处长大腹便便,操着一口晋中话,听了我的诉求,对我说:跨科太大,不能转。
退不得,转不得,只好无可奈何待下去。看着学校破破烂烂,还听说一些老师是从普通中学抽来的,越发想退学,心里想着还不如回村继续当民办老师。没有什么比不愿意、不开心更加痛苦的了。将近一年时间里,我被忧忧之浪拍来拍去,直到第二学年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回想当年高考,怀揣着梦想,不懈地努力,无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左拐右拐,终归像逆水行舟,其中艰难,只有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