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东山拜谒乔冠华墓
图 片:选自网络(部分)
初夏的一天,我专程来到苏州东山镇,探寻并拜谒乔冠华的墓园,看看这位杰出的乡贤到底魂归何处?忝列乔冠华研究会有年,除了几篇文章外,庶无贡献,不禁汗颜。 今年又值龚澎诞辰 110 周年,据说县里准备在香港举办图片展,此时不去,更待何时?我对乔老爷一直心向往之,情寄托之。高处不胜寒,他晚年过得并不顺,受审查久无结论,又疾病缠身,我不禁生出了几分同情,更加坚定了探墓的决心。
这是一次个人行为。年过七旬的我,背个双肩包从旅馆出发,倒了三部公交车,坐了 76 站,终于来到东山。腰酸眼花屁股疼, 口渴肚饥汗涔涔。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东山人对乔墓几无知闻,因而脑袋郁闷心口疼。他可是对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外交部长啊!换乘了第二趟公交车后,车入东山,就开始问人,乔冠华墓在哪里?竟然无人知晓。我问的可都是中老年人啊,一个个头摇的拨浪鼓似的,“啥人? ”“乔冠华!”“不知道。”我说,他可是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啊!可见青史留名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后来我说到东山华侨公墓看墓园,一位 70 多岁的苏州阿婆反问 我:“细雨濛濛,到公墓干什么?不要信邪教,不要信死人,侬要吃亏的!”我无语,心口更疼了。多亏司机解了围,说不要到东山,到桥头站下车,转 627 路去找。
上了 627 路,又开始问人,仍是没人知 道。627 路总计 36 站,人越下越少,心情越来越焦虑,道路两边的枇杷树飞快地一掠而过。于是再搜百度,又打电话给友人。东山一线带有杨湾的地名有四个,带有“东山 ”的站名有九个,纯粹叫“湾 ”的有金湾、槎湾、杨湾等三个,我该在哪站下车呢?愁的脑袋都大了。 最后,车上除我而外,只有一个老者,攀谈中知道他与我同岁,立即拉近了距离。他说,到华侨公墓,应该在“轩辕宫 ”站下车。我的天哪! 既非东山,又非槎湾、杨湾,于是带着疑窦下了车。
下车后,艳阳高照,雨早停了。“杨湾村党群服务中心 ”几个斗大的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幸好村部有人。值班的同志告诉我,从村部西侧的岔路步行 20 几分钟就到了。此时脑袋不胀了,心口不疼了, 如同注射了兴奋剂,立即打道上山。山,坡度不大。满山遍野的枇杷熟了,如同金色的小灯笼,小山坡被点缀得金灿灿的,又如同一个个悬挂枝头的小香囊,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甜味,更像一颗颗金色 的眼珠眨巴着,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外乡人。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迤逦前行,汗水湿透了衣裤。转了几个大弯, 终于见到了指示牌:“东山华侨杨湾墓地 ”。心头一阵狂喜。但见路向前方延伸,看不到尽头,到底还有多远,我的体力能否支持呢?路边的枇杷眨动着金色的眼珠,叩问着我的决心。想问人,无人可问。偶尔可见一辆从城里来买枇杷的车飞驰而过,将我远远的抛在后边。正午的太阳热辣辣的,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早已汗流浃背。忽见路边的路长公示牌,立即将电话打过去,可惜无人接听,只好奋力前行,终于见到了公墓大门。虽有卷闸门,但大门洞开;虽有值班室,但空无一人。满怀希冀的前行,终于见到了山顶处的楼房,原来正是公墓管理处。
管理处有两人值班,人倒挺客气,应答有笑脸。还卖了一点交情, 说是名人墓园,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你们是家乡人,我们可以照顾。 墓在九区 21 排,靠近停车场。我们要值班,请你自 己去找。我自然是十分感谢,但心里明白,级别不够,来头不够。
乔冠华墓就在停车场边上。墓碑是用黑色大理石雕刻的,像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正中是金色的大字:乔冠华龚澎之墓。左上方是两人并肩仰望的照片,极为传神。二人目光坚定,仰视前方,才子的坚毅,佳人的憧憬,跃然石上。照片下面是金字雕刻的伟人赠联:“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二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左下方是子、女、婿、媳及孙辈的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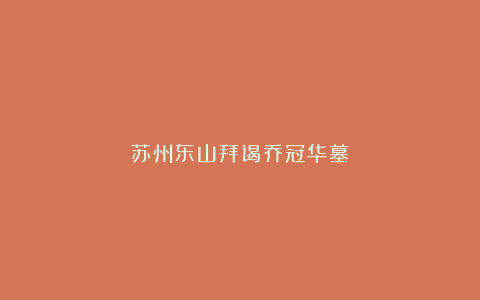
最有意思的是墓碑上的三个“澎 ”字,乔夫人龚澎,孙子乔澎,媳妇姓彭,也写作“澎 ”了,是媳妇对婆婆尊敬有加,连姓都改了,还是石匠的手下之误?就搞不懂了。碑前是一本翻开的大书, 上刻夫妻二人的生卒年月。乔老爷一辈子爱读书,爱写文章,时事短评加上鸿篇巨制,威力强大,比得上一个坦克师。
整个墓园占地约 20 几平米。墓前有香炉一,烛台二,墓后植松树六棵。墓园两侧,右边栽樱桃一株,小叶红枫一株,左侧栽樱桃一株,香樟一棵。树外有近一米宽的红花继木的篱笆墙,将墓园与外界隔开。整个墓园色彩明丽, 美观典雅,活泼灵动。墓地建在山坡最高处,坐北朝南。背靠巍巍群山,俯瞰太湖景色,可听万壑松风,可赏白云蓝天。渔舟唱晚,响穷太湖之滨;东山花香,味醉游子之心,实在是绝佳的安息之所。墓园无鲜花卖,本人采撷了一束野花,恭敬地献上,并磕了三个头方才离开。
我并没有离开。总觉得既然来了,应再去看看章含之为他修的原墓。于是又去询问管理处人员,她又为我指明了方位。但作为陌生人, 寻找也颇费周折。其实就在新墓东面 200 多米远的山坡上,被称作老区。原来的华侨公墓规模很小。乔老爷 1985 年下葬时,也只能偏安一隅了。后来墓园逐渐向西扩建,整个山坡都被建成墓园了,现有十几个区,规模挺大。
原墓占地亦有几十平米,卵石铺地,墓基以大块碎石垒砌。主体建筑为西式斜碑墓,20公分高,碑上大书“乔冠华之墓 ”五字,下面是横行书写的乔老爷的明志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碑前戗一石板,文曰,“此墓穴已迁至本墓园停车场 ”,并注明系 2009 年 4 月 15 日迁移,此时距章含之去世已有 一年了。背后有一等宽的长方形坑,已用水泥抹平,可能是原来放骨灰盒的地穴。空旷的墓地,迁走的骨灰,简陋的装修,呼啸的风声,物是人非,令人唏嘘。
值得说道的是,墓后栽有两棵十余米高的雪松,树干直径已有 30 多厘米,不由得使人想起了“ 生于幽谷,迁于乔木 ” 的诗句。她委身乔木,矢志不渝,作为自己一生的归属,章含之是刻意为之吗?西边的一棵高大挺拔,直插云霄,象征男主人顶天立地伟 岸旳身躯,东面的一棵在一米处渐分四杈,虬曲而上,颇像一个举手挥袖,翩翩起舞的曼妙女子。这是章含之的化身吗?
紧挨原墓的西北方向几米处即冠华老友李颢旳墓。李墓修于 1996 年,同样的西式斜碑墓,卵石地坪。台基三面无绿植,背后栽了八棵小松树。 四周是 12 根望柱,南北两面是八只威武怒吼的狮子, 算是镇墓兽吧。东西两侧各有两个胡人骑狮鼓乐俑,权当石翁仲吧。 斜碑上题刻二人籍贯与生卒年月,李颢 82 周岁,李夫人 100 周岁。
与乔墓不同的是,他们的骨灰放在斜碑下面。鼓乐俑咧嘴而笑,骑狮奏乐,憨态可掬。这样看来,李墓又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墓。李颢早年曾为年轻的冠华做过肠结核手术,是乔冠华与龚澎的婚宴的座上宾,交情真的不薄。解放后又往来不断。冠华故去后,李颢动用关系为乔老爷觅得东山华侨的墓地,两人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了。相隔十一年后,二人又比邻而葬,缘分真的不浅。
墓地参观完了。放眼远眺,但见群山苍翠,阳光灿烂,太湖浩渺, 烟波迷茫,鸟儿在蓝天掠过,白云在头上流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冠华的历史功绩也越来越被肯定,就像这满山遍野熟透的枇杷,果香四溢,香飘神州大地,味达五湖四海。
一年一度枇杷熟,一拨一拨追思人。敬爱的乔部长,故乡人民永远怀念你!愿乔老爷在东山安息!
(写于2024年5月)
该照片由作者拍摄于乔冠华墓园
【作者简介】徐杰凡,原名徐杰范,男,汉族,1948年11月生,江苏建湖人。1966年盐城中学高中毕业,遭遇文革,回乡劳动。后读师范,从教三十余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后,重拾旧时爱好,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篇。2016年与人合编《建湖县水利志》,为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