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文人的集体想象中,梅花早已被赋予固定的品格——它是孤高的隐士,是严寒中的斗士,是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道德象征。
直到苏轼的《定风波·红梅》出现,这株“好睡慵开莫厌迟”的红梅,以其慵懒、羞涩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姿态,彻底颠覆了传统梅花的形象范式。
苏轼在这阙词中完成的不仅是对一种花卉的重新诠释,更是对士大夫精神世界复杂性的深度挖掘,他让红梅成为了拒绝被简单定义的灵魂象征。
苏轼的《定风波·红梅》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当时苏轼被贬官在黄州,期间因读石延年的《红梅》诗引发了感触,于是作《红梅》诗三首,随后又把其中一首改制成词,并取调名为《定风波·红梅》。
《定风波·红梅》宋·苏轼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定风波·红梅》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这一背景为理解全词提供了重要线索。
面对政治上的挫折,苏轼没有选择传统士大夫要么激烈抗争要么彻底隐退的二元应对方式,而是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生活哲学——外在可以随遇而安,内在则保持精神独立。
这种思想在词中表现为红梅既能“偶作小红桃杏色”适应环境,又能保持“孤瘦雪霜姿”坚守本真。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
词作开篇便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梅花,“好睡慵开莫厌迟”中的“慵开”指花,“好睡”为拟人,“莫厌迟”绾合花与人而情意婉转。
这里的红梅不像传统咏梅诗中那样急切地凌寒独放,而是慵懒贪睡,迟迟不愿绽放。这种拟人化描写立即消解了梅花作为“岁寒三友”之一的严肃性。
就花开的时令而言,梅花理应开在百花之先,齐己在《早梅》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诗句;理应是报春的使者,李清照在《渔家傲·梅》中有:“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的佳句。
不曾想由于“贪睡”竟然延误了花期与桃杏同时开放了,所以说“迟”。梅花开晚了请求原谅:莫嫌疏懒晚放,莫厌姗姗来迟。与桃花同时开放是否切合时宜?“自怜冰脸不时宜”,梅花生就拥有冰清玉洁之姿,与姹紫嫣红的群花是不相宜的。
红梅似乎意识到自己洁白如冰的面容已不合时宜,这种自我怀疑的情绪在传统咏梅文学中几乎从未出现。梅花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的道德符号,而成了一个对时代氛围敏感、甚至有些焦虑的个体。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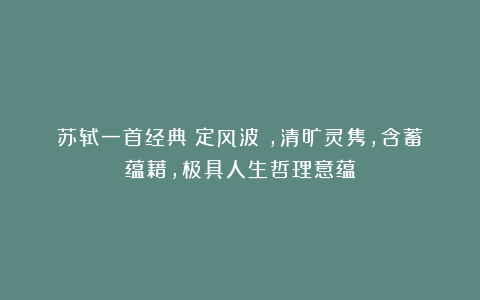
“偶作”三句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合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
当红梅“偶作小红桃杏色”时,苏轼用“闲雅”二字评价这种偶然的色彩变化。这绝非简单的赞美,而是对传统梅花审美的一种巧妙颠覆。桃杏向来代表世俗的艳丽,与象征高洁的梅花处于审美光谱的两端。
这里词人不说红梅天生是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接下来笔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苏轼笔下的红梅能够“偶作”桃杏色而不失其本质,这种色彩游戏暗示了雅与俗之间并非绝对对立。更为精妙的是,即便沾染了桃杏的红色,这株红梅依然保持着“孤瘦雪霜姿”的本色——外在的变化并未动摇其内在本质。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
过片三句继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虽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接上片的“尚余孤瘦雪霜姿”。
“酒生微晕沁瑶肌”承接上片的“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然是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
“休把”两个字一责,“何事”两个字一诘,其辞似有遗憾,其意仍然是为红梅作回护。“物态”在这里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
红梅本具雪霜之质,不随俗作态媚人,虽然呈红色,形类桃杏,乃是像美人不胜酒力所致,未曾坠其孤洁的本性。
苏轼在此既是对红梅的劝诫,也是对自己的提醒:不要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本心。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劝诫恰恰出现在红梅已经“随物态”(变化为桃杏色)之后。
这构成了一种微妙的自我解构:红梅既变化了,又未被变化所改变;它表面上顺应了某种潮流(“酒生微晕沁瑶肌”),实则坚守着自己的“梅格”。
这种矛盾统一恰恰体现了苏轼对复杂人性的理解——人可以有外在的适应而不失内在的操守。
“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词末对“诗老”(指前辈诗人)的批评尤具颠覆性。那些只知“吟咏”“绿叶”与“青枝”的诗人,在苏轼看来根本不懂得“梅格”的真谛。这里的批判锋芒直指将梅花简单符号化的文学传统。
苏轼反对的正是那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他笔下的红梅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隐士,也不是彻底的俗物,而是在两者间保持张力的真实存在。
从文学史角度看,苏轼对红梅的这番重塑具有深远的意义。他打破了咏物诗要么托物言志要么状物形似的传统,创造了一种能够容纳矛盾、展现复杂性的新型咏物范式。
这株红梅之所以历经千年仍令人耳目一新,正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象征,成为一个充满现代感的复杂文学形象——它提醒我们,真正的高贵不在于拒绝变化,而在于变化中保持自我;真正的坚守不需要刻意的标榜,而可以在表面的随和中默默实现。
「READING」
SICIZAJI
头条号|诗词札记百家号|诗词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