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苏联图-16轰炸机的坠毁事件至今笼罩在巨大的谜团之中,引发了无数争议。究竟谁对谁错,专家们始终没有弄清楚。时至今日,人们也对苏联当时展开的调查提出了诸多疑问。因此,让我们一起从事实出发,梳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苏联当局当年千方百计想要对这起神秘事故闭口不提。
这架军用飞机——一架中程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鄂霍次克海上空进行一次例行的训练飞行。由于技术故障引发的异常状况,飞机坠入了冰冷的海水中。机组指挥官、飞行员康斯坦丁·叶夫列莫夫成功将飞机迫降在水面上。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逐渐下沉的飞机中逃生。但大多数机组人员还是设法登上了为此类紧急情况配备的充气救生筏。他们在冰冷的海面上苦苦等待来自空军基地的救援,一边与寒冷作斗争,一边忍受伤痛,坚持求生。当时正值寒冷的二月,四周都是冰渣浮动的海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来,需要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和超凡的自制力。战友们相互鼓励,彼此支持,但时间无情流逝,救援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赶到。到那时,幸存者只剩下一人——飞行员康斯坦丁·叶夫列莫夫。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几个月的康复治疗后,他已准备好重返战斗岗位,继续飞行。
坠毁的图-16机组共有六人——指挥官康斯坦丁·叶夫列莫夫,副驾驶尤里·卡济米罗夫,领航员阿法纳西·列,副领航员皮亚特科夫,无线电机枪手布洛欣,以及武器系统指挥兼通信主管伊瓦先科。最后仅指挥官叶夫列莫夫幸存,他是被一艘核潜艇救起的。尽管飞机迫降后,起初还活着四个人。这段历史至今仍谜团重重,恐怕再也无人能够揭开其中真相了。
图-16轰炸机的神秘空难
这起事故发生在1988年2月26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时分,寒意逼人。当时,堪察加海岸雷达屏幕上的一个目标突然消失了。消失的是一架喷气式军用导弹轰炸机图-16。这架轰炸机已经在鄂霍次克海上空与另一架图-16组成编队,与两架米格-31战斗机进行了一场训练空战。这只是一场演习。
演习结束后,飞机编队各自脱离,第一架图-16已开始返航降落。第二架也开始下降,距离海岸仅剩100多公里。就在这时,雷达屏幕上闪烁的绿色光点——消失了。飞机从雷达上彻底消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令人焦急不安。无线电操作员紧贴接收机,屏息凝神地监听电波。然而图-16的无线电台再也没有回应呼叫……
图-16幸存飞行员的回忆
“我当时是第二架起飞的飞机,与第一架相隔二十分钟。当第一架机组已经开始进近降落时,我在下降过程中两台发动机同时熄火了。”——失踪图-16的机长康斯坦丁·叶夫列莫夫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我们试图启动发动机。试了一次、两次……都没有成功。发动机启动不了。”——机长那沙哑的嗓音听起来仿佛不是录在磁带上,而是此时此刻就在你耳边响起——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他的讲述充满了真诚。
“到了第五次尝试之后,已经很清楚——发动机无法启动。蓄电池的电已经完全耗尽。无线电失灵了,机上的内部通话装置也无法使用。
在图-16上,机组共有六人。副驾驶和领航员与我同在前舱。领航操作员在中段舱室隔板后面,只能通过无线电与他联络。还有两人在机尾舱室:炮手和无线电操作员。如果说我们三个人清楚当前的情况,那么那三个人只能从周围突然的寂静中猜测发生了什么。我无法向他们下达弹射指令。也不可能再飞到海岸。只剩下一种选择:迫降水面!
按规定——机长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这种可能性并未被排除,但实际上从未有人真正尝试过。不过在航校时,我曾短暂驾驶过别-12水上飞机,因此对重型机在水上迫降多少还有点经验。
当我们下降到迫降高度时,离海岸大约还有30到35公里。如果我们下面没有浮冰和碎冰带,也许结局会不同。但偏偏从那一带开始就是一条延伸至海岸的碎冰带。
机腹传来了如同机枪扫射般的猛烈撞击声,很明显机身外壳被击穿、扭曲。更糟的是,应在迫降时自动打开的紧急舱门被卡住了。
滑行结束后,导弹轰炸机在水面上摇晃着。我鼓起力气,用手击碎了头顶的舱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刺痛脸庞。那天的气温是零下17摄氏度,而就在近旁,冰冷的海水翻涌着。感觉再过一会儿,海水就要涌进驾驶舱。我下令全员通过我的舱门弃机。
飞机上配有两艘LAC-5充气救生艇,它们足以让我们六个人在等待救援时坚持很长时间。而且,每位机组成员的降落伞下都配有一艘个人充气小艇。因此,我们还是怀抱着生还的希望。”
航空救生艇 LAC-5 五人座
“我爬出驾驶舱,为战友们腾出通道,本想沿着机身先去领航操作员所在的舱段。但由于迫降时激起的水花,机身上结了一层冰壳。我刚迈出一步便滑倒,掉进了海水里。大家都知道,我们飞行时并不穿防护服,所以我立刻就浑身湿透。但连感到慌乱的时间都没有。我游到机翼边,爬上去,把降落伞、救生艇、应急物资包拖上来。就在这时,我看到领航操作员的紧急出口舱门打开了。他满脸是血,看样子在迫降时受了重创:双腿膝盖以下受伤,头部也被撞破。我赶紧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去帮助他。我打开了他的救生艇的充气阀门,帮他爬进救生艇,并把他推离飞机。
副驾驶已经在水面上,坐进了自己的救生艇,而领航员还留在飞机里。他正试图释放主救生艇LAC-5,那艘大救生艇放在驾驶舱后方右舷机身内的专门舱口中。
按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只要在驾驶舱内扳动阀门,救生艇就会自动落水并充好气,配备好救生物资。但那个舱口被卡住了,艇出不来。
我们迫降水面大约五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来得及了解尾舱里的炮手和无线电员的情况,副驾驶发出信号:“机长,飞机开始下沉,我们快走吧!”我对领航员喊,他回应:“机长,阀门打不开,救生艇出不来!”我下令他跳水。因为如果他先去解开救生艇和降落伞的连接,那肯定会立即沉下去。
领航员服从了命令,开始在水中游动。我建议他游向副驾驶的救生艇,把胸口趴在副驾驶的腿上。这时飞机明显下沉了,机翼已没入水中,我的救生艇被冲走了,我游过去追上它。爬上艇后,我回头望去。尾舱已几乎被水淹没,炮手和无线电员该通过的舱口已浸入水中。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尝试过逃生,也无力施救。整个飞机在水面上总共漂浮了约八分钟,不多。突然它急剧尾部下沉、机头翘起,随即沉入水中,带走了我们的两位战友。
四个人留在了空旷的海面上。两人各有一艘救生艇,两人共用一艘。如何才能活下去?大约一分钟后,副驾驶的救生艇不知为何破裂,他和领航员都掉进水里。幸好我们彼此距离不远。副驾驶游到我这里,把胸口趴在我的腿上,领航员则趴在领航操作员的腿上。此时只有领航操作员这个受伤的人还没体验过冰水的煎熬。
我们四处张望,奇迹般地在大约四百米外发现了一艘橙色的大型充气救生艇LAC-5,在水面上漂浮着,是空的。它怎么出现在那里,我们已无法得知。也许是迫降时尾舱的炮手和无线电员成功释放了它,也许是迫降震动时被甩出来的。但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上天的恩赐,让我们重燃了生还的希望。
我们开始向救生艇游去。只能用手划水。我戴着皮手套,还能划水,其他人没戴手套。碎冰阻碍前进。花了整整四十分钟,我们才到达那艘救生艇。它是底朝上翻着的。我把副驾驶托上去,他抓住侧边的绳索,靠向后一躺,用力拉住绳索,把艇翻了过来。
我们决定不去打扰领航操作员,他留在自己的小艇里,我们三人爬进了LAC-5。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脚,手也不听使唤,寒冷在一点点吞噬我们。但我们还得准备好救生物资,以迎接可能到来的救援。
皮手套虽在划水时派上了用场,但现在已经泡烂,我把它脱了。其他人的手被碎冰划得伤痕累累。我口袋里有一副羊毛手套,我拧干后给了领航员,他戴上了。我们分工合作,各自负责准备迎救的物品,希望很快会有直升机来救我们。
我们准备好了信号弹、桨,取出了无线电。但要将无线电和电源块连接起来却异常困难。电源块的防水盖被冻得硬邦邦的,只能用刀割开,但双手已不听使唤,电源块和无线电根本接不上。不过,我还是设法在电台中发出了求救信号。发完后,我把电台塞进怀里。为什么不是放口袋?因为我已无法解开口袋的拉链。
就在这时,我们发现救生艇的后舱开始下沉。可能是被冰块撞击后,艇体的橡胶出现了微裂缝。但我们没法找到裂缝,更别提修补了。当我们这些浑身湿透的人爬上艇时,也带进了很多水。水在艇底来回荡漾,我们能做的只是把阀门关上,好保住艇首气囊里的空气。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关上右边的阀门,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而橡胶在严寒中已变得又硬又脆。左边的阀门我已无力再去关了。这时我们头顶出现了一架安-12飞机。”
Ан-12
“我拿起无线电,但自己已经无法操作了:双手不听使唤。领航员把无线电和电源块夹在胸前,我用两只大拇指按着发射按钮开始呼叫。先是用语音报出呼号,发出求救信号,然后一直按着按钮,让无线电发出持续信号。
那架飞机转向朝我们这边飞来。我们明白了,那边已经收到了我们的信号,正在朝我们靠近,就差能看到我们了。
我好不容易把无线电收好,塞进领航员的外套里,自己则把那艘救生艇翻过来,把橙色的艇底朝上,用它不停挥动,希望能更快被发现。可是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哪里知道,那架飞机的燃油已经快耗尽了。它是从别处返航途中,调度员临时请求他们顺路帮忙寻找一下,他们也尽力了。
后来才知道,那架安-12并没发现我们的位置,只是听到了无线电信号。而我们却以为飞机发现了我们,只是返航去调派直升机来救援。我们还为此高兴了一阵,却没注意到副驾驶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线。他不知何时到了我们身后,倒在了救生艇下沉的船舷上,身体抽搐起来。接着,他整个人僵直了,开始滑向船外。
我和领航员急忙去拉他进艇,想让他坐下,但他的身体怎么都弯不下来。我跳到小救生艇上,试图从水里协助领航员一起拉,但他的身体还是从LAC-5的船舷滑了下来,正好落在我脚边。
我拼命想把他救醒,摇晃他,拍打他的脸,喊他醒来。他似乎有点反应,想说什么,但话已含糊不清。接着,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的喘息……他就在我们眼前去世了。
我们把他的遗体移到大救生艇上,我用绳索把他绑在艇边,以免被浪冲走。
抬起头,我几乎要惊叫出声。在我们约三百米外,赫然看到一艘潜艇静静浮在海面上。我们完全没听见它上浮的声音,艇上也看不到人影,它就像一头正在打盹的鲸鱼。我心里猛地一紧,生怕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沉回海里,连我们都没发现。”
核潜艇K-430。
事发地点的气温是零下17.4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落水是无法生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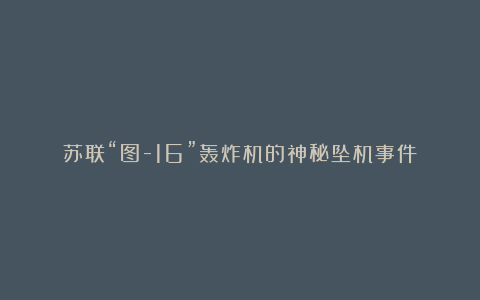
“我拿起船桨,想划过去敲敲它的装甲,请求救援。但领航员提醒我:’别去,指挥员!’因为要到潜艇那里,需要穿过大约150米的浮冰和碎冰带。这太危险了。领航员是对的:万一在半路上失去了救生艇,我们就永远回不来了。只能放弃这个念头,那艘潜艇依旧静静地停在那里,仿佛在打盹,一动不动。
领航员-操作员的视力显然出了问题。他虽然四下张望,却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停地问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周围怎么样。我们安慰他说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了,很快就会有救援到来。他虽然冻得骨头都僵了,但依旧很坚强地挺着。
终于,直升机出现了。我们高兴极了,觉得苦难要结束了!可……又落空了。直升机沿着海冰边缘和稍远处搜寻,有几次它们就在离我们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盘旋。但我们就是没法让他们发现我们。
我很清楚飞机走的时候我把无线电和电源块一起放进了领航员的怀里。无线电还在,但电源块不见了。很可能是我们搬运副驾驶时掉到海里去了。我们在艇底找过,试着把水排出去,但怎么都找不到。
于是我们开始燃放信号弹。绝望中把所有的信号弹都烧完了,也没有用。直升机没发现我们。这里天黑得早,六点半天就黑了,直升机撤走了,潜艇也不见了。我们明白,今晚别指望会有救援了,夜里大概不会再来搜救了。
领航员是个经验丰富的人,见过许多风浪。他说:’康斯坦丁,看来要告别了,恐怕熬不到天亮了。’
我们已经在水上漂了三个半小时,受够了折磨。我当然知道要再撑十个小时会更难,但我作为指挥员,在心里提醒自己:’坚持住,指挥员!’我对他说,还特意让另一位也听见,说:’别胡说,兄弟们,我们能坚持住,一定能等到救援。岸就在附近,我们有优秀的飞行员,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因为我明白,绝不能失去对获救的信心。
但是,我似乎没能把这份信心传递给战友。傍晚,受伤的领航员-操作员冻死了,尽管他没落水,但还是像副驾驶一样,先是身体抽搐,挣扎着想说话,然后就安静地走了。
我本想把他的遗体转移到大艇上,让领航员换到那只空出来的小艇,可领航员摇摇头,无力地拒绝了,仍趴在大艇半塌下去的船舷上。我的小艇绑在旁边,我尽量和他说话,不让他睡着。他有气无力地回答了几句,最后也沉默了。他比领航员-操作员多活了四十分钟。
我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想找找有没有剩下的信号弹,以便救援来的时候能示意,我把手伸到大艇的舷外,在艇底摸索,碰到什么东西,拉起来一看,是块帆布。我把它拉过来,盖在身上,就像搭了个帐篷。这也许救了我的命,帆布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空间。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撑到天亮。不能睡着。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感到暖和、舒服时其实是危险的假象,必须强迫自己动一动,不能让自己昏昏欲睡。感到发抖、冷得难受反而是好事,麻木和放弃才是真正的死路。
我还记得自己有份应急口粮:两罐果汁、一小罐炖肉、三块干粮和一块巧克力。当时就特别想吃。我吃了炖肉、两块干粮,喝了一罐果汁,剩下的留着后面再吃。
第二次吃东西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具体时间不记得了,虽然我的指挥员手表还走着,我一直看时间,但就是记不住。
双脚已经完全没感觉了,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做些简单活动,想象自己在活动手指、膝盖,手也麻了,就把手塞到腋下取暖。外套里多少还有点余温。
一开始我在艇里坐着,后来失去了控制,滑倒,半躺在水里。艇里进了水,寒冷渗透到肚子和后背,我从肩膀以下都没有知觉了,只有肩膀和手臂搭在艇舷上。”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开始回忆诗歌,大声朗诵出来。努力回想起那些已经忘记的诗句,还唱歌、自言自语,只为了不睡过去。或许听起来很俗气,但事情确实就是这样——我还想起了电影《恰巴耶夫》里的一个场景:他在最后的力气中游过河,高喊’你休想抓住我!’我也曾在那一刻喊出了这句话。眼前闪过了我的过去,整个人生都在眼前掠过。我不想死。
天开始亮了。突然,我听见了人的声音。我以为自己开始产生幻觉了。但那些声音并没有消失,有人在不远处低声交谈。我把盖在头上的帆布掀开,发现那橙色的救生艇已经结成了白色的冰壳,船舷上都结了厚厚的冰。那位躺在小艇上的领航员-操作员已经成了一块冰疙瘩,而大艇上的领航员不见了,他滑进了水中,只剩下一只手还露在水面,被他临终前绑在艇舷上的绳索系着,身体没有被水冲走。
那声音又响起了,没有消失。我回头一看,不敢相信——潜艇!就在不远处!但这次甲板上有了人。水兵们发现了我,明白我还活着,立刻开始行动起来。可我已经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放下了一只小艇,冲破冰水向我划过来。我也从身体深处又找出一点力气,试着配合他们。潜艇官兵们把我转移到潜艇上费了好大劲,但这已经是最后的困难了。之后就是医生们接手。他们给我脱掉衣服、擦洗身体,用酒精搓揉取暖。
我的身体已经冻得僵硬,没有体温,用普通体温计根本测不出来。呼吸像奔跑中的狗一样急促。他们不敢用强烈的药物,怕心脏停跳。三个半小时后,我开始恢复体温。在第二次酒精擦拭、热水袋包裹、被子捂盖后,身体温度升到38度,他们才开始降温处理。
直升机很快飞来了,但决定先用潜艇把我送近岸边,再由快艇送往医院。凌晨五点,我已经在病房里了。这时我的状态稍好一些,简单地向指挥部汇报了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这时候回忆的过程非常痛苦,医生不得不终止谈话,担心我的肾脏会衰竭,毕竟我在冰冷的水里呆了十七个多小时。最终决定将我送往海参崴,那儿有必要的医疗设备。一到那儿就进了重症监护室。起初医生们怎么也无法让我入睡,过度兴奋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但一旦睡着,我竟然整整昏睡了两天两夜,怎么都叫不醒。
医生们对我帮助极大,我非常感谢他们。我没有得肺炎,甚至连感冒都没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高压氧舱、一些非传统疗法、血液净化设备,都帮了大忙。当然,还有我妻子的照顾,她是医生,当时立刻从堪察加飞了过来。
我的手脚表皮都脱落了,但医生们还是避免了截肢。他们相信我的身体能够恢复。果然,一个半月后我开始重新站立。
感觉手和脚好像不是自己的,需要重新学会走路、拿勺子、写字。再过两个半月,我出院了,被送去疗养,治疗就此结束。”
在事故调查中,当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导致大多数机组成员没能活下来?毕竟当时是有救生设备的。对此我只能这样说:机组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我们在水上也进行过使用救生设备的训练。但训练时是在正常、适宜生存的温度条件下进行的,绝不是在我们所遇到的那种极端环境下。而这次又出现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因素。结果就是,从飞机里逃出来的四个人,最终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我们远东地区,没有自己的飞行员极端环境生存训练中心,而这样的训练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放弃,不失去希望,强迫自己去与严寒搏斗,也许其他人也能获救……”
图-16
图-16是苏联制造的一款重型双发喷气式多用途飞机。该机生产了多个型号,包括轰炸机、导弹发射型、加油机、电子战飞机等多种改型。它是在美国波音B-29的基础上研制的,从本质上说是美国飞机的改进仿制型。图-16于1955年列装苏联空军。
动力装置:两台推力各9500千克的涡喷发动机。
最大速度(6000米高度):992公里/小时;升限:15000米。
航程:5000公里。
空机重量:3773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72000千克。
翼展:32.99米;机长:34.8米;机高:10.36米;翼面积:165平方米。
总生产数量:1511架。
事故数量:126架。
遇难飞行人员人数:608人。
获救情况
飞行员叶弗雷莫夫船长在事故发生后一天,被核潜艇K-430救起。潜艇指挥官因成功救援溺水者而获得奖章。事故现场气温为零下17.4度,在如此严寒的水温中生存几乎不可能,但叶弗雷莫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获救时,他独自一人在一艘五座救生艇中。另一艘同样是五座的救生艇则漂浮在附近,里面有两名已经冻僵的导航员。
右侧飞行员的下落至今不明。位于飞机尾部的无线电员和火力指挥官的命运也未被查明。但机舱内的三名成员和中舱的一名成员从迫降的飞机中成功逃出,不幸的是,他们都未能生还。
幸存飞行员叶弗雷莫夫的结局也不幸。1993年,康斯坦丁在远东地区发生车祸去世。家人将他的遗体运回故乡塔尔缅卡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