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不能进酒馆?你要说这事搁现在,估计很多人听了得嗤之以鼻:怎么,公职人员吃个饭还得躲着点,难不成是怕喝醉了失态,还是怕被人看见和谁勾兑?但放在当年的京城开封,酒肆门口的匾还真像一道分割线,里头热闹喧哗,外头不少身穿官服的人站着犹豫,排场和规矩——都紧紧咬在一起了。
其实,说起宋朝,咱老百姓熟的,多半是苏轼李清照这类文人骚客,诗词里端着杯酒,姿态都带点闲云野鹤的劲儿。但官场那点门道,藏得远远比诗句要深得多。别的不说,《归田录》里鲁宗道那件事,窄得能挤下几百年官员的心虚。
往前追,宋的酒文化,比唐朝还旺盛。李白醉里写诗,酒意上来“天子呼来不上船”,那是风流。而宋太祖赵匡胤,喝起酒来,却透着股城府。陈桥兵变后的那场酒宴,说穿了,是场“心术”局:赵匡胤请功臣们喝酒,温声细语里藏着刀刃——你们的军权,今夜该交出来了。
但且慢,这事要是流入市井,少不得人说这皇帝腻味功臣、心忌太重。可话得反着说,赵匡胤一手建下大宋,城头变幻大旗的滋味还烫在心口。他怕的,不是官员喝醉闹事,是权力交错之下,谁会忽然举杯,翻脸称王。宋朝的律法,官员不得入酒肆,某种意义上,是之后千秋万代里官场对风险的谨慎避讳。
酒席,是个什么地儿?唐时文人豪客,宋时官员乡绅,大家都得在杯底攀比。门面必须做足,有事没事拉一桌,喝到天昏地暗,谁还记得“勤俭”?尤其是公式化的官场,公款吃喝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顽疾。宋朝越到后面,酒肆里没了诗酒风流,有的只是油腻腻的权钱交易,跟人情关系一锅端。
偏偏宋人对饮酒格外热衷。那会儿酿得多是低度酒,粮食不缺,喝起来就像喝水。开封城内,每条街几乎都有酒馆,晚上灯火通明,谁还分得清官百姓?但偏偏官员就得缺席,哪怕进门了,眼神还得飘着,生怕被人认出来。
这规矩不是玩笑。要是哪个官员不长心,进了酒肆,被人抓了现行,顶多是罚俸撤职,重了说不定家都回不去。这不是小心眼,而是连锁效应:酒肆里乱攀关系,吃喝中谈出来的事,要么贪污,要么拉帮结派。宋廷有御史专管官员行踪,专盯这些“脏地儿”,不然大宋的“清白”哪守得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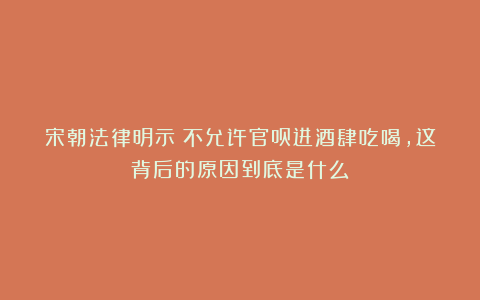
话说回来,官员真就不敢进酒肆吗?还是得看人、看情况。鲁宗道的那次,老家有人来,家里酒具临时不齐,他实在拉不下脸,穿了便装连夜带客户钻进仁和楼,心里七上八下,生怕碰上熟人。掩着身份当寻常人混进去,杯子举起来手却发抖,只为一顿“人情”不得已。
但世事偏不顺。偏巧那天真宗找他,朝服换了又换,迟到许久。皇帝脸色直黑,质问一句:“你为何私入酒家?”这不是问罪,是逼他自辩——真宗还算给台阶,但鲁宗道如果不认错,落入御史之口,仕途就黄了。他诚恳认罪,事情才算压下。宋朝官场,讲的是规矩,也是智商;情面之下,是夹杂着钢丝的戒律。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得取食于四方”那一条。吕夷简家吃的不稀罕?皇后想让仁宗补身,却犯了祖宗家法。宰相夫人回话,句句是在权力边界上打太极。家乡的名产,送到宫里也得查查规矩——不是没情分,权力和礼法就像一堵墙,谁敢逾越?
官员不能在地方索取“食味”,说白了就是不能仗势欺人。宋朝百姓日子安稳,皇帝怕的,还是上下串通,把公务变成人情债。百姓跑断腿,官员卷着袖子装没事人,到头来怨声载道,只会让“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漂上贪腐的味道。
其实一两条法令,未必能根除人性的私心。但你要说宋朝这套律法,能不能为后世做点示范?我觉得未必寻了个“万全”。官员再忌惮,还是有办法钻空子;规矩再严,百姓也未必都信。可“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终归让大宋少了不少动荡。在天下太平与人心躁动之间,皇帝和臣子一直是捏着酒杯、提着戒心活着。
有时候我琢磨,律令之上,是不是还有人的欲望、情感,或者那点小聪明?寒窗十年换来的功名,喝杯酒都要低头躲闪,这样的人生算不算可怜?到头来,律法在,欲望也在。谁都想安安稳稳,但谁又不是在规矩的缝隙间学着做局?
宋朝的法令转了几百年,勤俭节约成了老祖宗给的标签。有人真能做到底吗?还是只在纸面讲讲?现代社会约束更紧,明面上说为公,背后却照样有各种觥筹交错。换了穿着,换了牌匾,人心却没换。或许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靠几条法令截断了人情与欲望。只不过,要是谁能守得住本心,在权力和诱惑之间,说“我不进酒肆”,那才是做官的真本事。
很多年后,大宋的酒肆门口依然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是官员的身影少了些。人们喝完酒,嘴里吐着风凉话,有时还会瞧几眼不远处的那座衙门。谁也没说清,这一纸禁令是保了天下,还是留下了更深的隔阂。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不把话讲死,总得让人琢磨琢磨——如果鲁宗道那天没穿便装,会怎样?如果赵匡胤不摆酒宴,江山会不会坐得更稳?酒杯一举,权力与人性都浮上水面,这些故事,谁又能说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