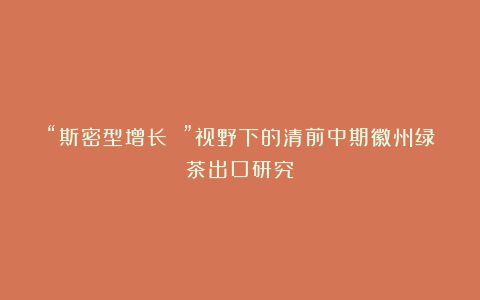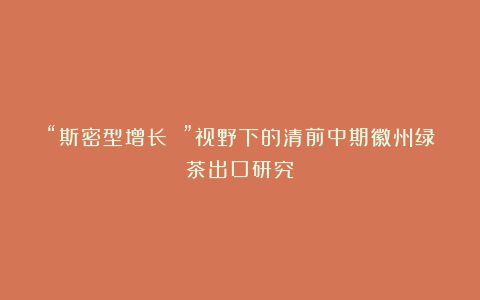|
摘 要:16世纪以降,中国茶业进入由市场力量主导、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主要动力的“斯密型增长”时期 。徽州地区凭借悠久的产茶历史、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以及徽商的经营能力,成为最重要的绿茶产区之一。18世纪,随着中西直接贸易兴起,徽州又成为主要的外销绿茶产区,徽州茶业的“斯密型增长”进入内销和外销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综合多种外文资料记载的贸易数据进行核算,鸦片战争前近 120 年间,以徽州绿茶为主的广州口岸绿茶出口量增长近45倍,主要是在 19 世纪的前三十几年剧增近 15 万担 。1836—1839 年间绿茶在广州茶叶出口量中占比约39%,绿茶出口值超过红茶。在融入全球贸易网络的过程中,“小农经济+商人资本”的产业模式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徽州茶业内部形成内销和外销的分工,完成了局部的产业升级: 其一,专供外销的“ 园茶 ”种植推广,加速了茶农经营专业化和集约化;其二,外销绿茶的精制环节复杂化,促使商业资本深度介入加工过程;其三,出现多个外销绿茶新品种,形成了更为细化成熟的茶叶分类分级体系。
关键词: 清前中期; 徽州; 绿茶; 出口; 斯密型增长
1.张宁,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硕士、博士期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2002年博士毕业后到湖北大学任教至今。在科研方面,专注于经济史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银两货币史研究”,并担任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此外,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已结题。出版专著两部,在《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学遗产》《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得1项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刘洋,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420062) 。
16世纪,中国茶业进入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发展阶段,此后逐渐形成多个重要的内销和边销茶产区。其中,徽州是内销绿茶主产区之一。1757 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后,茶叶外销迅猛增长,徽州又成为外销绿茶主产区。
明清时期,随着交通和市场网络的不断扩大,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特征的“斯密型增长”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以长途贸易为基础的专业化大宗商品产区相继兴起,徽州茶区与长江、京杭大运河和沿海航道等三大水运干线直接或间接相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因此研究清前中期徽州绿茶出口,对于理解当时中国经济的“斯密型增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研究茶叶出口需要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资料,欧美进口国政府、企业和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留下了丰富的贸易数据和调查报告,是研究徽州茶业较为系统可靠的史料。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强调茶叶出口对世界的影响,未能充分利用这些外文史料, 故而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定量分析少,未能充分整理出口数据; 二是对于茶叶出口如何提升徽州茶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进而推动工艺和品种的创新,尚无专门探讨。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在“斯密型增长 ”的视野下分析徽州成为外销绿茶出口主产区的背景,进而使用各种外文史料尝试解决上述两点不足,并探讨“小农经济+商人资本 ”产业模式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适应性和创新力。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直接贸易兴起,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出口商路。18世纪20年代,茶叶成为广州贸易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徽州得益于水运交通优势以及明代以来茶产业“斯密型增长”过程中形成的产业优势,成为外销绿茶主产区。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荷印公司”) 商船首次将茶叶(日本绿茶) 运回欧洲。因日本从17世纪30年代实行锁国政策,此后欧洲商人只能买中国茶。中国茶叶最早的出口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中国商人从厦门运茶叶到东南亚出售。据1643—1649年间在巴达维亚等地游历的法国旅行家让-巴普蒂斯特·塔维尼尔(Jean-BaptisteTavernier) 记载,殖民地的欧洲人大量喝茶,“一天都会喝四五次”,包括把水变绿的茶、把水变黄的茶、把水变红的茶(即绿茶、乌龙茶和红茶)。可见各类茶叶都在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大量销售。荷印公司在荷兰的殖民地买茶,运往欧洲。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英印公司”) 也加入这条商路,从万丹购进茶叶143 磅,首次将茶叶进口到英国。此后年年购茶,“通常是公司的商馆从在万丹贸易的中国帆船( Chinese junks) 购买的”。另一条是葡萄牙人在澳门买茶,运往南亚的殖民地。英印公司在印度苏拉特购茶,“是从那些往来澳门与果阿及达曼(Daman)的葡萄牙商船购买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解除海禁政策,同时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地点、规模和人员。中西直航贸易开启,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到厦门、广州和舟山等港口寻找贸易机会。市场的天平逐渐倾向广州,“与中国沿海其他港口不同,广州是重要的内河港口,便于顺利获得内陆补给品、船只必备用品和包装所需物料的供应”。1689年,英印公司商船“公主号”在厦门购茶。1699—1700年,英印公司第一次派商船去广州,“麦士里菲尔德号”购上等松萝茶(Singlo)160担。1704年,英印公司指令“斯特雷特姆号”开往广州,认为广州比“厦门好得多,这个口岸的待遇较好,办事较快和价格最便宜”。至于“舟山口岸的定海,只不过是一个小市场,只有本地买卖”。1715年后,英印公司不再派商船去厦门。直到1734年,该公司再度派船去厦门,但贸易不成功,“当地商人资金少,要五六个月才能完成他们的定货,而广州通常是三四个月。而他们的价钱比广州最近的高 10%到20%”。同一时期,荷印公司也改变“从广州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获得中国货物”的方式,于1729年第一次直接派船到广州。康雍年间,继法国、英国、荷兰三国在广州设立贸易站后,丹麦、瑞典等国东印度公司也到广州开展贸易。由上可见,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外贸中心,并非乾隆二十二年( 1757) “一口通商”政策所致,而是中外商人选择的结果。
茶叶货源是广州胜出的重要原因。1701年贸易季度,开往广州的英印公司商船“诺森伯兰号”收到训令,“各种品质的茶叶在人们中间已获得声誉”。到 1717 年,“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但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所以要订长期的特别合约”。这些地区出产的茶叶,通过两条重要商路运至广州。
一是赣江—大庾岭—珠江商路。大庾岭古道开凿于秦汉时期。唐开元年间开凿的大庾岭新道成为连接赣江和珠江水系的重要通道,极大地便利了商旅转输 。明清时期,鄱阳湖—赣江—信江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水路之一,可以连接周边数省,沟通数条重要商道。进入18 世纪,江南生丝、徽州绿茶、闽北红茶、景德镇瓷器等出口商品通过这一商路网络源源不断运往广州。
二是洞庭湖—湘江—南风岭—珠江商路。清代,随着洞庭湖流域的开发,湘潭成为商业重镇,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茶叶转运中心。康熙四十二年(1703) ,顾彩游历鄂西南武陵山区的容美土司时,发现“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这说明鄂西南山区的茶叶运往湘潭的商路已是长江中游茶叶产销网络的一部分,可见湘潭茶市辐射范围之广。广州“一口通商”后,茶叶等土产“在湘潭装箱,运广州启洋,洋货亦经此路,先集湘潭,再分运内陆”。
广州贸易的开展,为徽州茶业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到18世纪中叶,形成了以徽州绿茶和闽北红茶(含部分乌龙茶) 为主的茶叶出口格局 。乾隆四十二年(1777),行商回禀广东巡抚,称“夷人出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ngy) 在《中国与西方: 18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 》中利用欧美各国档案研究广州贸易,认为绿茶主要产于“松萝山西北端的徽州以及婺源”(按: 明清时期,婺源隶属于徽州府) 。
广州茶叶贸易开展之初,湖南也是绿茶来源地之一,何以后来被徽州超越? 这是明中叶以后茶业“斯密型增长 ”形成地区分工的结果。在政府减少管制的产业环境中,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主导产业发展,因此重要茶区向着特色化的方向发展。两湖茶区的产业特色是生产边销的紧压茶,虽有绿茶出产,但不能与盛产绿茶的徽州竞争。上文所引乾隆四十二年广州行商介绍出口茶叶产地时,不再提及湖南。
徽州成为最重要的绿茶产区,是水运交通优势、徽商资本和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前工业时代,“比较单由陆运,水运之便可以开拓更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往往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茶叶是长途贩运型商品,地区专业化生产必须依赖通畅的水运。明代,长江下游和中游的航段连接起来。清代,长江水系相互连通的水运网络基本形成,并与大运河和沿海航道相连,构成了18世纪中国水运系统的主干。徽州在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优势:向西,翻越海拔不高的榔木岭,经徽饶水道进入鄱阳湖,再从九江入长江;向北,经徽宣水道,沿青弋江水系进入长江,再经漕路由大运河北上; 向东,走徽杭水路,由新安江水路到杭州; 向南,从徽饶水道至湖口再由鄱阳湖转入赣江—大庾岭商路,或从饶河口直抵南昌后转入赣江—大庾岭商路。随着国内长途贸易的发展,徽商通过内河航运不断扩大贸易范围。
徽州茶产区具备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条件,茶业基础和徽商经营使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徽州地处山区,地少人稠,从宋代开始依赖自然地理和水路交通条件发展专业化商品生产,销往外地 。南宋《新安志》载: “祁门水入于鄱(鄱阳湖) ,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茗者,茶也。当地初步走上茶叶生产专业化的道路 。至明初,徽州已是国内重要的茶产区。四川自宋代以来以产茶闻名,洪武初年,四川“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洪武九年(1376),徽州府茶树约1040万株,是四川茶株的4倍多。到洪熙元年(1425) ,徽州府茶树增长到约1966万株,比洪武九年又增加近一倍16世纪,徽州商品经济加速发展,“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擅长经营长途贩运的徽商群体兴起,“小农经营+商人资本”的茶业发展模式走向成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16 世纪下半叶,炒青茶技术从苏州传至徽州后,松萝茶在徽州境内的休宁松萝山被创制并流行开来。十数年间,松萝茶便跻身顶级名茶之列,并在明末清初传播至福建武夷山和浙江绍兴等地。松萝茶的创制和传播,说明绿茶技术创新中心开始从江南向徽州转移。
清前中期,水运交通优势的强化、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徽商成为全国性的顶级商帮,继续强化徽州茶业的产业模式和竞争优势。当国际市场需求来临时,徽州必然脱颖而出。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师塞缪尔·鲍尔( Samuel Ball) 明确说: “外销绿茶产区在江南省南部的徽州府地区。熙春茶( hyson) 主要( 如果不是全部) 从休宁和婺源这两个区域及毗连地区运来的。”至于晚清时期另一个重要绿茶出口产区绍兴府,此时还未见茶叶出口记载,关于“平水珠茶”( Ping-Suey) 的记载,目前最早见于 1856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报告。当时浙江的外销茶主要是普通绿茶,1858 年领事报告记载“能够收到一些优质的绿茶,但是数量不大”。
从18世纪20年代到鸦片战争前,国际市场成为中国茶业发展的新动力。在“斯密型增长 ”模式下,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必然进一步推动专业化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升,直接表现为出口量增长。测算出口数据,是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徽州茶业以及中国茶业和中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虽然清政府不统计商品出口数据,但参与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保存了丰富的贸易数据。本节使用多种外文资料,对清前中期绿茶出口进行定量研究。
1785年以前的广州茶叶贸易中,英商茶叶购买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荷国、法国、瑞典、丹麦及欧陆诸小国商人合计茶叶购买量占比近三分之二。这些茶叶运往欧洲后,较多走私到英国,“由荷兰诸港及瑞典之哥德堡,不断秘密输入。并且,当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代,又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 ” 。
1784年,英国政府鉴于茶叶贸易走私与竞争的双重威胁,通过了《折抵法案》(the Commutation Act)。该法案将英国的茶叶进口关税由119%降至12.5%, 导致走私贸易剧减,于是欧陆诸国商人在广州茶市的份额急剧下降,1799年至1806年间年均占比降至10%,此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购买量。英商的市场份额在18世纪末超过75%,1807—1813年间年均占比达到88%的最高点。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此后,英国散商在广州贸易中占主导地位。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展直接对华贸易,美商在广州茶叶贸易中的份额迅速增长,1799—1806年间年均占比17%,1836—1839年间年均占比约30%。
各国商人历年购买绿茶量的数据不全。我们目前搜集到部分年份的英商购买数据,1742—1794 年荷印公司购买数据,1790—1839 年间大部分年份的美商购买数据,缺少其他欧陆公司购买绿茶的数据。鉴于此,本文采取如下推算方法: 在1740年以前,英印公司一直试图垄断广州绿茶市场, 特别是熙春茶,其他公司购买量很少,故本文以英印公司的购买量作为 1721—1740 年广州贸易绿茶总出口量。1742— 1794 年间有荷印公司数据,考虑到欧陆公司购买的茶叶大多走私到英国,各公司购买绿茶占比应该相近,故以荷印公司购买绿茶占其茶叶总购买量的比例,作为欧陆公司的平均水平,再乘以欧陆公司茶叶年均购买总量(使用路易·德尔米尼的数据),得出欧陆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1795 年后,广州出口的绿茶主要由英商和美商购买,有贸易统计可用 。本文在合计各国茶叶购买量时,单位统一折算为英制磅。
英国是中国外销茶叶最主要的消费国,英商是广州市场上实力最强的买家。 图1显示 1721— 1839 年间的部分年份英商购买绿茶数量及绿茶占购买茶叶总量的比例。
据现有史料,英国商船来广州购买绿茶始于1699 年,从1721年开始有购茶量的连续记载。1721—1760 年间,以每10年为一段,英印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分别约为487754 磅、531545 磅、937577 磅、1263791磅,增长不到2倍,40年间的年均量约为805167磅。同期,英印公司年均购茶量增长3倍多。从1784 年《折抵法案》实施到 1834 年英印公司失去贸易特权以前,该公司在广州茶市占据主导地位。英印公司 1792 年购买绿茶 2082133磅、1810年购买绿茶 6396933磅、1832 年购买绿茶 6699600磅,仅从1792 年到 1810 年就增长了2倍多。1834—1839年为英国散商主导对华贸易阶段,期间的最后4 年英商购买绿 茶量分别约为 8818665磅、7561333磅、7728800 磅、7469930 磅, 绿茶年均购买量约为7894682 磅。英印公司在早期试图囤积绿茶,购茶总量中绿茶占比接近或超过一半。由于英国茶叶消费风气变化,英印公司在18 世纪下半叶转为主要购买红茶,绿茶占比在18世纪末一度跌到 10% 以下。此后,英商购买绿茶比例增加,1810年后增至20%以上,在1839年高达26% .
自1729年荷印公司开通对华商贸直航,荷兰商人只在广州购买茶叶。荷兰驻广州商馆档案较详细地记录了 1742—1794 年购茶数据(见图2)。1794 年,荷印公司结束对华贸易。1822 年,荷兰驻广州商馆关闭。
1742—1794年间,除去1759年购买茶叶数据不详,1781年、1782年、1793年未购茶,1791年购买的茶叶中工夫茶和拣焙茶数量不详,荷印公司档案均记录了荷商在广州的购茶数据。图2显示荷商的购买绿茶量从1742年的126193荷兰磅增长至 1751年的 354883 荷兰磅,绿茶在茶叶购买总量中占比大致在13%至26%之间。1752年起,荷商购买绿茶占比急剧降低,1757年后缓慢波动回升,最高为 1786年的约16%。后受到英国《折抵法案》以及美国于1789年对来自欧洲的茶叶征税的双重打击,荷印公司购茶量大减,并于 1794 年基本结束了在广州的茶叶贸易。
1784—1785 年贸易季,美国与广州间的直航贸易开启,两艘美国商船直航到广州,购买880100磅茶叶,其中“中国皇后号 ”贩运红茶327918磅、绿茶74915磅。《美国国会文献集》(American State Papers)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记载了 1789—1839 年间大部分年份的美商购买茶叶贸易数据, 这些外文材料在国内茶业史研究中较少被关注。
图3显示1789年至1839年间,美商在广州的绿茶购买量从约 727419 磅增至约 15737332 磅,增长了21倍多。自1805 年起,美商购买绿茶量占比超过红茶并波动上升,到 1836—1839 年间占比约79%。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美国社会仍延续殖民地时期饮用红茶为主的传统。之后,美国市场的绿茶消费占比提升,“就连农民也不喝武夷茶和劣等茶,而改喝熙春皮茶了”, 这促使美商更多购买绿茶。
美商的购买绿茶量迅速增长,从1810年的2178989磅(约为英商购买量的 34%) 增至 1832 年的6508533 磅,已与英商购买量(6699600 磅)相当。1836—1839年美商的绿茶年均购买量为11964300磅,是英商购买量(7894682磅)的约1.5倍。美商成为徽州绿茶最大买家。
根据上文的思路和数据,本节估算 1721—183年间的部分年份广州绿茶出口量及占当年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数量统一折算为英制磅,估算如图4所示。
图4中的1721—1760年数据估算以10年或20年为一段 。英商和荷商购茶数据来自两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欧陆公司整体购茶数据来自路易·德尔米尼以六到八年为时间段的研究。为统一标准,该时期所有数据均按10年或20年进行了归整估算。估算结果难免存在误差,但误差很小。
1721—1740年,以英印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约 509650 磅作为广州贸易的绿茶年均出口量 。这一阶段,各国商人年均茶叶购买总量约为 21720 担( 2896000 磅)。因此,广州绿茶年均出口量约占茶叶年均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 18%。这一数字可能略有一点低估。
1741—1750年,英印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约为 937577磅。欧陆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估算如下: 使用1742—1750年荷印公司绿茶年均购买占比20% 的数据,再以1741—1748年欧陆各公司茶叶年均购买量约46844担(6245867磅)为基数,估算出1741—1750 年欧陆各公司绿茶年均购买量约为1249173 磅。两者合计,广州绿茶年均出口量约2186750 磅,再除以1741—1748 年间各国商人茶叶年均购买总量约8227600磅,得出绿茶出口量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27%。
1751—1760年,英印公司的绿茶年均购买量约为 1263791磅。欧陆公司的绿茶年均购买量估算如下:使用1751—1760年荷印公司绿茶年均购买占比7%的数据,再以1749—1762年欧陆各公司茶叶年均购买总量58114担(7748533磅)为基数,估算得出这一阶段欧陆各公司的绿茶年均购买量约为542397 磅。两者合计,广州绿茶年均出口量约1806188 磅,再除以1749—1762年间各国商人茶叶年均购买总量约10919200磅,得出绿茶出口量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17%。
1792年,英商购买绿茶2082133磅,占其总购茶量约9%; 美商购买绿茶213788磅,占其总购茶量约14% 。欧陆各公司数据估算如下: 在路易·德尔米尼的统计中,分为1785—1791年和1792—1798年两段,在这两段时间里,欧陆公司的市场份额持续下跌,年均购茶量从66578担降至33942担,降幅几近一半。1792年在两段中间,为避免使用1792—1798 年数据必然造成的过分低估,故以1785—1798 年欧陆公司年均购茶50260担(6701333 磅) 作为1792年欧陆商人的购茶量,这与实际情况应相差不多。以荷印公司该年购买绿茶占比8%作为欧陆公司的平均水平,乘以6701333磅,得出欧陆商人的购买绿茶量约为536107磅。综合英、美、欧陆商人的购茶数据,1792年广州绿茶出口量约为 2832028磅,再除以1792年茶叶出口总量约 31159462磅, 得出广州绿茶出口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9% 。
1810年和1832年,英商和美商垄断了广州茶叶贸易,两国商人的购茶量基本是广州的茶叶出口量 。1810年两国商人共购买绿茶8575922磅,购茶总量 30651275磅,绿茶出口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28%。1832年两国商人共购买绿茶 13208133 磅,除以购茶总量约43896267磅,得出绿茶出口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30% 。
1836年至1839年,根据《中国丛报》所载广州外国商会统计的出口商品数据,英商和美商垄断了茶叶出口,两国商人购买的绿茶总量分别为 22483731 磅、17845467磅、15899467磅、23207262磅 。这4年的绿茶年均出口量约为19858982磅,除以这4年茶叶年均出口总量约50368412磅,得出绿茶年均出口占茶叶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39% 。
综上,以徽州绿茶为主的广州绿茶出口量在近 120 年间增长了近45倍。1839年的绿茶出口量比1792 年增长超过2000万磅(超过15万担) ,从图1至图4可见,增长主要发生在19世纪前的三十几年。1836—1839 年,绿茶年均出口量占茶叶年均出口总量的比例约39%。由于绿茶采购价格普遍高于红茶,如以高一倍换算,鸦片战争前广州绿茶出口总值超过红茶。
此外,还有少量徽州绿茶(主要是珠兰茶)从北方的恰克图出口到俄国。1800年,恰克图出口俄国绿茶8387普特,折合301932 磅。此后,由于英商将广州购买的绿茶运往孟买后转运至俄国中亚地区,恰克图的绿茶贸易极少。1846年,绿茶在恰克图茶叶贸易值中仅占0.4%。
明代到清前中期,商品经济大发展,人口增长数亿,但没有重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入增加造成的外延式增长,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造成的内涵式增长孰轻孰重?茶叶生长于山地丘陵,消费主要在城市,是典型的长途贸易型商品。茶叶产销集种植业、手工业和商业于一体,是研究前工业时代“斯密型增长”的重要课题,但中文史料零星分散,记载多语焉不详。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威廉·米尔本 William Milburn) 于1813年对中国出口茶叶品种作了专门记载; 该公司茶师塞缪尔·鲍尔于1804 年至1826年常驻广州与澳门期间,也通过走访茶商、茶农及茶工,形成了翔实的调查报告。1839年,《中国丛报》第8卷刊载的《茶叶种植记载》(Description of the Tea Plant) 一文,进一步融汇当时中外茶叶著述,对中国茶叶的种植、生产与加工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记录均为珍贵史料,但学界关注、利用不够。本节主要使用这些史料,从三个方面探讨绿茶出口如何推进徽州茶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并促成其局部的产业升级。
其一,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与对高档绿茶的偏好,推动了茶农经营的专业化与集约化进程 。徽州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破碎的山体地貌下平地十分有限,平地更多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茶树分布于各山的山麓和山坡上。只有市场需求大增且茶价提高时,农户才会愿意将优质的平地、更多劳动力及肥料等投入茶叶种植,以获得更多现金收益。与英印公司长期做生意的年长绿茶商人高茂(Cow Mow) 以及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茶商靝馨( Tien Hing) 向塞缪尔 · 鲍尔讲述了这一变化: “熙春茶以前被称为园茶,最早种植于休宁和婺源。”“婺源和休宁的绿茶种植方式与其他地方不同。这种茶分为两种,山茶和园茶。山茶的叶子是黄色的,小而薄,味道淡,用来制作中等和普通的熙春茶。园茶种植在菜园里,也种植在田地的边界和田埂上。园地必须用桶、瓢施肥,肥料来源于以此为目的建造的粪坑。施肥后茶叶变得厚、平、大,且颜色变成绿色。这种茶的茶汤清澈,且芳香四溢 。泡过的叶底是绿色的,大大优于山茶。园茶最早在本朝( 清朝) 被带到广州,然后送往国外。然后,种植面积逐渐增加,直到每个村庄都开始种植 (即从山上移栽) 和施肥。茶叶变成了淡绿色,叶厚有光泽,气味宜人,茶汤的味道香甜可口。”“欧洲商贾热衷于探寻带有’熙春 ’字号戳记之茶叶———此乃精培园茶,遂促使众茶商广以此名统称此类茶叶,并推广改良种植之法。”英国人将“熙春”译为“Hyson”。 中国传统茶业的一大特点是茶树零散种植,以便充分利用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主要供出口的“园茶”在婺源、休宁等地推广,其栽种地从山坡转到菜园、土地边缘和田埂,更易于管理和施肥,种植更集中,集约化水平更高。在茶农经营规模扩大和专业化的道路上,这是重要的一大步。栽培与采摘方式的进步,使茶叶品质得以显著改善。
其二,在茶叶生产过程的分工中,外销绿茶精制环节更为复杂,促使商业资本深度介入茶叶加工,建立专门从事精制加工的大型茶号。直到民国时期,徽州内销绿茶精制工艺简单,茶庄向茶农收购毛茶后,略加筛分、簸扬、分拣、复烘,即可包装发货 。外销绿茶则精制手续繁复,这是“一口通商 ”时期形成的特色。塞缪尔·鲍尔现场观察了徽州来的茶工用熙春工艺加工“Honan”( 广州产茶区域“河南”) 茶叶的全过程,还在广州记录了一箱徽州毛茶的精制过程,并采访多位徽州茶商 。将他的记述与清末至民国时期《做茶节略》④等史料关于外销绿茶精制过程的记载进行比较,我们看到外销绿茶的复杂精制工艺在 19 世纪早期已基本成熟: 一是工序成熟 。塞缪尔·鲍尔在精制茶厂亲见“八九个人同时在工作,有的筛茶,有的炒茶,有的用托盘( 按: 即蔑盘) 扬簸扬出皮茶,有的用机器筛茶( 按: 指操作风车风选),有的挑出皮叶”。他结合现场考察和调研,详细记述了精制工艺程序,与清末民国时烚、筛、撼、扇、补火、匀堆、补老火、装箱的工序大体一致。二是形成细致的筛分和风选工艺。19 世纪早期,“熙春地区通常使用七道筛子”。到清末民初,最常用的筛子多至 10 种,最多的记载达20种。除了筛子,塞缪尔·鲍尔还描述了用来风选茶叶的风车形制,前面有大口,另有“三个侧面的出料槽口”。这与民国时的图片基本一致,3个侧嘴即正口、子口和副子口。在精制加工过程中,用孔眼从小到大的多个筛子对毛茶进行筛选,筛出不同大小的茶叶,用篾盘簸扬和手工拣选挑出难看的、多节的、发黄的、破碎的叶子 。此外,用风车筛最小的茶叶,分离出茶末和不同大小的茶叶。筛选出的每一种茶叶内部还要根据大小、完整度和色泽再分级。最晚到 19 世纪初,每种茶叶分成“普通至普通上 ”到“中上 ”共 11 个级别,每一级的价格不同。外销绿茶精制环节分工细化,形成专业化、高难度、大规模的加工程序,这要求商业资本(茶商) 必须投资建立茶号,专事精制加工。 由于外销茶精制工艺远较内销茶繁复,茶号“组织也因之较为复杂”,规模大,雇员多。
其三,由于外销绿茶精制环节的专业化水平高,劳动分工细化,徽州茶业衍生出一批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绿茶新品种。广州贸易最早交易的是明代以来在徽州流行的松萝茶( 购买记载始于 1699 年) , “叶短而厚”, “大而扁平,且没有特别卷曲”。松萝茶是中国早期外销绿茶中的基本品种。此后,在广州茶市出现了6种供出口的绿茶新品种: 首先是大珠(Imperial),关于该茶的最早记载是在 1704 年,出现时间仅次于松萝茶,“是一种精制茶叶,采用轻度加工工艺,其叶片经手工揉捻成细小圆珠状,由此得中文名’珠茶 ’(珍珠茶) 或’大珠 ’(大珍珠) ”。其次是熙春茶(Hyson) , 是广州茶市的高档茶。1734 年,东印度公司下令垄断熙春茶,说明此前它已是热门货。其外观特点是“大而紧结卷曲的茶叶,外形匀整和色泽统一的,归类为熙春茶”。再次是屯溪茶( Twankay) ,在18世纪中叶进入广州茶市,是一种上等的松萝茶。相较于普通松萝茶,制作屯溪茶时筛拣更频繁,其上品有时可作为次等熙春茶售卖。进入19 世纪,屯溪茶基本上取代了松萝茶,不再有松萝茶出口的记载。此外,由于熙春茶精制时有复杂的筛选分级工艺,18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又分化出3个品种: 一是熙春皮茶,或称皮茶( Hyson Skin) ,“其名取自’表里 ’之喻———犹如熙春茶之外皮,虽为包裹,然品质次之。此茶乃是从熙春茶中拣选而出,皆取叶形粗大、形貌粗拙、色泽晦暗、未及卷曲之叶”。由熙春茶中分离出的大的、圆的、多节的,色泽几乎相同的茶叶会被归类为上等熙春皮茶。二是雨熙春( Young Hyson) 茶,或称雨前茶,主要销往美国市场,“是一种采摘于谷雨之前,非常小的叶子”, “外形条索紧结、短钝似雨点状”, “很薄很小,质地细密” 。三是芝珠茶,或称虾目、麻珠(Gunpowder) 茶,用最嫩的叶子制成,“圆形的,类似于球状”,其颗粒较“珠茶”更小,色泽墨绿,表面显莹润光泽,因形色酷似火药颗粒而得此名。19 世纪上半叶,广州茶市交易的绿茶包括大珠茶、屯溪茶、熙春茶及熙春皮茶( 或称皮茶) 、雨熙春( 或称雨前) 茶和芝珠( 或称麻珠) 茶。
16世纪中后期,以松萝茶的创制和畅销为标志,徽州绿茶业开启了内需推动下“斯密型成长 ”的第一阶段 。进入 18 世纪,在出口推动下,徽州绿茶产业发展到“斯密型增长 ”第二阶段 。其特征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轮驱动,产业内部形成内销和外销的分工。徽州外销绿茶从茶树栽培到茶叶加工都形成专业化的特色。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大、价格优且对高档绿茶需求强劲,外销绿茶的茶树栽培集约化、茶叶加工复杂化、茶叶分级体系细化成熟,生产率提高,附加值提升,徽州茶业完成了一次局部产业升级。
18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直接贸易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估算,1840年的茶叶外销量占茶叶总销量的比例超过 23%,外销茶叶商品值占茶叶总商品值的比例超过 35%。这是18世纪20年代以来出口持续增长的结果,出口是这一时期中国茶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茶叶出口扩张的背景下,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同需求,生产绿茶的徽州茶区与生产红茶( 包括部分乌龙茶) 的福建武夷山茶区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出口品种分工。两大茶区产业优势的形成,都是传统社会晚期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特征的“斯密型增长 ”的结果。明中叶以降,交通运输的进步,长途贸易的增长,推动国内市场网络不断扩大,形成了众多区域专业化的大宗商品产区。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成为国内主要的绿茶产区之一。“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主要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越大、越完善,为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就越多。”当国际市场需求的历史性机遇到来之际,徽州茶业因其产业基础、徽商经营和水运交通优势,加入全球贸易网络,进入内需和外需双轮驱动的“斯密型增长 ”第二阶段。由于外销的推动,徽州茶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达到新的水平,表现为集约种植型外销“园茶”的推广,外销茶和内销茶生产的分工,外销茶精制工艺的复杂化,茶叶分级体系细化成熟,由此带来了产出持续增长( 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 以及高档出口茶占比增加 。以徽茶为主的广州绿茶出口量在近 120 年间增长了近45倍,主要是在 19 世纪的前三十几年间增长了近15万担。鸦片战争前,绿茶出口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量的39%,出口值占比超过一半。
明清时期,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斯密型增长 ”在供给端表现为“小农经营和传统手工业+商人资本”模式。方行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既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又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这种双重结合是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这种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长期发育,到清代前期臻于成熟。”在有些地理位置好、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市场条件便利的地区,农民生产“出现不同程度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自给性生产为辅的情况”。徽州茶业的发展,说明小农经济并非天然保守落后,在“斯密型增长 ”的推动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率。茶农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精细化的投入,实现了对边缘土地的集约利用与茶叶品质的系统升级。在精制环节,商人资本采用“劳动集约型的资本积累策略 ”提高生产率。刘仁威根据清末民初的资料,发现徽州茶商用“非机械化的计时仪器———匀速燃烧的线香 ”作为生产管理工具,以求“在最少时间内生产出大批量茶叶”。据英印公司茶师塞缪尔·鲍尔的记载,在 19 世纪早期,茶商已普遍用线香管理生产。他亲测一炷香的燃烧时间,是45分钟。作为“小农经济+商人资本 ”产业模式的典型,徽州茶业的创新力持续到晚清时期,徽州茶商群聚上海,开拓市场。徽州本地“迎合国内外市场需要,结合徽州本土茶叶的资源优势,注重制茶技术的革新,创制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新的茶叶品牌,极大满足国内外茶叶市场需求”。19世纪晚期,印度、锡兰、日本茶业兴起,中国茶业的“斯密型增长 ”模式才相对落伍。与此同时,晚清时期中国经济更深更广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越来越多来自乡村的土产进入国际市场。直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密型增长 ”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说明: 文中使用的部分外文材料因目前未见中译本,由本文作者自行翻译,并经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皋峰校对,特致谢!
文献来源:张宁,刘洋.“斯密型增长”视野下的清前中期徽州绿茶出口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49(06):1-12.
温馨提示: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后台小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