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当代敦煌”蓝字关注我们哦,更多精彩!
敦煌藉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融合了东西方歌舞艺术,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敦煌民间乐曲。1900年藏经洞敦煌遗书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抄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的工尺谱抄本三谱(P.3808)完整记录了唐五代敦煌乐谱,但因谱字难识,素称“天书”。甘肃著名敦煌学学者席臻贯先生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终于破译了这部难懂的“天书”,著名的“唐乐”原原本本的复活了。
敦煌壁画总共出现乐器54种,除古琴、筝、箫、笙、笛等之外,还有4种琵琶、3种箜篌、3种风首琴、17种鼓。据该书不完全统计,这些乐器在壁画中共使用4095件次,绘有741把琵琶、293把笙、347支荜篥、410支横笛。出现100件以上乐器的洞窟6个。如五代第61窟,绘有经变画10种,有乐舞造型67组,出现乐器21种,182件次。其中绘有古琴8张,各式琵琶24把,排箫10把,笙11把,筚篥27支,横笛21支,拍板38串。实在是充实光辉,洋洋大观。
本期的《当代敦煌-丝路花雨》,作家李玉真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以自己对敦煌古乐的鉴赏和理解,通过隽永、优美深邃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敦煌古乐之美。
敦煌古乐欣赏二题
文 / 李玉真
嘈嘈切切有还无
——《敦煌古乐·琵琶独奏卷》欣赏
少年时我就认定了音乐的魔力,或许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家庭,过惯了每天在傍晚放留声机以乐伴餐、每周以家庭歌舞度周末的生活,以致音乐成了我的生死之交。记忆最深的是“文革”时与一群红卫兵赴京途中发高烧身如烂泥,情如死灰。火车停至昆明时如若天外飘来一曲,即刻我便像服下了灵丹妙药,重病痊愈,情怡身硬了。我永远忘不了著名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舒展优美的歌声:“太阳啊,霞光万道,雄鹰啊,展翅飞翔……”尽管后来几乎听不见这支歌了,但仅一次深切的体验,足矣。几十年来,我一直将美的音乐作为修生养德、抒情冶性、养身治病的绝妙药方与良师益友。
丙子年夏末,听了敦煌研究院的朋友赠送的敦煌古乐录音带,使我全然进入了新的音乐领域。录音带分《琵琶独奏卷》《民乐合奏卷》和《配词演唱卷》三盘。在世间到处都喧闹着通俗歌声的今天,能反复聆听当代敦煌乐神、中国音乐家席臻贯先生破译的全世界唯存的正宗中国唐代音乐,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幸事。
因民乐中我偏爱琵琶与古筝,所以让琵琶独奏曲首先入耳。
不配歌词的乐曲是通过欣赏主体的知识与联想去描绘、造型,同时唤起情感体验的。特别是琵琶,嘈嘈切切,弹挑错杂,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就敏锐地将无形的音乐语言变成的视觉形象作了流传千古的笔录:“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同时,诗人还在琵琶声中暗生忧愁,借“满座重闻皆掩泣”,问“座中泣下谁最多”,然后表述自己泪湿青衫的凄情。
《琵琶独奏卷》25首由中央民族乐团首席琵琶著名演奏家吴玉霞演奏。弹、挑、滚、勾、抹、摭、划、轮、推、挽等指法娴熟自不必说,无论曲子怎样变换,总不离嘈中有柔、切中有慢、动中有静、声中有无的意蕴。
第一首《品弄》,一开始就发出四个空弦散音,若空谷滴水,落入平滑润洁的清潭。接着在轻舒的弹挑中,又多次吟揉,给人不稳定感,以致聆听者随声轻摇如同乘坐于湖面微风中的一叶扁舟。第二首《(缺字)弄》主要用子弦弹挑,发出轻脆悦耳又牵动心弦的声响,使聆听者产生向上飞升之感。演奏者的纤指时而从缠弦和老弦划过,发出淳厚的坠落声,又使人感觉身心向下滑落,却仍未着地。这一曲,已无形间将聆听者诱入微风轻拂的半空之中,离脚踏实地的人世已有了距离。
第三首《倾杯乐》,演奏者在子弦上用了较多的长轮,犹如清纯的泉水叮冬,与白云绕身而过,让聆听者伸手可得。第四首《又慢曲子》又转入在中弦上的长轮,好似泉水又流入了幽深的隧道,使聆听者的感觉也幽暗而神秘起来。这时演奏者用双弹连续发出两根弦的浑响,间或勾弦发出清而不脆、短而不亮的单音,好像迷蒙中的夜游者如梦初醒的询问,而心安神泰的僧人正敲着木鱼引导迷误不觉的人超度。接着又出现了清朗的流水声,好像顿悟者与泉水同在白云间缭绕,人籁、地籁、天籁全无,人也变成一朵消散的云。
演奏的技巧可以强化曲子的内涵。曾经古代与当代的弹拨指法不尽相同,但隋唐时中原等地乐器改革时,已学习西域将木拨弹奏改为手指,也就是说,西域琵琶指法与沿袭至今的指法是一致的。那么,当代演奏就更能表达唐代敦煌古乐的曲义。
当然,古曲曲义主要来自乐曲本身的创作。25首曲子跌宕甚少,几首没有高亢激烈的情调。就是所谓《急曲子》,也没有顾名思义的急剧汹涌或急不可耐,整体给人的感觉是舒缓平和的。这种情调与优雅的抒情又大相径庭。抒情优雅可牵动人的喜、忧、念、虑,让人“一声肠一断”、“几年愁暂开”。而敦煌古乐琵琶曲却用舒缓平和去化解人的七情六欲,消融人的殚精竭虑。它像僧尼念诵经文,不仅让人用心去感受千年前唐代敦煌超然于世情之外的佛教氛围,而且引导人的身心进入道家的静虚之境。
唐代敦煌与西川一样,是未因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的冲击而中断音乐文化发展的重镇。饶宗颐先生的《行城文》里有“笙歌竟奏而啾留,法曲争陈而槽拨”的记载,说明由佛曲、胡曲、清乐与道调融合而成的法曲曾风行于敦煌。姜伯勤先生的《敦煌悉摩遮为苏摩遮乐舞考》一文又称其“天宝末年是其高峰”,可见25首唐代敦煌古乐的创作本身就离不开佛与道。这一定论是笔者在欣赏琵琶曲有此感觉之后才拜读到的。由此笔者想到了当时作者的创作美学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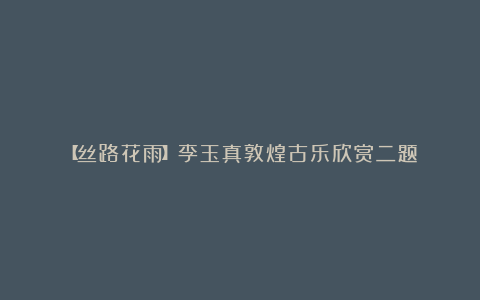
佛教将涅磐作为人生理想、追求净化思想的净土,亦即涅磐境界。道有崇尚自然全美、追求静观的思想境界。佛道影响着敦煌古乐作者的审美意识,使艺术创作成为高于生活静心观照的创造活动,因而用清静平和的音乐语言去唤起审美主体清和恬淡的感觉,让其用全身心去体验与自然合一直至空寂的心境。
以佛道理想为主要审美追求的唐代敦煌古乐琵琶独奏曲,最可贵的审美价值,是像神奇的渡筏,帮助审美主体将在现实中碰撞、挣扎或躁动不安的心灵送往最佳归宿——纯净与宁静的小岛。心的净静是神清气正的沐浴之水,是培育高情远致的沃土,是和谐生活成就事业的基础。净静以生博大之爱、圣洁之真、无形之象,正是美的最高境界。
写到这里,笔者由衷地感谢因积劳成疾而先逝的敦煌古乐破译者席臻贯先生。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古人的抄本只是竖着排列的类似日本片假名字形的字谱,席先生继任二北、叶栋之后新译出的乐谱不仅与唐代敦煌的审美追求相吻合,而且让当代人能够从中受到启迪,得到美的享受。无疑,唐代敦煌古乐在今古艺术领域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席臻贯的名字将与新译唐代敦煌古乐一样留芳百世。
声外俯仰亦从容
——《敦煌古乐·民乐合奏卷》欣赏
唐代敦煌古乐琵琶独奏以四弦琵琶嘈嘈切切的单一的音乐语言表现了佛道以净静求美的美学追求。配器的民乐合奏则主要以弹弦、吹管、打击三类乐器丰富的音乐语言扩展了美学追求的界限,拓宽了欣赏者的心理审美空间,由音乐生发的各种场面的形体律动也仿佛历历在目。
民乐合奏敦煌古乐的音乐语汇多而不乱,形象从容,因而声外俯仰舞之蹈之的形态表情也恬适从容。
第一首《品弄》以弹弦乐器混响慢起开始,紧接着出现低浑的弦音,如若四周漆黑,一束追光渐亮。好似万籁俱寂、万劫不复之时,又豁然间有了生命萌动的希望。少顷,弦管合声如潮涌起,由小至大,短促而清脆的定音鼓点瞬息而止。又宛如场灯骤亮,万物复苏,生命以最强的心音宣告自己的存在。
与后来的乐曲相比,第一首好像生命进行曲这个大的主题中的序曲。第二首《(缺字)弄》以琵琶清音与阮咸浊音相配慢起,好似男女二人翩翩起舞,一个丰肌罗裙、长巾舒卷,一个面丰体健,扬臂踏脚,二人俯仰交错,顾盼有情。其间时有碰铃与击板加强节奏感,使舞容更为清晰。后来响起的笙声如同生命在俯仰间的述说,用急板结束又好似意犹未尽。
第三首《倾杯乐》用定音鼓点开始,贯穿始终,使乐曲“均等律动”,增强了乐舞的气氛。乐曲展示的场面让人联想到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开始的“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的情景和百年后唐宣宗因敦煌从吐蕃统治中归唐,“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从葱岭踏歌舞到长安途经敦煌的情景。中速节奏使旋律如千里戈壁潺潺流淌的小河,不紧不慢,步履稳健,让人似乎看到群体生命在流动、流动,亦俯亦仰,从容不迫。
第五首《又曲子》之后,多首曲子弹弦与洞箫齐鸣。前者纷纷推出纵横交错的大小溪流作近景,后者让远处隐现深居简出的僧人俯仰慢舞的形态。生命的画面时隐时现,渐渐消散在大自然的真实与佛道延伸的玄学之中,让聆听者在体味生命飞升的同时享受生命与宇宙同样浩瀚无垠的惬意。其中第七首《又曲子》中板鼓声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传递着高深莫测的禅念。第十二首《倾杯乐》用了近似日本小调的乐句开头,又让曲调蕴含的佛性更浓,如若神奇的彩带挽住聆听者,任随它拉进佛界天地间。
敦煌古乐民乐合奏卷尽管配器较多,音乐语言丰富,但并没有与舒缓的主旋律发生冲突。配器只是在恬适从容这个大的审美趣味中灌注了由凡人与僧侣俯仰间表现的生命意识。而音乐形象中,俯,没有畏缩卑微之状;仰,亦无轻狂浮浪之态。全曲的场景没有烈风浮雨,惊雷闪电,生命过程没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它的审美价值在于最终又归于恬适从容,即生命与精神净化到与大自然合一,与宇宙同一。 唐代的大统一,带来了敦煌艺术空前的大发展。唐代是古代乐舞发展的鼎盛时期。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的百年间,由于吐蕃占领的河西重归于唐朝,经唐宣宗等人提倡之后,踏歌踏舞就流行于葱岭及河西。敦煌更甚,还有参加踏舞的少年由所在寺院用羊款付与报酬的规定。当代敦煌乐神席臻贯在破译古谱时,联系当时的情景,根据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观点,特别是根据乐舞的特点,将节拍译出,使乐曲的听觉形象化为视觉形象,即化为舞容。他又根据唐人信奉的《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将“俯仰”作为舞容的基本,以致配器后的音乐形象俯仰常见。
对唐代敦煌乐曲民乐合奏的译编,席臻贯也是查有所据的。他发现古人并不满足于乐器本身的和声,而早就懂得通过合奏可以获得更丰满的和声音响。这种和声合奏方法可追溯到《礼记·礼仪》的记载:“三笙一和而成声”。在经济与文化非常发达的唐代,也风行这种演奏方法。因此,由中央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分别配器并演奏的25首敦煌古乐民乐合奏卷,除了比较准确地传递唐代敦煌乐曲的审美追求以外,从表现形式上也令人信服。
( 图片来自网络,公益宣传,如有侵权请告知)
作者简介 李玉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重庆建专、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鲁迅文学院。曾任青海油田文学杂志《瀚海魂》编辑部主任、文学协会常务副主席。1998年从敦煌石油城退休,定居北京。在《文艺报》《文学报》《散文百家》《报告文学》《美文》《中国女性(中文海外版)》加拿大《光华报》《爱华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电视散文《西部女人》由央视多次播出,为主持、播音朗诵课件。著书7部。数十篇作品收入《新世纪优秀报告文学选(2001-2006)》《2010年中国散文经典》《2016中国散文排行榜》等全国各类文集。获上海《文学报》首届(1985年)命题文学全国征文一等奖。第二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全国“人与野生动物”征文一等奖等多种奖项。歌曲《采油姑娘上山来》(罗成谱曲、著名歌唱家于文华原唱,颁奖大会上由全总文工团龚七妹演唱)、《石油女性的风采》 分别获全国新世纪工人歌曲二等奖和优秀奖,《采油姑娘上山来》获全国“五一”文化奖。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 END –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