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两条互不相关的线索链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嫌疑人,德雷福斯的冤案该得昭雪了吧?
上篇,请点链接
撕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也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上)
无罪判决
军方迫于压力,开始了对埃斯特哈齐的审判。
佩里厄将军(Général de Pellieux)是当时法国陆军的一名高级军官,1897年底,他被派来调查“埃斯特哈齐是否叛国”的案件。
AI彩色还原佩里厄将军照
军方知道他忠诚、保守、仰慕上级,于是选他来主持调查,实际上是让他走个形式、替军方洗白。
他早在调查初期就被总参谋部暗示:“真凶不是埃斯特哈齐,而是那个皮卡尔中校。”
于是他从一开始就站在军方一边,不是在查真相,而是在制造无罪。
审判闭门进行了;证人被嘘、原告马蒂厄和露西(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妻子)被拒绝入席;法庭上违规辩护;三位笔迹专家“看不出相似”——结论是“笔迹伪造”。
最后,法庭仅用三分钟就宣判:“一致通过——埃斯特哈齐无罪。”
蒙冤的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命运没有一丝改变。
当埃斯特哈齐走出法院时,外面1500人高喊“法国万岁!”、“打倒犹太人!”。
埃斯特哈齐携情妇走出法庭
一个无辜者被判刑,一个真凶被赞美。这真是倒反天罡啊!
左拉的呐喊
与此同时在1897年年底,作家左拉也被舍勒尔–凯斯特纳说服了,就是之前提到的参议员,阿尔萨斯出身的共和党元老,法国参议院副议长,他是一个道德感极强、信仰理性的政治家。
AI彩色还原舍勒尔–凯斯特纳照
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长谈数小时,这场谈话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左拉当时已经是法国文坛的巨人,写过《萌芽》《娜娜》等自然主义小说。他一向关注社会正义,但对军方问题不熟。舍勒尔–凯斯特纳把皮卡尔的发现、埃斯特哈齐的线索、军方伪造的传闻全告诉他。
他最后说了一句被传为名言的话:
“Monsieur Zola, il n’y a pas seulement un innocent à sauver,
il y a une nation à guérir.”“左拉先生,这不只是要救一个无辜的人,
而是要让整个国家恢复理性。”
这句话击中了左拉的心,他回去以后整夜未眠。
AI彩色还原左拉照
于是,1897年11月25日,左拉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为德雷福斯辩护。他在文中写道:“这个国家正在用沉默杀死一个人。”
随后又写了两篇连载,但这些文章让他被极右翼猛烈攻击,《费加罗报》老板在压力下停刊他的稿子。左拉被封杀了,但他没有退缩,转向了另一家报纸——《黎明报》(L’Aurore)。
1898年1月13日,他发表了那篇震撼世界的公开信:
《我控诉!(J’accuse…!)》。
刊登《我控诉》的《黎明报》
这封信以共和国总统为收信人,以一个作家的名义,逐条点名控告军方伪造、法院不公、政府掩盖。整篇文章用冷静、理性的语言,写出了文学史上最有力量的愤怒。这篇文章震撼了法国,也震动了世界。当天,《黎明报》印了30万份(平时3万),被抢购一空。
同时,还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支持正义,纷纷发表文章。
此时法国分成两拨人:一拨喊“左拉万岁”支持重审,另一拨喊“处死犹太人”。城市陷入一种集体歇斯底里。
《我控诉》刊发后巴黎反犹集会,燃烧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的人偶
这里还有个插曲,现在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也是因为雷德福斯案而创办的。此时法国社会被撕成两半:支持重审的(德雷福斯派) vs. 反犹、保守的民族主义派。尽管支持后者的报纸占大多数,但一家体育报叫 《Le Vélo》(自行车报)是德雷福斯派的。
于是一群保守派就不乐意了,包括米其林(Michelin),阿道夫·克莱芒(Adolphe Clément)(自行车制造商)等。
他们愤怒地认为:“《Le Vélo》让体育变得政治化,让法国显得软弱。真正的法国需要力量与团结,而不是犹太人的阴谋与知识分子的怀疑。”
于是,他们集资办了另一份报纸来对抗《Le Vélo》。但销量远不如自行车报,为了推广新的报纸,主编想出一个主意:我们要办一场全国性的自行车赛。于是,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 诞生了。旨在用运动让被德雷福斯案撕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起来,顺便推广他们的新报纸。
书归正传,此时的法国政府做了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他们起诉了左拉。
1898年2月,左拉在巴黎塞纳重罪法庭受审。他被指控“诽谤军方”,而那些真正散布仇恨、喊“杀犹太人”的报纸,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审判充满暴力与偏见——
法庭外暴民辱骂左拉是“意大利佬”“无祖国者”;法庭内,法官不断阻止他谈论真正的案件,反复说那句著名的拒绝语:“这个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
最后左拉被判一年监禁,并罚款3000法郎。
左拉被审判后被愤怒的人群攻击指责
左拉选择了逃亡,他偷偷乘火车从法国北部的加来出境,经多佛抵达伦敦。尽管在那里他陷入各种困境,但是他说“我宁可流亡,也不能在谎言的国度里活着。”
但左拉的法庭辩论让“德雷福斯案”的全部细节第一次公开曝光。全国人民这才意识到:原来那桩“叛国案”,充满伪证与谎言。
真相逼近:伪造者自杀
1898年的夏天,局势突变。
新的国防部长卡瓦尼亚克(Cavaignac)上任。他是个“信念坚定的爱国者”,反复说:“我相信军队,我不相信阴谋论。”
AI彩色还原卡瓦尼亚克照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核查所有涉案档案,“干净地结束这场争议”。7月7日,他在国会公开宣称:三份文件足以证明德雷福斯有罪。
全法国欢呼,他成了民族英雄。
在调出当年的秘密档案时,部长秘书发现所谓“确凿证据”中有一封信——
笔迹颜色不一致,纸张被拼接,显然是一封伪造信。
调查追查到伪造者——正是军情局的亨利上校(Henry),也就是当年陷害皮卡尔、伪造“亨利信”的人。
AI彩色还原亨利照
1898年8月30日,卡部长亲自质问亨利,最终亨利承认了自己伪造了一切。这是卡部长一生中最震撼的时刻。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议会中振臂宣誓的“铁证”,居然是假的。换句话说,他刚刚在全国面前“以谎言证明真理”。
那一刻,他确实看出了整个军方系统都可能参与了掩盖真相。震怒之下,他命令把亨利关进了牢房,明天再审。
然而,8月31日清晨,警卫发现亨利割喉自尽了。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我宁愿死,也不愿看到我祖国蒙羞。”
刊登亨利自杀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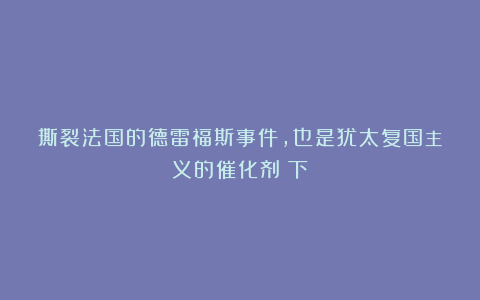
这一刻卡部长当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造假,而是一条从参谋部、情报局、将军办公室直通内阁的造假链。
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说:“这个人做错了,但这不影响结论。”
他依然坚信:“或许文件有假,但德雷福斯有罪的’事实’不假。”
政府被夹在两股火焰之间:一边是法律的呼声,一边是军方和街头民族主义的咆哮。国防部长卡瓦尼亚克迫于亨利的自杀而被免职了,但旋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重审的头号旗手。他决定在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直到去世,卡部长都没有公开承认自己错了。
接任的新国防部长祖尔兰丹将军更听命于总参谋部,他公开反对重审,极端报纸随即大肆叫嚣:重审,就是战争!整个法国几乎到了要撕裂为内战的程度。
可政府这次硬了心,9月26日投票决定把案子交给最高法院。刚上任的祖部长辞职了,又上任一位沙部长顶不住压力,也辞职了。最高法那边也没闲着,高法的相关庭长也因为派别问题辞职换人,走马灯的国防部长,一锅粥的法国政坛。
重审:真相被绑着手
1899年,最高法院终于开始重审了。司法部长把案子正式送上法庭,民族主义报纸发动了一场丑陋的反犹运动,尤其攻击主审法官罗厄夫,说他“是德裔逃兵”。可尽管军方拒绝配合,真相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刊登最高法院法官的报纸
卡瓦尼亚克作证两天(之前的那位卡部长),结果离奇的是,这反而帮了德雷福斯派的忙。卡部长本想以权威姿态为军方定调,却在“展示证据”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个致命漏洞——
他证明了那封信写于德雷福斯已经无法接触机密的时期。
信中涉及到的军事情报只能是发生在1894年8月以后,而德雷福斯已经在当年7月就从可以获得情报的总参谋部调去军校了,这意味着,德雷福斯根本没有可能接触这些情报。
卡部长还声称,笔迹“相似”,但在法庭和后来的复查中,皮卡尔和专家发现,真正的笔迹更像埃斯特哈齐。当他展示这些样本时,专家和记者都注意到里面存在多次临摹痕迹,尤其是笔画起止不连贯、纸质不同。
荒唐的是,一个“反复审派”自己在逻辑上推翻了自己的阵营。
1899年2月9日,刑事庭终于抛出了两颗炸弹:
第一,埃斯特哈齐使用的信纸与“叛国便条”完全一致;
第二,那份所谓的“秘密档案”,几乎是空的。
这两条发现足以击碎整个控罪的根基。
6月3日,最高法院庄严宣判:撤销1894年判决,发回雷恩军事法庭重审。
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
至少在那一刻,司法似乎战胜了权力。左拉从流亡地归来,皮卡尔获释。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案子被“发回”军法系统,也就意味着,法官依然是军人。雷德福斯的冤案能否昭雪,还未可知。
8月7日,军事法庭的审判开始。德雷福斯被押解回国,消瘦、苍白,但镇定。辩护团队却分成两派:年长的德芒日想低调争取无罪;年轻的拉博里要掀翻军方的黑幕。
8月14日,拉博里在上庭路上被枪击,凶手逃脱。这一枪,几乎让真相再次倒地。
刊登最拉博里遭到暗杀的报纸
9月9日,判决下达:有罪,但情节减轻。十年监禁。七名军法官中,两人反对。
叛国罪还能“情节减轻”?这不是法律,而是妥协——一种用荒谬包裹的面子工程。
刊登军事法庭宣判的报纸
德雷福斯几乎崩溃,蒙冤六年,坚信正义,换来的却依然是叛国罪,只是变成了轻微叛国。1899年9月19日,总统签署特赦令,21日德雷福斯出狱。在许多人眼里,这近乎“默认罪名”——但从法律上,他仍有权继续寻求平反。
外面的阳光刺眼,但正义仍被关在铁窗里。
1899年11月17日,政府提出大赦法案;到1900年12月,这部法案最终通过。伪造、陷害与造假者在法理上得以免责,社会则以“总算可以翻篇”为理由选择沉默。
舆论哗然,但国家松了一口气。1900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在即,法国厌倦了撕裂。军方宣布:“事件结束了。”
德雷福斯事件终于落幕了。
可留在法国的,是一道无法缝合的伤口。
荣誉与正义,两种信仰在那场审判中彼此撕咬;而从那以后,法国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法国了。
尾声:迟到的正义
1906年,最高法院终于宣告他无罪,恢复军衔。
他重新穿上军装,出席国会仪式。
掌声稀稀落落,他只是轻声说:“法国万岁。”
AI彩色还原德雷福斯复职后的照片(中间4人里的右2)
1908年,左拉国葬。
德雷福斯到场,结果被极右翼分子开枪击伤。
子弹擦过他的手臂,他没有还手。
这个国家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但已经晚了十二年。
自由的幻觉
1900年4月14日,巴黎世博会如期举行。巴黎灯火辉煌,摩天轮旋转,乐队奏起《马赛曲》。
巴黎世博会的海报
人们谈文明、谈进步,展示着电力、地铁、汽车、摄影、电影等现代科技,向19世纪挥手告别。
没有人谈那个曾被关在魔鬼岛上的犹太人。
而对犹太人而言,这场事件像一记警钟,几年后,当时在巴黎亲眼目睹反犹乱象的维也纳记者赫茨尔写下《犹太国》。
他在序言里说:
“德雷福斯事件让我明白,即便在巴黎,犹太人也没有祖国。”
这场冤案,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
它是一场文明的自我崩塌。
当民族、信仰、舆论与权力交织成一张网,
理性就像那封撕碎的信,被拼接成任何人想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