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研究》专题
司豪强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秦钜鹿郡[1]地处今河北省中南部,属华北平原。目前关于钜鹿郡沿革史的脉络已大体梳理清晰[2],但其沿革中尚有一些关键的争议点和模糊点有待继续探讨。尤其是秦至汉初的钜鹿郡沿革情况争议颇多。辛德勇便曾感慨始皇三十六郡中“设在赵国旧地的邯郸、钜鹿两郡,情况最为复杂”[3]。故而,本文试对秦钜鹿置郡时间、与河间清河二郡关系及是否废弃等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更好把握秦钜鹿郡的具体设置情况。
1.
钜鹿置郡时间之争议
钜鹿郡置于秦,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所划定的三十六郡之一[4]。关于其设置时间学界历来有不同见解。
钜鹿置郡的最早记载为《汉书·地理志》(以下皆称《汉志》),然其仅言:“钜鹿郡,秦置”[5],寥寥数语,但言秦置而无准确系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有明确置郡时间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灭赵以为钜鹿郡。”[6](以下皆称“郦注”)
据郦注,杨守敬认为:“考《史记·始皇本纪》,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赵地东阳……二十五年,王贲虏代王嘉。钜鹿郡正赵东阳之地,似不得至二十五年灭代始置郡。郦氏盖合灭代之年为说耳。”[7]杨守敬怀疑郦注所言二十五年(前222)是为契合秦灭代时间,而钜鹿置郡可能更早。后晓荣亦据此以为“郦注误,杨说可从”[8],然二人皆未言明置郡准确年份。
王国维未取郦注,而求诸《汉志》,认为钜鹿郡“当为十九年灭赵后所置”[9]。马非百[10]、谭其骧[11]二位先生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12]及《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尽定赵地为郡。”[13]两条史料亦认为钜鹿置郡应在始皇十九年(前228)。
但辛德勇却考证十九年赵故地所置当为赵郡,到始皇二十六年重划天下,设三十六郡时,分赵郡设置钜鹿郡[14]。何慕亦持十九年置赵郡说,又折中认为郦注未必为误,钜鹿郡“或如《水经注》记载于秦始皇二十五年设置,或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时析分,置郡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到二十六年之间(前222-前221)”[15]。而辛、何二说成立的前提是对赵郡的重新认识和合理推断。
过去学者们多认为秦灭赵,置赵郡、钜鹿郡,统一后赵郡更名邯郸郡,其沿革与钜鹿郡无干。这种看法大概始于《元和郡县图志》,其文曰:“今州(定州)盖秦赵郡、钜鹿二郡之地。”[16]《太平寰宇记》也有相同记载,可见唐宋时期就已将赵郡、邯郸郡混淆并用,直到近些年依然有学者赞同这种说法[17]。但周晓陆、孙闻博的研究开始打破传统的观念,他们认为:“秦统一后,又分赵地为邯郸、钜鹿等郡,因此,赵郡可能为嬴政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间所置。”[18]辛氏在此基础上考证出“赵郡应设置于秦王政十九年”[19],何氏亦持此说。如此一来,若秦灭赵置赵郡,而邯郸、钜鹿二郡由其析置,则“二十五年之前说”和“十九年置郡说”便须修正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赵郡是否析置钜鹿郡?从秦灭赵“尽定赵地为郡”[20]来看,当如灭韩后,“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21]一样将其故地悉置为一郡。且在秦始皇十八年(前229)兴兵伐赵之前,赵国的领土已所存无几。据辛氏考,当时赵国辖域“只有邯郸周围和钜鹿及迤东地区,还有北部的代郡”[22],代郡和邯郸之间早已为秦国拦腰截断,代郡无异于飞地[23]。由于当时赵国直辖地十分促狭,故被灭后当置一郡为宜。只是赵郡是否如辛氏所论包含钜鹿一带尚待进一步考察,如赵郡未含钜鹿地,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详见下文)。
综合诸家考证,钜鹿置郡时间大致有四种观点(即二十五年之前、十九年、二十六年、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之间)。杨守敬很早便对郦注所云始皇二十五年置郡说产生质疑,认为置郡时间更早。在此基础上,王、马、谭等诸位先生根据传世文献皆推断钜鹿置郡当在秦灭赵之始皇十九年。但该说随着更多秦封泥、秦简的整理刊布[24]而被学者们重新修正,于是关于钜鹿置郡时间产生了辛德勇“二十六年”和何慕“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间”两种说法。
钜鹿置郡时间虽颇有争议,但秦钜鹿郡延续至西汉向来为学界所认可[25]。只是《秦汉卷》却提出秦至汉初时段,钜鹿郡被废[26](姑且称其“废弃说”)。其核心观点便是秦代清河、河间二郡瓜分了钜鹿郡,尤其是清河郡囊括了钜鹿地区。故论证钜鹿郡是否废弃之前,须先理清钜鹿与清河、河间二郡之关系。
2.
钜鹿郡与河间、清河二郡之关系
《战国策》记载了秦惠文王时河间入秦经过及文信侯吕不韦欲攻赵以广河间二事:
(赵武灵王)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27]
“燕、秦所以不相欺者,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广河间,……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28]
《史记·张仪列传》:
今赵王已入渑池,效河间以事秦。[29]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30]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31]
岳麓秦简374号简也有关于清河的记载:
清河假守上信都言。[32]
此外秦封泥有“河间太守”[33]、“河间尉印”[34]、“清河太守”[35]和“清河水印”[36]各一方。
学者们据以上材料认定河间、清河两郡亦为秦郡[37],只是二郡与钜鹿的沿革关系尚不清楚。目前存在极大争议的是:究竟先置钜鹿郡后析分河间、清河,还是先置河间、清河二郡后并其地而置钜鹿?
后晓荣认为河间、清河二郡为秦统一后由钜鹿郡分置(姑且称为“分置说”)。理由是秦惠文王时占有“河间地”为插花地,后为吕不韦封邑,不可能置郡。秦统一所置三十六郡中,赵地仅有邯郸、钜鹿二郡。推测河间郡为统一后因钜鹿地广而析分,至于清河郡,仅推测或为钜鹿郡分置而来[38]。
辛德勇总结诸说,得出推断:河间曾为吕不韦封邑,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吕不韦死,地改为郡。十四年(前233),秦攻占清河区域,置清河郡。十九年,灭赵置赵郡。因钜鹿在战国时便是赵国境内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于是二十六年便从赵郡中分出大陆泽附近的钜鹿地区,与河间郡以及清河郡东部地区合并组成钜鹿郡[39](姑且称为“合并说”,参见图1[40])。
图1 秦钜鹿郡形成示意图(辛氏推断)
何慕据《齐鲁封泥集存》序认定“河间太守”、“清河太守”两枚秦封泥极大可能出自山东,因其为故齐国之地,从而推断河间、清河二郡至少存在于秦统一之后。但何氏又以为不能因此否定钜鹿郡的存在,钜鹿郡建置应存疑为妥(姑且称为“存疑说”)。[41]
周群结合王国维推论[42]和秦封泥有“河间太守”而论定河间置郡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43],又据秦封泥和岳麓秦简判定秦始皇二十六年后秦置清河郡[44](姑且称为“河前清后说”)。
以上关于四种观点中,仅辛氏“合并说”是主张河间、清河置于始皇二十六年前,“分置说”和“存疑说”很相似,二者均认为河间、清河二郡为秦统一后由钜鹿析置,而钜鹿仍存,只是推论过程不同。那么哪种说法更为可靠呢?
后氏仅言河间为吕不韦封邑不可能置郡,但吕不韦死时,距秦统一尚有14年时间,距灭赵亦有7年,后氏并未交代这期间秦国该如何处置“插花地”(与本土不接壤)的河间,秦当不会给河间留下统治空白,不置封邑,自然便置郡或归入临近之郡。若从辛氏,河间、清河置郡早于钜鹿郡,河间的管理形式在逻辑上便说得通,然何氏所论封泥出土地点一说又使辛氏之说变得扑朔迷离。
何氏推断出清末所出两枚封泥的出土地点极有可能是山东省。“山东为齐国故地,该省所出秦式封泥应当全部是秦统一之后之物,最早也只能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之物。秦统一之前,秦国的两位太守不会交通敌国,把公文发往齐国境内。这就可以证明,河间、清河二郡至少存在于秦统一之后”[45]。由此认定辛氏因未注意到封泥出土地点而导致误判。笔者以为此言不确,且不论这两枚封泥尚有一定可能性是出自直隶地区,即便果真出自山东也未必是出自齐国故地。因清末山东省不等同于齐国故地,原属赵国后被秦国占领的清河部分地区也在山东省境内(参见图2[46])。如此,两郡封泥应即便出自山东,也属秦国境内,二郡太守不存在交通敌国之嫌。何氏所论两封泥出齐国故地,二郡至少存在于统一后的说法便不成立了,而辛氏推论(清河、河间统一前置郡)目前仍是可信的。
图2 清河郡跨省示意图
再说“河前清后说”,周氏所论证过程有些前后矛盾[47],然而其结论却未必错误。据上文可知吕不韦死后,其封邑河间很可能仿照“穰侯卒于陶,……秦复收陶为郡”[48]的惯例进行置郡管辖。另据辛氏考察清河地区大概在秦始皇十四年入秦。此时期的清河地区与本土接壤可以就近并入其他秦郡,待统一天下后再重新分置。
综而言之,诸说纷杂,关于钜鹿、河间、清河三郡建置细节当存疑为妥[49]。
3.
《秦汉卷》钜鹿郡“废弃说”之辨析
在上文基础上,接下来分析一下《秦汉卷》所持之钜鹿郡“废弃说”是否可信。
欲辨析其可信性,首先需要清楚“废弃说”所持依据为何?笔者将其依据概括为如下五条[50]:
一、据岳麓秦简374号简和《汉志》内容推断秦清河郡界已西至信都(项羽改襄国)县,即清河已囊括了钜鹿郡地(《汉志》襄国属赵国,钜鹿县恰位于清河郡与襄国之间,故有此论),故秦汉之际必有一段时期无钜鹿郡存在之可能(下文皆称“依据一”);
二、因《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陈豨拜为钜鹿守”[51]有误,故汉初必有钜鹿郡的依据没有了(下文皆称“依据二”);
三、“秦汉之际有关赵地其余几郡的信息都可以从史籍记载中寻到蛛丝马迹,独钜鹿郡毫无同时存在之证据”[52](下文皆称“依据三”);
四、陈豨反叛战事中竟没有提及钜鹿之名,“即便提及为汉守者也未尝提及钜鹿”,故钜鹿郡之名当时不存在(下文皆称“依据四”);
五、根据《水经·浊漳水注》记载:
秦始皇二十五年,灭赵以为钜鹿郡,汉景帝中元年,为广平郡,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赵敬肃王子为平于国,世祖中兴,更为钜鹿也。[53]
认为西汉初年实无钜鹿郡,应是景帝时置广川、清河两国,后分两国地置广平郡,之后广平再析分钜鹿。(下文皆称“依据五”)
据此五条依据,《秦汉卷》认为钜鹿郡在秦始皇时即被废弃。
其次,便可试着逐一分析“废弃说”所持五条依据是否可靠。
一、“依据一”难以自圆其说。即便清河曾囊括钜鹿全境亦仅可说明二郡并非同时设置,如依辛氏之说清河先于钜鹿置郡,那么便不能得出“秦汉之际必有一段时期无钜鹿郡存在之可能”[54]的推论,更何况就算秦清河郡曾辖信都,也未必钜鹿郡完全被囊括,二郡完全可以并存[55]。
二、再说“依据二”,即使陈豨“钜鹿守”记载为误,也不能贸然因缺少一条材料而抹杀汉初钜鹿郡的存在可能性。
三、“依据三”所言:“秦汉之际有关赵地其余几郡的信息都可以从史籍记载中寻到蛛丝马迹,独钜鹿郡毫无同时存在之证据”的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
《秦汉卷》提到多见秦汉之际的赵地其余几郡信息如下:
《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云:“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卷96《张丞相列传》云:“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汉书》卷1《高帝纪》云:“三年,韩信东下井陉,斩陈余,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史记》卷8《高祖本纪》有,项羽“封成安君陈余河间三县,居南皮”,则河间郡亦存于秦末。以此可推断,恒山、清河、河间三郡当在秦末存世,且至汉初亦是如此。[56](恒山即常山,为避汉文讳改)
此处稍有援引史料问题,不作赘言[57]。重点在于所引史料并未涉及清河,单就传世文献而言,难以推断清河在秦末存世,仅可言其存在于汉初[58]。再者,所引史料虽提及“河间三县”,是因战国时河间地便是一相对独立的行政和地理单位,或为史官不拘文法所致,难以据此说明河间郡存在于秦末,遑论汉初。至于恒山、上党、代郡本与钜鹿郡建置无关,不做探讨。
另外,秦汉之际的“钜鹿”在史书中十分活跃,并非如其说言没有存在的证据。《史记》《汉书》在钜鹿之战前后,多次提及钜鹿,《秦汉卷》应将史料中出现的“钜鹿”认定为钜鹿县、钜鹿城。故而忽视了钜鹿郡在秦末的“登场”。但如此一来,既然不能认定史料中提到的钜鹿为钜鹿郡,那么又怎可轻易便断定史籍中出现的河间必为河间郡呢?可见,当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河间、清河二郡在秦末存世,而钜鹿独废,“依据三”难以自圆其说。
四、“依据四”所言非虚,但陈豨反叛战事中没有提及钜鹿之名,仅可说当时战事并未涉及钜鹿郡,且当时钜鹿郡为赵国属郡,每每言及“赵”自然包含钜鹿郡,而单列出的郡名基本遭受叛军袭扰或为当时汉军防守要地。况且即便西汉初年果无钜鹿郡,也未必袭自秦末。
五、对于“依据五”所引《浊漳水注》记载,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认为:“这段注文以为巨鹿郡即广平郡即平干国即东汉巨鹿郡,未言明景中元年巨鹿分广平。事实上,广平由巨鹿所分,故疑此处注文有误。”[59]北魏距西汉初年已甚远,郦道元混淆钜鹿、广平郡二郡亦在情理之中。若《秦汉卷》认为郦注无误,且认定秦时废钜鹿郡,则东汉建立,钜鹿方才复置,岂非《汉志》钜鹿郡为虚构?或尽依郦注之说,则钜鹿郡当未废于秦,而应于景帝时更名广平,则“废弃说”不攻自破。但《秦汉卷》又以为西汉钜鹿郡复置,岂非变相承认郦注有误?故无论郦注是否有误,“废弃说”都陷入了前后矛盾的境地,此举实为仅采郦注中钜鹿郡曾在西汉不存在的利己说法作为“废弃说”支撑论据,而肢解郦注史料的原意,笔者窃以为不可取。
由上可知,“废弃说”看似证据颇多,却未必是确凿之论。秦钜鹿郡“废弃说”若要成立,目前还缺少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此外,《秦汉卷》在“废弃说”前提下还提出了汉代钜鹿郡复置时间。此处不妨先假设“废弃说”成立,即秦钜鹿郡真的被废弃了,直到汉代才被重置,则其重置时间果如《秦汉卷》所认为的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吗?[60]
《秦汉卷》据《汉书·路温舒传》记载:温舒为钜鹿东里人,为县狱史,“太守行县,见而异之”[61]。认为“此时钜鹿县当不为郡治,否则太守何须行县方见之”。推测陆舒温为武帝时生人,故可能至武帝初年,钜鹿郡仍未置;据此,又因征和二年(前91)广平改郡为国,故疑即此年将广平北部地析置钜鹿郡[62]。
因陆舒温为钜鹿东里人,《秦汉卷》便理所当然认为此处的钜鹿为钜鹿县,而东里是县下属之里[63]。按其说法,则钜鹿县不为郡治,没有钜鹿郡存在,故有太守须行县。但是,这里有另外一种解释,即陆舒温为钜鹿郡东里县人。秦时,有杠里县,而《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条下又有槐里县,且槐里为“高祖三年更名”[64]。《汉志》钜鹿郡条下虽无东里县,但并不排除钜鹿曾短暂置东里县后废而汉志缺载的可能,且《汉书》传记介绍人物籍贯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以郡(国)县或直接以县命名,介绍某县某里极为罕见[65],故笔者窃以为此处很有可能是指钜鹿郡东里县。如此一来,钜鹿郡郡守行县至东里县也便可以说得通,且至少在武帝时期是有钜鹿郡的。故而即便秦钜鹿郡果真遭到废置,也未必会如《秦汉卷》所论述那般被废了那么长的时间。
4.
关于钜鹿郡沿革的几种推论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使秦钜鹿郡的整体面貌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笔者也得出了一些浅见。
首先,钜鹿置郡时间方面。
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
秦将王贲虏王嘉,秦灭赵。[66]
可见司马迁著《史记》时是将赵公子嘉所建代国视为赵国的延续,故直到始皇二十五年虏代王嘉之时方言灭赵。据此,笔者以为郦注所谓“灭赵”当源自《史记·六国年表》的说法,而灭代之年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六国仅存齐国,秦国已经拥有了重划郡县的基础和余力,或在此年秦国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定郡县,钜鹿郡得以设置。故郦注未必有误,且诸多秦郡郦氏皆有准确置年岂皆有误?[67]当然,辛德勇认为钜鹿郡于秦统一后,重划天下时设置也极有可能,但终究缺少了史料支撑。故笔者窃以为何慕结论更为合理,即钜鹿置郡时间当在秦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之间。且若无其他新材料出现,仍当采用郦注所载时间为宜[68]。
其次,关于钜鹿置郡有几种可能的情况。
考察秦攻赵史事可知,秦始皇十四年(前233),秦“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69],再参考《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十四年)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70]此年攻赵战事皆为桓齮率军负责,而桓齮军当先攻平阳,次攻宜安。
《秦汉卷》曾据岳麓秦简374号简认定清河郡曾囊括钜鹿郡地,虽可能是混淆二郡置郡先后次序原因发生误判,但却明确指出了信都县曾为秦清河郡辖地[71]。为何清河郡会辖信都呢?笔者以为信都当在桓齮军北攻宜安路线上,桓齮军顺道攻占了信都,而此年秦国整合桓齮所攻占赵国领土(不含宜安)设置清河郡[72],信都自然归属清河郡[73](参见图3[74])。
关于这条北攻路线,除了根据信都为清河郡属县这一结论倒推外,还可参考汉初樊哙北攻陈豨叛军路线:
(樊哙)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75]
据此可知,樊哙先攻襄国、次至柏人,最后进入常山境内作战。故笔者推测桓齮军很可能也选择了相同路线。而樊哙进军路线和其最后降定诸县皆属清河常山二郡,也说明在汉初清河郡是与常山郡接壤的。
又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
(汉武帝时)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76]
可推测甚至到汉武帝时,清河和常山二郡仍是接壤的,故笔者所绘图3当有一定的可信度,且清河与常山接壤是有一定历史传统的,这一传统应当始于桓齮军攻赵时的路线及之后的信都一带归入清河郡。
如此一来,根据十四年以桓齮军攻赵所得领土置为清河郡,可对钜鹿郡沿革产生不同的推论。
其一,若此年桓齮军亦攻占钜鹿一带,而钜鹿地区归属清河郡,则钜鹿郡当为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组合清河郡东部与河间郡所置(参见图3);其二,若攻占钜鹿一带,而钜鹿与清河二郡并置,则钜鹿置郡时间当亦为秦始皇十四年。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若桓齮军攻赵所得领土分置二郡,则据地形推断信都一带应当划归钜鹿郡而非清河郡,不如此则清河郡辖域会很奇怪(参见图4)。当然,也不可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只是如此一来,二十六年之钜鹿郡当为组合钜鹿郡、河间郡及清河东部三郡之地所置;其三,若此年桓齮军未攻占钜鹿一带,直到十九年秦灭赵,置钜鹿郡(参见图4),二十六年之钜鹿郡当为组合钜鹿郡、河间郡及清河东部三郡之地所置;其四,若未攻占钜鹿,十九年秦灭赵,将新占领的钜鹿地区直接归入清河郡管辖。则钜鹿郡当为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组合清河郡东部与河间郡所置(参见图3)。
由上可见,因为秦始皇十四年这次桓齮攻赵的军事行动,使得钜鹿地区与赵国直辖地分割开来,故日后赵郡的设置与沿革当与钜鹿郡沿革无关。这虽与辛德勇先生推论不完全相符(赵郡部分地区与河间郡以及清河郡东部地区合并组成钜鹿郡),但笔者所提之四种推论正是在辛氏提出的赵郡、河间、清河三郡置郡于钜鹿郡之前的推论基础上形成的。辛氏之推论原本是符合逻辑说得通的,只是随着岳麓秦简374号简公开面世,产生了信都属清河郡的证据,笔者方才在辛氏推论基础上稍作调整,将赵郡沿革与钜鹿郡沿革割裂开来,从而提出四种钜鹿郡沿革的可能性。这四种推论前提是辛氏提出的秦始皇十四年置清河郡之说,当然何慕和《秦汉卷》所论之信都属清河郡也是其重要依据。
综合来看以上四种推论,第一、四种推论只是钜鹿一带入秦早晚的差异,对置郡而言并无差别,钜鹿郡皆为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组合清河郡东部与河间郡所置(姑且称之为“猜想一”);第二、三种推论若成立,则始皇二十六年之钜鹿郡皆为组合钜鹿郡、河间郡及清河东部三郡之地所置,只是置郡时间上有所不同(姑且称之为“猜想二”)。当然,仍以第二种推论的秦始皇十四年置郡可能性最低。因有郦注有准确时间记载和史书未有秦收钜鹿记载,故第四种推论成立的可能性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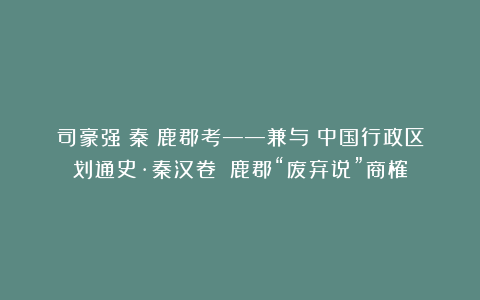
在这两种猜想的基础上,再回头看谭其骧等人所提出之秦始皇十九年置郡说也不当为谬误,而为其中一种可能(即推论三)。且置郡时间的说法,多出一种概率极低的推论,即钜鹿与清河二郡在秦始皇十四年并置(即推论二)。
当然,辛氏秦始皇十四年置清河郡的推论建立在秦将桓齮定武城,且武城为清河重镇东武城的基础上。若从杨宽之说,则此武城在邺城附近,且宜安之战桓齮败绩[77],桓齮败走后,信都一带当复为赵有。如此,则清河郡与赵郡可能共同置于灭赵之始皇十九年,只是信都不知何故划入清河郡。钜鹿郡当为组合清河东部与河间郡而置郡(大致仍符合图3)。
图3 桓齮攻赵路线图兼秦钜鹿郡形成示意图(猜想一)
图4 秦钜鹿郡形成示意图(猜想二)
此外,“废弃说”之“依据四”因陈豨反叛战事中没有提及钜鹿之名,而推断钜鹿郡不存于汉初。如依此说,则考察秦末亦未尝提及清河,尤其是钜鹿之战前后,史仅言“陈余北收常山兵”[78]、“张敖亦北收代兵”[79]而未尝见清河、河间之名。若当时二郡存在何以不见其支援钜鹿?是以当时应无二郡。且到秦郡大举来攻时,张耳与赵王歇为何不仍居信都,却要东入钜鹿城?此举应是因信都城为普通县城难以御敌,而当时钜鹿应为东部唯一郡城重镇,且邯郸大部分已沦陷于秦军,赵国可就近依靠的力量为钜鹿兵,东移钜鹿亦是出于就近依靠钜鹿兵御敌的打算。据此,笔者窃以为秦始皇二十六年时存在的钜鹿郡当延续秦末。当然目前尚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当时清河、河间二郡秦末不存,故此说也只为推论。
5.
结语
钜鹿置郡时间众说纷纭,至少存在秦始皇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六年及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四种可能性。其中秦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置郡之说相对可靠,或仍采郦注所载时间之秦始皇二十五年亦未尝不可。
钜鹿郡与河间、清河二郡之间的关系复杂,尤其是钜鹿、清河二郡之间存在着辖域重叠的情况。仅可说明钜鹿与清河二郡很可能非同时设置,并不意味着清河、河间取代钜鹿郡。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尚不足以断言秦末至汉初钜鹿郡曾遭到废弃。《秦汉卷》“仅由某个时间点上的置郡情况,贸然否定另一个时间点土某个郡的存在,太过武断”[80]。钜鹿郡的具体建置情况,仍当以存疑为妥,但本文关于钜鹿郡置郡情况的四种推论或可作为参考,而更为准确细致的建置沿革情况尚待新材料的发现和刊布方可进一步推进和补充、验证前人之说。
注释:
[1] 目前存在“钜鹿”和“巨鹿”两种写法,文中(除引用他人研究部分外)皆采用“钜鹿”写法。
[2] 关于钜鹿郡沿革的专门研究成果有:乔国华:《历史上的巨鹿》,《历史教学》1997年第9期;程动田:《影响巨鹿行政区划变迁的因素分析》,《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沈媛:《秦汉至唐中叶巨鹿郡行政区划的变迁》,《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侯纪润:《汉唐时期的巨鹿——以行政区划为中心》,收录于秦进才主编:《巨鹿历史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20页等;此外对秦钜鹿郡有所涉及研究成果还有: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司豪强:《汉唐间廮陶县政区变迁考察》,《邢台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等。
[3]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辑。后收入氏著:《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61页。
[4]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前人研究已经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辛德勇先生提到谭其骧先生的结论(谭氏结论三十六郡包括钜鹿郡),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并且他“综合诸家考证见解,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秦郡”有三十三个, 这三十三郡亦包含钜鹿郡。周群《秦代置郡考述》(《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所举诸家公认三十三郡与辛氏完全相同,徐世权《学术史视野下的秦郡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详细梳理了秦郡研究史,亦未有学者曾否认钜鹿为秦郡之说。故笔者遍观目前学界研究,关于钜鹿郡置于秦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5]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6页。
[6]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页。
[7]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55页。
[8] 后晓荣:《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5页。
[9]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10]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649页。
[11] 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第300页。
[13] 《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2839页。
[14] 辛德勇:《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70—72页。
[15]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38页。
[16]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北道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509页。
[17] 如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邯郸郡(赵郡)条下云:“估计赵郡应为初郡名(或暂置名),邯郸郡或为统一后改置名”将赵郡附于邯郸郡之后,明显认为赵郡统一后更名邯郸郡。也大概是由于对赵郡的这种看法,后氏才会对钜鹿置郡时间采取了一种模糊的处理,但大体上还是认为在始皇二十五年之前的。
[18] 周晓陆、孙闻博:《秦封泥与河北古史研究》,《文物春秋》2005年第5期,第44页。
[19] 辛德勇:《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65页。
[20] 《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2839页。
[21]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300页。
[22] 辛德勇:《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65页。
[23] 辛德勇考证:“在秦始皇十四、五年间,恒山周围区域已并入秦境。”故可言代郡和邯郸之间已被秦拦腰斩断。详见氏著:《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20—21页。
[24] 关于秦封泥、秦简等刊布情况与秦郡研究的相关情况,可参看徐世权《学术史视野下的秦郡研究》第四章第二节《2001—2016 年间学者依据出土文献的秦郡研究》,第166—222页,及第三节《2001—2016 年间学者综合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第223—239页。
[25]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周振鹤先生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便认为:“《汉志》云巨鹿郡秦置。高帝四年以封张耳赵国,九年析置清河、河间两郡,……景帝三年,赵国之巨鹿支郡属汉。”可以看出当时周先生认为自秦到汉初钜鹿郡是存在的。且前文凡有考证钜鹿郡沿革除《秦汉卷》外皆持汉钜鹿郡是秦钜鹿郡的延续的观点。
[2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4—27页。
[27] (西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7《赵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42页。
[28] 《战国策笺证》卷7《秦五·文信侯欲攻赵》,第460页。
[29] 《史记》卷70《张仪列传》,第2791页。
[30] 《史记》卷71《甘罗附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816页。
[31] 《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第3216页。
[32]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页。
[33] 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51—252页。
[34] 陆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碑林辑刊》第11辑,第316—317页。
[35] 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第195页。
[36] 陆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第315页。
[37] 参见辛德勇:《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12—64页;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第97—105页;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58—60页等。这些学者研究成果,包含对钜鹿、邯郸、河间、清河等郡的考证,并认定河间、清河亦为秦郡。另有如周晓陆、孙闻博:《秦封泥与河北古史研究》、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等诸多文章亦对河间、清河二郡做过讨论,此不一一列举。
[38]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第97—105页。
[39] 辛德勇:《秦代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12—72页。
[40] 图1系结合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附图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秦时期“山东北部诸郡”组图绘制而成。仅为表示诸郡位置与辖域大意,具体郡界划分尚须深入研究。
[41]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58—60页。
[42] 王国维:《观堂集林》(上册),第339页。
[43] 周群:《秦代置郡考述》,《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44] 周群:《秦代置郡考述》,第40—41页。
[45]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59页。
[46] 图2系结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时期“冀州刺史部”组图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中“清末山东省政区图”附图绘制而成。秦清河郡已无法绘出详图,其大体范围应与西汉时期接近,故此处参考西汉清河郡。
[47] 周群《秦代置郡考述》中河间郡条下论曰:“今秦封泥有’河间太守’印一方,足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前秦已置有河间郡。因为’太守’之称只见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始二十六年后秦郡长官皆名之为’守’。”清河郡条下论曰:“存世秦封泥有’清河太守’者,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多次出现’清河’(或写作’请河’)郡,如 374、864、865号简,则秦始皇二十六年后秦置有清河郡无疑。” 按照其所论标准(姑且不论此标准是否符合史实):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称“太守”,之后称“守”。同样的“太守”印,“河间太守”印使河间置郡归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清河太守”印却违反前文所言标准,使清河置郡归入了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如此前后不一,论述矛盾,应误。
[48] 《史记》卷72《穰侯列传》,第2828页。
[49] 关于河间尚有一点疑惑,诸说均认为秦惠文王时河间地归秦,彼时距吕不韦受封河间地尚有数十年时间。这数十年内秦国对河间地的统治方式因史料匮乏已难以考究,河间或置郡或置封邑,故应当注意的是河间的置郡时间或许可以上溯至秦惠文王时期亦未可知。只是此文中心非河间郡,故未细作考察。
[50] 以下五条依据参见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4—27页。
[51]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3184页。
[52]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4—27页。
[53]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262—263页。
[54]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5页。
[55] 正如何慕《秦代政区研究》中所论述:“如果邯郸、钜鹿、恒山、河间、清河五郡并存,则赵国故地置郡有过密之嫌。前两郡有传世文献为依据,后三郡有出土文献为依据。仅由某个时间点上的置郡情况,贸然否定另一个时间点土某个郡的存在,太过武断。邯郸、钜鹿二郡在秦统一之后的建置情况,以存疑为妥。”
[5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6页。
[57] “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一句当出自《汉书》卷42《张周赵任申屠传》,而非《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原文为:“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而引用《汉书》卷1《高帝纪》原文应为:“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斩陈余,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
[58]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樊哙与陈豨作战时“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但此处仅可说汉初曾设置清河郡,未必承袭自秦。若据《西汉政区地理》,清河郡当为高帝九年赵国更王之时析钜鹿郡置。
[5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8页。
[60]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7页。
[61] 《汉书》卷51《贾邹枚路传》,第2367—2368页。
[62]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7页。
[63] 辛士影《论<史记><汉书>人物籍贯书法比较》(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7页)亦认为此为指县、乡。
[64]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6页。
[65] 参见辛士影:《论<史记><汉书>人物籍贯书法比较》第二章第二节《<汉书>人物籍贯分类》,第21—27页。
[66]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907页。
[67] 周群《秦代置郡考述》战国秦郡多采用《水经注》置郡时间,并对《水经注》所载多个秦郡的置郡时间作了列举。
[68] 周群《秦代置郡考述》即直接采用郦注,将钜鹿郡归入战国秦郡,但仍存疑。
[69]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99页。
[70]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904页。
[71]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也曾据此简考证指出:“信都县位于清河郡境内”。第60页。
[72] 辛德勇论断:“武城为清河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秦已攻取整个清河区域。所以,秦清河郡即应设置于此时。”当然信都并非清河区域,只是此年攻取主要为清河地区,而信都一带不足以置郡,故附之清河郡也。而宜安当属恒山地区,应归入秦恒山郡。详见氏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20—21页。
[73] 杨宽认为:“是年(秦始皇十四年)秦以桓齮为主将,经赵之上党,越太行山进攻赵之后方,攻赤丽、宜安,宜安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赤丽亦当在其附近。赵使长期与匈奴作战之名将李牧应战,交战于肥,肥即在今宜安东北,在今河北省晋县西”结果李牧击败桓齮,桓齮败走。然而笔者以为杨氏此说似有不妥,秦军为何选择崎岖难行的太行山井陉关进攻赵国,而不选择从邺城、平阳一带渡漳河北上?要知道井陉自古易守难攻赵军必会重点布防,而邺城渡漳河北上为华北平原,赵国无险可守(赵于两年前筑城柏人,应当即是出于防守需要),汉初韩信击赵走井陉路是自西而来,不得已行险,而秦国当时已占据漳河流域,且桓齮本就一直攻略漳河流域,为何会舍易求难,舍近求远,不北上走适宜行军的平原地区,而由平阳一带绕上党,经井陉而击赵?不甚合理。加之王翦一直在太行以西攻略,但王翦军也直到始皇十八年方才从上地过井陉攻赵(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300页)可见在此之前太行以西,赵国势力尚未清除,越井陉击赵时机尚未成熟,且若越太行攻宜安,当遣王翦军为是,不当遣桓齮。故笔者仍持桓齮当北攻之说。至于杨氏又言宜安未被秦攻下,时李牧大胜,桓齮败走,故应从之。此外,杨氏还认为始皇十三年秦攻取武城,且此“武城在邺之西,在今磁县西南”即此“武城”非清河重镇“东武城”,若依之说,则辛氏所论置清河之说便难以成立了,当然笔者以为目前尚不能断言此武城究竟是何地,毕竟赵国有三处武城。详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32—1133页。
[74] 图3及图4系笔者在前文图1的基础上结合秦简和《史记》记载改绘而成。图3中取东武城者为桓齮偏师,考虑到秦军两次渡河存在的风险和麻烦,故推测取武城(即东武城)者当为桓齮军北上时所分出之偏师所为。当然若所取武城非东武城,则图3攻取东武城路线便不存在了。至于两图中河间郡界改变是因项羽曾将环南皮之河间三县封陈余,故笔者认为南皮周围当属秦河间郡辖地。
[75] 《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第3222页。
[76] 《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531页。
[77] 考杨氏之说是以《李牧传》《赵世家》记载为是,“秦始皇本纪及六国表依据秦记,讳败为胜”,笔者以为诚如是言,然具体到武城具体位置,河北献县西南之武遂当如其论,非是。邺城西之武城,清河之东武城皆有可能为桓齮所拔武城,且桓齮军攻赵宜安未必越太行而过井陉道,可能渡漳水而北击。详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132—1133页。
[78] 《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第3129页。
[79] 《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第3130页。
[80] 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60页。
本文原载《秦汉研究》第十四辑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