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往南开的时候,窗外的山像一层层绿色绸布,被风轻轻推开。
我这个四川人本以为自己看山看多了,不会再被震住,
可贵州的山不一样,它们贴得更近,绿得更深,
有种“你只要抬头,它就能落在你肩上”的亲密感。
第一站是都匀。
一下车我就闻到了水汽——
那是一种混着青苔味的湿润。
都匀的风软软的,像经过河面被过滤过一样,
吹在脸上不会凉,会让人慢下来。
青云湖边的水波一点点推岸,
我坐在栏杆边喝着热豆奶,
看对面有人在慢跑,
脚步轻得像落在云上。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都匀这座城,是不急的。
它不拉扯你、不催促你,
像个温柔的人,只是递给你一把椅子,让你坐会儿。
我随便走进一条小巷,
本地人坐在门口削笋,
笋壳剥开的碎屑掉在地上,被风一吹,
滚得像小小的黄纸片。
一个婆婆抬头看我,问我吃不吃笋子干,
她说话不高,带着南方特有的软尾音,
听起来像是雨滴落在瓦片上的声音。
而就在我沉在这份“温柔”的时候,
凯里突然跳进了我的脑子——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第二天我到了凯里,
火车站外的风一下子就把我从都匀的温柔里抽了出来。
凯里的风是亮的、快的,
像是从鼓点里跑出来一样。
凯里的街道比都匀更“狠色彩”。
路边的布店门口挂着刺绣背带,
红得像要滴下来,
蓝得像深夜的星。
走进去,我被那种跳跃的配色晃得心口一亮——
这是典型的苗族审美,
没在怕的,越亮越好,越满越美。
我一边摸布料,一边回想都匀的色调,
那里是山水的绿灰色,
到了凯里,就是“把山水调成最大饱和度”的彩。
两个地方,连呼吸都像不同节奏。
街口我买了一碗酸汤粉,
汤一端上来,酸得我眼睛都亮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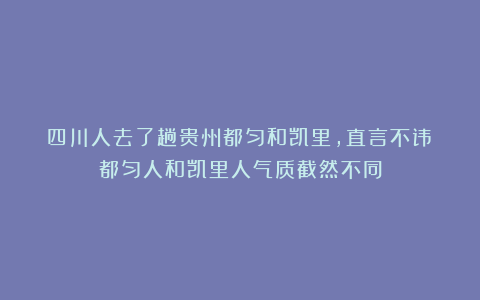
她笑了笑:“四川来的嘛,加点更爽。”
说完她手一抖,辣椒像雨一样撒下去。
酸、辣、热、冲,
味道一下子就把人点燃了。
我边吃边想起前一晚在都匀喝的清汤粉,
汤温温的、味道淡淡的,
像是轻轻贴着舌头说话。
凯里的酸汤粉可不是,它是直接拍你的肩膀:“吃嘛!”
那两碗粉,就把两座城市的人情味都说透了。
吃完粉我往苗侗风雨桥方向走,
桥上有小孩跑来跑去,
大人坐在木椅子上聊天,
风穿过木缝时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远处谁在吹芦笙。
一个奶奶拦住我,把手里的糯米饭塞给我尝,
饭团里还加了一点酸菜。
她笑着说:“我们凯里的味道就是要酸一点,人也这样,说话都直接点。”
我就站在桥上笑了:
都匀的婆婆说话像雨点,
凯里的奶奶说话像鼓点。
晚上我坐车回都匀方向,
车窗反射着我的脸,
我突然意识到——
在贵州这样山里穿行,
每到一个地方,气质都不是慢慢渗出来的,
而是“啪”地一下撞到你。
都匀让我心口往下沉,
沉进水雾、沉进绿意、沉进静得能听见风吹草的声音里。
凯里让我整个人往上跳,
跳进色彩、跳进味道、跳进苗寨那种热情的鼓点里。
两个地方只隔了一段山路,
但灵魂不一样——
一个像溪水绕城,一个像山火照夜;
一个轻轻托着你,一个直接拉着你往前走。
而我一个四川人夹在中间,
被温柔收了一次,被热烈推了一次,
两种力都不大,
可都刚好落在心上。
我后来跟朋友说:
“都匀和凯里,差别不是显著,是直接刻在空气里的。”
都匀的风告诉你“坐下吧”,
凯里的风告诉你“跟上来”。
而我两个都舍不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