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书院绝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且不说中学历史课本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必背知识点“中国古代四大书院”还有挂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门头照片,许多城市都已经将当地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书院作为旅游景点而重修开放。
但是,书院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是陌生的,因此当书院被称作“中国古代的大学”时,许多人感受到了一些不对却又无从说起。书院究竟是什么?书院是如何发展的?书院给历史和现实留下了什么?这篇文章希望的就是探讨以上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萌芽:唐代
对于书院是什么的问题,普遍的解释是这样的:“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是官学的补充。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在我国的教育史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这样的定位并不准确。书院的发展历经千年,其组织性质、组织职能、组织形式等都发生过极大的变化,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要搞清楚书院是什么,必须回到历史当中去。
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清代学者袁枚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书院之名起唐玄宗。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所也。”(《随园随笔》)书院之名大抵始于此,但就其性质而论,它仅仅是官府搜集遗逸图书,校理经籍撰写文章的场所,而非教育机构。这个观点可以从具体的历史记载(主要是《唐六典》和《集贤注记》两部文献)中得到印证,其创立历程大致如下:
1.乾元殿写书廊时期:开元五年至六年冬
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开元六年,“制令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东廊观书”。开元六年冬,“及还京师(长安),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
2.丽正书院时期:开元十年三月至开元十三年四月
开元十年三月,“车驾幸东都,始移书院于明福门外中书省之北,仍以丽正为名”,“院内屋并太平公主所造”。开元十一年,“归京师(长安),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造书院,依旧谓之丽正书院”。开元十二年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
3.集贤院时期:开元十三年四月以后
开元十三年四月,“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
(以上图文引证自王书林《唐洛阳宫集贤院址及布局考》,《中原文物》2023年第4期。)
章柳泉对袁枚的说法表示赞同,并补充说:“唐代也有一些私人读书处称书院,见于唐人诗篇,也不是授徒之所。作为讲学授徒培育人才的书院,始于南唐升元四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中国书院史话》)按照这种说法,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古代最早的书院是唐玄宗时建立的丽正书院;二、官家书院早于私家书院,其职责各不相同。
然而,有部分学者对这一观点持异议态度,认为私人性质的书院出现在官方的书院以前,并且其发挥“学校”职能也更早。他们根据《(雍正) 四川通志》的记载指出:“唐代的私人读书治学之所,也称书院。这些私人设置的书院有具体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建’,这要比官方的集贤书院早90年。”(《中国古代的书院》,《百科知识》1980年第11期)这一观点被很多历史书籍使用,甚至是被当地的文旅作为重要宣传点。但是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会发现,“贞观”实际上应该是“贞元”的误笔,张九宗在遂宁创立书院的实际时间距“贞观九年”至少要晚150年左右。(详细的考证和辨正过程可见胡昭曦《唐代张九宗书院建立时间探考》,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而且在唐朝,中国书院的发展尚处于肇兴阶段,当时的记录甚为简略稀少,而书院建置亦未形成制度,当时的张九宗书院和唐朝许多书院一样,主要是学者的一个读书之处,尚未具备完善的教育功能,又事隔千年以上,今日探识其原貌至为困难。从研究的角度,也不宜将它们与后世的民间书院等量齐观。在当时许多书院中具备讲学、授徒活动的书院,据志书记载仅有四所。即:“在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的皇寮书院,“在漳州府,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的松州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义门书院和“在奉新县,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而且都还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仅仅是私人书院的萌芽阶段。
此外,宋人洪迈的《容斋三笔》中也有可佐证袁枚观点的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这段记载不仅是对“白鹿洞学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讲学授徒培育人才的书院”这一观点的证明,也为我们梳理五代与两宋时期的书院发展历史提供了参考。
二、书院的发展与极盛:自五代而两宋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均处于混乱状态,人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教育。而到了960年北宋统一天下时,当时北宋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到了巩固中央政权上,也无暇顾及文化教育。据记载:宋初八十三年间(公元960年至公元1043年庆历兴学)官学未有发展,学校状况与唐末五代相差不多,就中央官学而言,当时只有一个国子监,而地方则是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才在永康军设立乡学,成为州郡设置官学的开始,直到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其他各郡才允许设立学校。书院就兴起于这样一个乱世渐平,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的局面中,其兴起既符合读书人求学要求,又为国家解决了社会问题。
北宋为书院的兴起阶段。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等史书记载,宋初著名的书院有六所:即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这些书院多为名士、士大夫或地方官私人创办,并择名胜、山林幽静之处,建舍生簿、广招贤纳士、授业讲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与官学有所区别。书院在北宋初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兴盛时期。朱熹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 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 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麓洞之类是也。”(《衡州石鼓院记》)吕祖谦也强调:“窃尝闻之诸公长者,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白鹿洞书院记》)
但随着北宋建立比较完善的分层级的官学教育体系,开始在地方教育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书院的地位又逐渐被取代,而各书院的院产、学田要么失落,要么被侵占,民间书院在短暂的兴盛之后开始走向没落。北宋书院的衰落之势,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亦有论述:“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变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整个北宋一朝,书院教育始终不是特别发达。
南宋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各地方书院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体制之健全、组织之严密,都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据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统计,南宋时期全国共有书院 711 所,北宋遗留下来的有年代可考的约150所,其余多为南宋新建(江堤《书院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重视读书,崇尚讲学之风支配和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关。而且南宋的书院,比起北宋的书院,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具体而言,南宋书院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一是数量剧增,规模日益壮大;二是学院教育经费较为充足,各项设施较为齐全;三是学院办学不断正规化、体系更加完备;四是学院功能更加丰富、充实。
南宋书院的兴盛,有其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北宋以来,官学的发展一直是全社会教育的重点,官办学堂的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植。但是三次兴学的失败,使官办学校名存实亡。尽管南宋时期官学在形式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势头,各级地方官学的数量和规模也相对可观,而且国家还拨出了大量的经费和学田用于各级官学的日常运营。但官学的教学内容完全是科举利禄之学,学术风气极其浅薄,往往流于形式,殊无教学之实,基本上沦为了科举附庸。士子入学,“非图缀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无补与时”([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学校考》)。而这种完全以科举为导向的官学与当时理学兴起背景下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兴趣是不相匹配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士子渐感厌倦,甚至耻于进入官学学习,转而开始仰慕那些知识渊博且气节高尚的名师大儒。而书院所宣讲的“道学”恰好满足了学子们的这一需要。《宋元学案》载:“文靖(杨时)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所谓“道”,即道学,也就是理学。很多理学大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热心书院教育,积极创办书院,开展讲学活动。如朱熹在地方任职期间,就先后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撰写了石鼓书院重修的碑记。其他热心推动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还有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而对于当时社会上浮躁功利的学风,朱熹这样警戒学生:“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彼青紫之劳势,亦何心于俯拾!”(《白鹿洞赋》)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态度也吸引了许多一心探究理学义理的学子加入书院,向大师们请教学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宋书院的复兴,可以说是官民合办,而民间力量又较官方力量为多。
南宋孝宗光宗时,民间书院初兴。乾道元年(1165),刘珙知潭州,决定重修岳麓书院于废墟之上。不到半年,书院落成,刘便请平民理学家彪居正为山长,又请在家丁忧的理学家张栻授课,招收二十名学生,以示纪念。淳熙十五年(1188年),信奉理学的安抚使潘畴扩建书院,使学生数量增至三十人。绍熙五年(1194)五月,朱熹知潭州。他到岳麓书院视察,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并自选门生黎贵臣赴岳麓书院讲学,以扩大理学的影响。在此之前,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初至淳熙八年(1181)三月担任权发遣南康军事。他一到任,立即下命令对白鹿洞书院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进行重修,于次年三月竣工。他亲自担任书院“洞主”一职,对于书院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书院的教育方针、学生的行为规范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开后世书院学规之先河;他亲自为书院遴选教职人员并且亲自写聘书以示恳切;书院首次开课,朱熹亲自登台并主讲四书之一的《中庸》;白鹿洞离郡治有十余里路,每十日官吏的例假,他都到书院用整个的休息日来指导学生的学业。朱熹可以说为南宋书院的发展费尽心血,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历史上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事实上,哪怕到了这个时候,民间书院的生存与发展也并不能称得上很好。此时,复办的岳麓书院,学生人数已远远少于北宋。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废其旧十七八”,其建筑规模恐怕连北宋的1/3都不到。北宋初年,书院有近百名学生,此时仅一二十人。北宋初,这所书院有学生近百人,而这时只有一二十人。朱熹在重修书院时,还特意向朝廷汇报,这一次重建的土木工程很小,“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希望减少重建书院的阻力。但无论如何,南宋的书院教育在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理学家顶住压力,利用书院这一平台进行学术宣讲学习研究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走向复苏。这一时期的书院教育也是最符合大众认知中的“书院教育”的,最具历史特色的。朱熹等人重修的书院虽属官办,但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他们对书院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使得书院的教学、用人等制度逐渐成熟,受到朝廷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图为今白鹿洞书院中朱熹像)
两宋期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院,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大书院”(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各不相同,四大书院有六个很合理吧):王应麟的《玉海》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和嵩阳为四大书院,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和岳麓为四大书院。此外,茅山书院也是当时著名书院之一,现在对于六大书院进行简要的介绍: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 785—805 年),洛阳人李渤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 825—875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名为白鹿洞。唐南升元中(公元 937—943 年),置田建立学馆,命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教授学生。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 年),知江州周述陈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南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 1179 年),朱熹为南康军太守,申请修缮修,订立教规,从此白鹿洞书院闻名于世。
石鼓书院,因设在衡州石鼓山(今湖南衡阳市场石鼓山)而得名。原为唐刺史齐映建合江亭于山之右。唐宪宗元和(公元 810 年左右)时,州人李宽建造房屋并在此读书,刺史吕温曾来拜访。宋至道三年(公元 997 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在李宽读书处创建书院。宋景祐二年(公元 1035 年),仁宗根据集贤校理刘沅的请求,才赐书院匾额和学田。
岳麓书院在湖南潭州(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初创者是彭城人刘鳌。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五间,书斋五十二间。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潭州太守李允又加以扩充,学生达六十余人。大中祥符五年(公元 1012 年),山长周式被任为国子学主簿,归任书院教授,并赐书院匾额。
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县,原为宋代名儒戚同文旧居。商丘宋代称为南京,为当时应天府治,所以取名。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当地人曹诚在戚同文旧居,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并以自己修建的学舍捐给政府。政府令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为主教,曹诚为助教。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也记载了应天府书院的创立经过和书院盛况。他写道:“真宗皇帝由之嘉叹,面可其奏”,并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嵩阳书院,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该地点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时称嵩阳寺,隋朝大业年间(605年)更名为嵩阳观,五代周时(公元951-960年),改为太乙书院。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司马光、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且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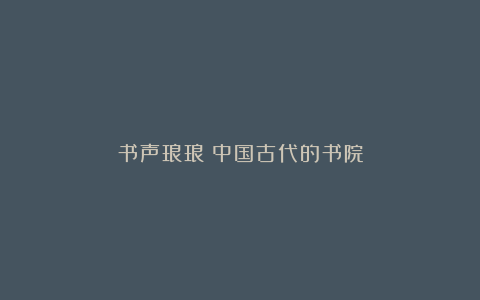
茅山书院,又名金山书院,由处士侯遗创建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地点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院址在江宁府三茅山后侧,故称茅山书院。侯氏在此教授生徒十余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经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赐给田亩,充书院经费。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迁至金坛县顾龙山之麓,现已无存。
而这一时期的书院教育有许多突出的特色,也正是这些特色让书院享有了“中国古代的大学”的美誉。
其一是书院制度的臻于成熟,其重要标志是首次为书院确立总体教育方针的朱熹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不仅是南宋理宗朝以后的钦定书院学规,而且是后世书院学规的共同范本,是历代书院学规的通例。此学规吸取了佛教丛林清规的有益成分,同时也融会了在理学评价体系下有利于培养优秀儒生的学识和性情的实践经验。除此之外,书院的组织管理趋于健全,并在管理人员编制、招收学生等方面加大了管理力度。整个书院的运作已经走向机制化、正规化的轨道。
(《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内容: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其二是讲学、祭祀、藏书三大职能长足发展,书院择师讲学,传授不同门派的学说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讲学形式趋于多样化将教师讲学和学生自学相结合; 书院在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同时,重视祭祀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朱熹等北宋以来理学家,并将祭祀仪式改为春秋祭的模式。尤为突出的是当时书院中自由的学术风气:
1、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实行“门户开放”,允许不同学派之间相互交流与争辩,在诸家学问中兼得其长。“讲会”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种重要教学活动方式,也是书院的一个重要标志。讲会始于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陆九渊两位理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在鹅湖寺公开辩论,即著名的“鹅湖之会”。虽朱陆学术观点不同,但朱熹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将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中,为不同学派在同一所书院讲学的“讲会”起到了示范作用。逐渐,各个书院的主讲在讲学时都标上“话头”(即讲学主题),欢迎他人质疑、发问、辩论,目的在于相互探讨,发挥某一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窗各派主张的异同之处。讲会最初只是书院内的一种授课方式,后来就超出了书院的范畴,成为一种在社会融为一体的学术活动:名士讲学,别院及外地书院师生慕名千里而来听讲,书院热情欢迎,给予周到安排。听讲人的身份并不局限于书院的师生,许多社会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可以参与或旁听,这种“讲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区域性的学术集会,书院也成为一个地区的学术活动中心。书院依靠讲学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风气,提高了教学水平,形成了兼收并蓄、学以致用的教学风格;同时,书院教学敢于面向大众、面向百姓,是对封建社会教育阶级性、等级性的挑战。书院学术传播到民间,不仅普及了地方文化和学术,还使许多贫苦子弟受到教育,也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
2、学术传授方法以学生自学和自省为主,采用难问辩式的方法,注重启发和诱导学生的思维。书院教学主要以个人阅读研究为主,因此非常重视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很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学会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了很多读书的道理,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和阅读效果。如朱熹提出了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等六大读书原则,对学生自学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同时,南宋书院主要讲授理学,在书院传习理学的过程中,有一种修心养性的方法是静坐,向内观察。理学家认为这是上通天理或致良知的不二法门,是读书人的头等功夫,是做圣人的不二法门。如以发明本心为主的著名理学家陆九渊认为,人性本善,为我所固有,所以教人“存心”、“求放心”——要存心,要安心,必然要下反求诸己的功夫。而在阅读上,书院教育中强调学生对于典籍的自我理解和建构,老师会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因此书院强调学生阅读要善于提出疑难问题,鼓励学生辩论,教学中采取的是问难的辩论式。如朱熹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尤为重视。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吕祖谦对读书也很重视,他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读书贵在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独辟蹊径。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同时,书院中有许多讲学活动,但大师讲学多是提纲挈领,由学生自己去体会,由浅入深。如淳熙八年,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稽山书院的一次大会,王守仁只阐发了《大学》中“万物同体”的旨意,皆以启发、诱导为主,而非逐字逐句的全部阐发。书院通过教会学生自学,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不惧权威,敢于质疑,并给予必要的启发和辅导,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极大的调动,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
3、学院师生关系融洽,情深意长,彼此砥砺。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种优良的传统,即学生尊师重教,教师爱生如子,这一传统也充分体现在学院的教学中。毛泽东指出:“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瑕豫,玩索有得。”(《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南宋州县学腐败,学校只管课试,发膏火,并不进行教育,而书院自由择师,倾慕在先,道义为重,师生以诚相待,往往一日为师终身不忘。南宋大师都受生徒尊敬,不仅在书院行礼恭敬,离开书院后,有所成就仍对大师行弟子礼。弟子尊师重道,不仅表现在学术上对学说旨义的继承,更体现在平时的生活中。教师爱生虽然也有做人的一面,但主要是关心徒弟的德行和学养的进步。大师们愿倾其所知以授徒。据《朱子年谱》载,朱熹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其三是书院建筑结构趋于规制,形成包括礼殿、祠堂、讲堂、斋舍、书楼等功能齐全的教学设施,具体的建筑形制可参考下图:
(图源吴晶晶,王建群《庐陵地区书院建筑的空间形态研究》,重庆建筑年2024第11期)
其四是书院经费来源相对稳定,以学田田租为主,地方拨款为辅,个别书院以抵质库(即明以后的当铺)的利息收入作为经费来源,经费主要用于供给书院管理人员与生徒之所需以及书院的祭祀费用等。
但随着书院的极度兴盛,官府必然要介入这个独特的教育平台,书院也随着官学化而逐渐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与没落。
三、书院的官学化与僵化:自南宋后期而清
孝宗、光宗时期,书院是朱熹等理学家对抗朝廷正统教育、宣传自己学说的阵地。但到了南宋后期,理学已经转变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为国子监、太学、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特别是到理宗朝(1224-1264年)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书院教育也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家的遗产,由官府承袭。理宗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亲自为多所书院题写院名。书院教育的发展,成为地方官博取名誉地位的重要手段。官办书院很快就遍及全国。各州普遍设有官办书院一所,有的州设立了二、三所。不少县也办起了书院。很多官员和学者还办了私立书院。于是朝廷将书院纳入全国官办学堂体系。从景定元年(1260年)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一职务的,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或正式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景定三年(1262年)或四年(1263年),朝廷把担任书院山长的条件提高到与州学教授相同。“山长应注有出身,应格合入教官,及经任合注教官人”(详见王应麟《玉海》、《宋史》)。由于朝廷派山长到各州,州级书院成为官办地方教育的法定组成部分。既然山长和教授的人选完全一样,书院和州学的教育就不会相差太多。以岳麓书院为例,理宗年间,潭州在岳麓书院南面建立了岳麓精舍。潭州州学学生每月参加测试,以成绩累积学分,积分达到“高等”即可升入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是通过每月的小考积分,达到“高等”即升入岳麓精舍,当地人称其为“三学生”。潭州州学、岳麓书院、岳麓精舍构成一个提升体系,可见书院与州学在教育上的一致性。南宋后期,私立书院虽然也有显著发展,但已无法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相抗衡。官办书院已经成为书院教育的主流,而民办书院只是官办教育的附庸。事实上,此时的私立书院几乎无一例外地向官办学校靠拢。永丰县士人黄惟直开办的龙山书院,从成绩考核到伙食供应,完全仿照州县学,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为目标,平时由黄惟直主讲,考试则请县官或已通过科举的人主持,仿照官学,唯恐不及。此时,书院官学化的倾向已渐不可阻挡。
并且由于元朝的汉化政策,书院的官学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元代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联合北方各少数民族共同创建的封建大帝国。为实现长治久安,统治阶级推行汉化政策,明令保护书院、宗庙等文化机构,鼓励书院教育,提倡创办多种方式的书院。朝廷出资兴办了官府书院,解决了书院学生的就业问题。《续文献通考》记载:“自京学、州县学及书院,凡生徒之业于是者,遵旨举荐,台宪考核,或用为教官,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自此,从唐末开始,书院由民间创办和经营的传统被打破。元代书院官学化演绎。朝廷在兴办官学书院的同时,对民间私塾进行资助,为元代书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措施。据曹松叶《元代书院概况》统计,元时新建书院143所,恢复原有书院65所,改建19所,共计227所。丁益吾先生的《历代书院名录》中,标明元代所建的书院有296所。考虑到宋代已有书院600余所,至元代多有保存和修复,元代书院近千所的说法并不奇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于元太宗七年(1235年)的北京太极书院,设有专款、田产、编制,各级官员兼任或有官府出面选聘山长,并设置专门管理官员的钱粮。对民间私塾,由官府给予经费、田产补助,加强经济监管;山长须经政府认可,授予官阶才能任职,官府实际上加强了对民间书院的监控。继太极学院之后,各地的书院也不断涌现。据《续文献通考》载:有昌平谏议书院、河间毛公书院、京兆鲁斋书院、开州崇义书院、苏州甫里书院、宣府景贤书院、凤翔岐山书院、常州龟石书院、济南闵子书院、曲阜洙泗书院、琼州东坡书院等四十所。元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学活动多沿用南宋书院制度,但朝廷通过修建官学书院、资助私学书院、配置官员管理等具有鲜明的官学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学者们自由讨论、学术独立的文化人格的发展,书院教育在官府的监控下逐渐失去了灵魂。
明初,不仅书院数量骤减,而且由于文字狱盛行,当时许多书院如崇安梓翁书院、龙溪芗江书院等,仅以祭祀先贤、名儒或自家祖师为活动内容。其余如江苏丹阳濂溪书院,江西鄱阳白云书院等。…无不如此。也就是有的书院搞一些文化活动,也是以个人的藏学作为一个内容。如江西新喻石门书院,为洪武初乡人梁寅所建。“结庐石门山,聚书遗子孙,名曰书庄。”(光绪《江西通志》卷81)至于吉水竹庄书院,是邑人陈秉献、陈秉哲读书的地方。更多的书院成为士大夫或缙绅的私塾。如福建龙溪书院,是洪武时乡人苏廷龙的“延邑中宿儒教子弟于此”。(嘉靖《龙溪县志》卷六)江西星子龙潭书院为邑人查琛教其家子弟之处,万载绿阳书院为邑人郭正彦于永乐年间(雍正二年《江西通志》卷二十一、二十二)所建私塾,用以“课其子弟”。书院成为私塾,主要是受科举熏陶。有明一代,当时构成教育制度的主要是学校和科举。“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东林列传·高攀龙传》)故《明史·选举志》云:“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不可不由科举”,“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可见,在以官本位为本的社会里,士子们的出路除了科举这一条别无他途。综上,在文字狱的打击下,书院不可能在科举、官学的挤压下发展起来。
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松动,科举制度的日益衰弱,心学思潮兴起,王守仁、湛若水等思想家曾开办民间性质较强的书院,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对抗朝廷的正统学说,批判朝廷的弊政,书院教育又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不少书院一度得到重修和兴盛。但最终的结果是,明代官府一方面出资不断重建书院并加强对其的控制,另一方面却一再打击学术风气相对自由的民间书院。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御史上疏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疏中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续文献通考》卷五十)明世宗虽慰留若水,令有司毁其书院。次年五月,吏部尚书许赞对上一年度毁书院仅限于湛若水所建书院,而未能完全达到禁止“邪学”的目的深感不满,遂上疏要求将禁绝范围扩大至所有书院,并疏称: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请。”(《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并在书中一再强调,上一年度拆除书院,深得人心拥护。虽然这两次拆除书院的活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声浪,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两次书院被毁,这是一个信号;之后,书院为了存在,不得不顺应现实的生存环境,其教学内容开始逐渐“变质”,这已经违背了书院创办的初衷。明代中叶书院的一个变化是其教学内容已向科举靠拢,后来书院甚至基本取代官学成为主要教育阵地。到了明代后期,书院更是因为两次卷入政治斗争(张居正变法、东林党案),甚至被官府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元气大伤,风光不再。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于贵州修文县任驿丞时建龙岗书院)
进入清代,书院的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性质上多为官办书院,各级官府、官吏或以公银创建,或以私产创建,已丧失了书院应有的自由学术精神。据曹松叶统计:清代书院 1800 所,官办 1381 所,民办 182 所。清代统治阶级在鼓励书院发展的同时,又加大了对其的控制力度,采取“各省省会先设一所书院,书院经费由政府拨付;”书院山长由各省督学大臣聘请;书院学生由各省道员、布政司共同考核,私创书院需申报“官厅查核”(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等一系列举措。至此,清代书院彻底官学化,一同沦为科举附庸,科举考试成为书院办学宗旨,以八股文为主要传授内容。虽然也涌现出一批传习理学、经史学独树一帜的书院。如著名教育家黄宗羲的甬上证人书院,讲求穷经、读史、经世,主张独立思考、自由发挥,不唯司讲者,不专主一家之说;清初启蒙思想家颜元的漳南书院,推行重习行、不尚空谈的教育理念;清代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阮元及诂经精舍、学海堂,推崇汉儒博学经史的学术宗旨。在官学腐败、学风衰落的清代教育体制下,这些书院不能不称其为特色,但终究影响微弱,未能形成学术风气。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西方教育的冲击,加上旧有的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书院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的学堂。如前所述,清代书院官学化现象严重,书院腐败现象日渐显露。一是山长不再热衷于教书,转而追求时名,不学无术者居多,徒有虚名;二是书院里的弟子,大多以名利为唯一追求,迷恋科举,在八股中消磨青春;其三,晚清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深知欲富国强兵,必晓西学以求救国之道。而且当时的书院教学内容,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国学、理学,都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书院不出意外地成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众矢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提出:“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者,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其民间亦有公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有师生,皆有经费。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坐受修脯者……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私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州府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1998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院史资料·陈谷嘉》)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建议,七日后发出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此拉开了书院改制之序幕。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各地掀起了一股重修学堂的热潮。到光绪二十八年,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达到书院改学堂的要求。
四、中国古代书院在今天的回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五代、宋朝和元朝,第二阶段是明朝和清朝。每个阶段都是一个书院从独立于官办学校系统之外到被纳入正统教育体系之中的发展过程。但第二阶段的结束不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而是传统书院教育的灭亡。然而,古代书院制度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历史影响力的消失,当我们看到现在在许多名校中又重新恢复的“书院”式的人才培养制度,当我们看到那些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书院的遗址到如今仍然在当地的文旅事业与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在研究书院制度与它的现实应用时,我们就绝不能说它的影响消亡了,而是能真正感受到它融化在目前的文教事业当中了。是的,书院或许没有那么“现代化”,它也的确在很多层面上与目前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大学”在很多地方是迥异的。但是,只要我们还需要思考,只要我们还需要探讨,只要我们还需要将文化事业往前推进,那么,这象征的中国文教史上自由学术空气的书院,就会一直回响在每一册史书中,滋养着我们的文化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