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的第二个答案,是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这里施展将中国内部划分为海洋亚区域、大陆亚区域和中介地带,并对大陆、海洋区域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与世界秩序对比,得到该答案。
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
中国作为海洋陆地的地理枢纽的原因在之前已经提过,而在中国内部,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合题。在这里,我们从地理、人口等角度出发,展开对秩序的认识,并将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进行一个对比,当然在这一部分,我也会掺杂许多自己的理解。
(对秩序的展开难以绕开经济的影响,而关于经济会单独出一篇内容,这里我会略过经济直接进行分享)
一、秩序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秩序先进行一个了解。在这本书中,施展给了秩序的多种解读,我们也需要先明白一些关于秩序的概念。
秩序是按一定标准进行排序,并指向稳定的结构。施展给出了几种关于秩序的表达,让我们先去了解这些词语的概念。
1.摩尼教秩序与奥古斯丁秩序
(1)摩尼教秩序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波斯先知摩尼创立的二元论宗教,其教义融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等元素,形成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其内关于宗教的元素我们不必过多了解,只需知道其世界观是一种终极二元对立的体系,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进行着永恒的斗争。
而摩尼教秩序便是施展基于该宗教给出的一种秩序理解,具体内容是指一种善恶二元对立的秩序,且这二者都是实体性的存在,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以消灭对方为目的。
这一秩序在近代被施展用于描述冷战时期苏美的二元对立格局。在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就宛如摩尼教中的善恶二元对立一般,具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双方的普遍精神在互相倾轧,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也都在冲突中各自发展。
(2)奥古斯丁秩序
奥古斯丁是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秩序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秩序,而是一种一元的秩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并非两个实体,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实体,相应的,恶只是缺乏善的体现。所以与其说是“恶”,不如说是没有“善”。
简单来说,奥古斯丁秩序是一种一元秩序,进一步的理解,这是一种以秩序(善)对抗无序(缺乏善)的状态。
这一秩序在近现代被施展用于描述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格局。在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变成一超多强,苏联势力范围内留下了大量的秩序真空,大陆也因此进入到一种失序状态,海洋秩序成为普遍秩序并逐步向大陆扩展,因此这是一种以秩序对抗无序的状态。
2.多神秩序与多神世界
多神秩序和多神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理解,这里主要指一种多元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去主导秩序,而是多种秩序并存,或对抗,或相融,或相依。
这一秩序也被施展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格局上。当苏联解体后,世界秩序从二元对立的摩尼教秩序进入了一种一元的奥古斯丁秩序,而在奥古斯丁秩序统辖不到的领域,可称之为失序,也可称之为一种多神秩序,其内多种宗教信仰、精神力量在互相交流、碰撞。这就是大陆世界的现状。
3.普遍秩序(全球秩序)与区域秩序
全球秩序和区域秩序在上一篇内容中有讲过,这里就不做具体的解释。
4.哈耶克秩序与黑格尔秩序
根据秩序的生成逻辑,可以将秩序分为哈耶克秩序与黑格尔秩序。
(1)哈耶克秩序
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但它们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哈耶克秩序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生秩序。在秩序的生成逻辑上,他并不是人主观刻意的产物,即不是人的权力表达,而是自发形成的,正如经济学领域那张看不见的大手——市场那样,自发地进行调控。这种秩序自己有其发展方向,它是无数个体行动的非意图结果,其复杂性远超人为设计能力。
在这个方面,施展更多地用哈耶克秩序来去表达秩序的一种演进路线,他想说明的是,秩序并非完全由人力主导,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自己演进的方向的。
(2)黑格尔秩序
同样的,黑格尔秩序是与哈耶克秩序对应的另一种秩序样态。哈耶克秩序是一种自生秩序,而黑格尔则是一种建构秩序。这种建构秩序并非是超脱人的主观意识进行自主演进的,而是依据自我意识,由人主动建构的。
在这个方面,施展也指出秩序的演进方向,除了自生秩序,也存在着依循自我意识进行演进的建构秩序。
捋清这些秩序的表述,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秩序和中国的秩序。从秩序的一元、多元角度展开为摩尼教秩序、奥古斯丁秩序以及多神秩序,从秩序的统辖范围展开为全球秩序和区域秩序,从秩序的演进生成角度展开为哈耶克秩序以及黑格尔秩序。
二、世界的秩序
秩序理解完毕,我们现在透过这些视角,去看看世界秩序是怎样的。
1.海陆的秩序
在上一篇推送中,我们从海洋、陆地的角度进行切入分析,并且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海洋秩序作为全球秩序对世界进行着深刻地改造,同时陆地国家是一种区域秩序。
而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也从摩尼教秩序进入奥古斯丁秩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多神秩序也嵌入了奥古斯丁秩序中失序的那部分当中。宏观视角审视世界,我们又会发现世界秩序的演进既有着哈耶克秩序的生成,也有着黑格尔秩序的生成。
这里我们讲一讲哈耶克秩序以及黑格尔秩序在世界秩序中的体现。
世界秩序在精神范畴内,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内容,是平等、自由、人权这些价值,基于这些价值,一种全球性的精神秩序被逐步构建起来,及至一系列的政治秩序、其他秩序都受此影响。具体的体现,如在法律秩序中,很多国家都会体现平等、人权等价值;在现代生活中,个人观念对于自由的探索和对平等的追寻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发达地区。而这种秩序的生成线去细细思索一下,会发现它现在已经很难人为控制了,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价值传导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
我国的儒家精神相比于人权、平等、自由等价值是不具备普遍性的,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具备该普遍性,这种自生秩序的蔓延和影响已经渗透进各个国家并实施影响了,而这种影响也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进展中体现的更加深刻且剧烈。这是哈耶克秩序不可阻挡的一面。
但同样的,诸如儒家精神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依然存在,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传承或扬弃,这又是黑格尔秩序的体现。根据国家的主权意识又自主地进行着秩序的建构。这是黑格尔秩序在哈耶克秩序背景下的体现。
海洋和陆地则是对上述秩序进行了很好地区分和诠释,笼统地来看,即:
海洋国家象征着全球秩序、哈耶克秩序、奥古斯丁秩序(有序部分);
陆地国家象征着区域秩序、黑格尔秩序、奥古斯丁秩序(无序部分、多神秩序部分)。
当然,上述分类并不完全正确,诸如海洋国家难以完全代表哈耶克秩序的生成,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西方海洋世界以人权、自由等价值作为哈耶克秩序的传导基础,但其政治、经济等领域上的实践操作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这一点,正如之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批判,其人权、自由等价值背后潜藏的,是反人权、反自由的国家、民族利益。所以这里的哈耶克秩序更多的应该是代表的精神内容的传导。
2.人口的失序
通过地理结构,我们大致划分出了不同的秩序,现在我们进一步聚焦在人口上面,聊一聊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人口结构及流动也是秩序考量的必要因素。纵观历史,我们也会发现,秩序的崩溃和流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里以国家(非海洋国家)进行切入,分析人口特点。
(1)部分国家的秩序建立
这里我们主要可以看看俄罗斯、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
俄罗斯凭其对苏联的遗产继承,以及其内部的统一,构建出了一个大范围的区域秩序。
中国也凭借其过去历史和当今实力,构建出了一个区域秩序。
东南亚各国毗邻中国,正如中东部分各国毗邻俄罗斯,作为邻近稳定秩序的国家,它们呈现出来的秩序面相也会相对稳定。
简单来说,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秩序的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边,站在具有稳定秩序的陆权大国角度去看,它们也不会允许身边有着过多不和谐的扰动因素,毕竟这算得上是一种风险。另一方面,作为这些稳定秩序相邻的国家,它们也能承载稳定秩序国家富余的经济、人口的流动,也会受其较稳定的精神内核的影响。
这种区域秩序或因邻近一些陆地大国而形成,或通过一些海洋帝国留下的殖民财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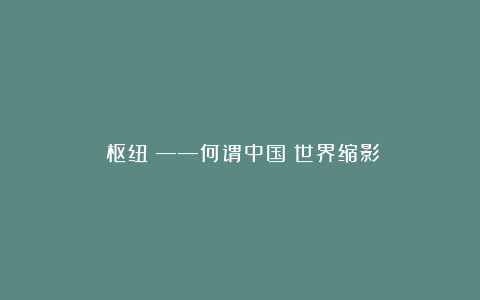
(2)第三世界秩序的崩溃
让我们将视角投入第三世界,我们会发现其上存在许多秩序的崩溃,在这里我们不把中国及东南亚纳入。
“三个世界”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种表达。从当代去看,这种说法已经不是那么的适用。但在这里,我们用其指称部分亚非拉国家即可。
第三世界秩序的崩溃,是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思考。
从社会演进来看,早期秩序的建立并不以经济作为决定性因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世外桃源,纯粹的用一种等级秩序的精神去做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即便生产力不足、经济疲软,也可以存在着稳定的分工和社会秩序。
但在与外部的交流下,经济对稳定秩序的决定性作用在不断地扩大。因为经济力量能具现化为军事力量,进而确保拥有足够的实力免受外界影响和干预,保持自身内部秩序的稳定,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在自身稳定的同时,又能更大地影响其他小国。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何时代发展至今,经济的力量反而更强大了呢?
回到当今,全球化的进程让“区域的”变为“世界的”。作为国家主体,维系其内部秩序的稳定上,经济力量的决定性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也是温铁军所讲的地缘战略向币缘战略的转变。
中国根据其超大规模性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迎来了自己的强劲发展,这里面的内在关窍和经济的作用力我会在 “何谓中国?经济枢纽”中进一步展开。这里先上结论,第三世界难以在全球化的经济互动中得到自己的发展。
简单来说,全球化的思潮带来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发展转向,但因为经济方面的限制,又让它们难以成功地完成这种城市化转向,其内的人民则卡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
第三世界的社会结构因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的失败而受到冲击,秩序崩溃带来的是第三世界流民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显现为毒品经济、黑帮经济等,在此基础上还叠加着各种“文明的冲突”导致的宗教性动员效应,终导致出一系列的动荡。
这部分的讲解逻辑链条并未完整地展开,大家先且看着。
3.不可能三角
这里施展还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是“不可能三角”的逻辑,这个逻辑也深深地嵌在秩序演进过程中,我认为很有必要跟大家进行分享。
“不可能三角”一开始是一种货币理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到,经济层面的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
蒙代尔模型是由蒙代尔提出的,其核心即是“三元悖论”,也即“不可能三角”,对应的是经济层面的三个目标,分别是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且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在这里,我且不对该“不可能三角”进行一个内部的逻辑分析,我会直接分析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
罗德里克进一步将这种经济领域的“不可能三角”扩展至政治领域,三个目标分别是超级全球化、民主制度以及国家主权。但这种名词其实并不好理解它们内部的逻辑关系,而施展在同张笑宇博士讨论后,对这三个目标作了另一种表达,在我开来这个反而是更好理解的。
三个目标分别是:资本自由流动、主权国家能力、阶级矛盾。我们最多在三者中取其二,下面我会分享自己的逻辑思考。
资本自由流动会抑制主权国家能力,这里的主权国家能力是一种对内的稳定,而这种主权也必然要包含对该国家内部经济的绝对把握,这种绝对把握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相悖的;同时,资本自由流动是会导致阶级矛盾的,资本是会集聚的,自发地汇聚到能充分发挥资本价值的人手上,随后进一步增殖,而这当然会因分配问题导致阶级矛盾的爆发。
主权国家能力会抑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上段已有讲述,对国家内部的绝对把握必然会限制资本流动的自由性;同样,主权国家对内的绝对把握,这种秩序一般指向等级秩序或是一定程度的集权,这种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也将推动阶级矛盾的爆发。
阶级矛盾的解决会抑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要解决阶级矛盾就要在生产分配上尽可能公平,资本的自由流动是难以带来所谓的公平的;同样,阶级矛盾的解决也会抑制主权国家的能力,解决阶级矛盾将指向阶级平等,这种阶级平等是更容易导致政治从秩序走向失序的,充分的平等和多元就意味着没有统一的声音和强权,主权国家能力其内的秩序应是一元秩序而非多元秩序。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应该明白,这三者的关系是其中任意一者都在抑制其他二者的,那么,三者都想达到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彼此极度互斥的目标是难以相容的,只能说牺牲掉一者,从而最大程度追求其他两者。
这就是政治领域上的“不可能三角”,以这种视角去看待世界诸国,也非常的有意思。
三、中国的秩序
世界的秩序以及一些秩序概念的理解已经梳理了,那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看看我国国内的秩序是怎样的。
1.中国的秩序结构
中国的内部秩序被施展分为三个地区,分别是海洋——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大陆——内陆边疆地区;中介地带——庞大的中原地带。这种秩序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也于中国内部提供了这种复杂性的秩序管理的视角可能。
2.中国的海洋秩序
这里我们只讲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海洋秩序,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以后再谈。
(1)东南沿海
首先,东南沿海继承了历史的遗产。何谓历史遗产?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宋朝的靖康之耻带来的两次人口大量南迁,对长江流域进行了很好的开发,让其在宋朝就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其次,东南沿海也是近现代海洋秩序的传播线。近代海洋秩序由欧洲建立并通过联通的公海进行传播。西方的陆地军队第一受限于规模,第二受限于地形,想要以军事的方式通过中东、西域抵达东方进而在经济、文化领域影响我国,是十分困难的。相反,在古代反而是我国的茶叶、丝绸曾一度影响西方经济。正是因为陆地传播的局限,所以近现代以来西方是以海洋贸易的方式进行着海洋秩序的建构。自然而然,东南沿海承接了这份影响。
中国东南部绵长的海岸线以及一定数量的港口,再加上人口发展和近现代的政府施策等等因素,成为近现代西方制造业外包大潮的弄潮儿。
时至今日做一个总结,会发现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深深嵌入了世界市场,又因经济脉动牵连着文化脉动,所以其文化视野也被西方极力拓宽。
(2)南洋地区
南洋地区主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产业结构和制度特点是值得一说的。如果在现代发展的视角去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和江浙沪地区的发展,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本书在第八章中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分享,而产业结构及其他具体策略聊的相对较少,我也会在这里做一点点小小的补充。
南洋地区尤其是港澳地区,其制度性差异更多的体现在法律层面。港澳那边奉行的海洋法系,国内是大陆法系,海洋法系相比于大陆法系,权力限制相对较小,资本的流动性更强,市场的自由度也更高。在金融市场的体现,就是海洋法系地区的直接融资机制,即债市和股市的规模,远远大于大陆法系地区。同时因为海洋秩序的一个核心体现,也是在于法律的适用是偏向普通法的(除了适用一些国际公约的情况),因为海洋法系的动态适应性相比于大陆法系刚性法律的滞后性,也更好地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法律对金融投资的影响,也形成了其与东南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这其中也有着土地的限制,同时伴随着制度本身的一些劣势。
第一,粤港澳地区相比于江浙沪地区,土地面积要远远不足,城市土地开发也很容易达到饱和,导致后续发展乏力;第二,制度对金融资本的利好,让粤港澳地区的产业结构会更多的倾向于金融产业的构成;第三,粤港澳地区不同制度(内陆和港澳)之间存在割裂,进而会有跨区难以协调、政策落地有限的问题。资本的集聚性流动、土地的有限性开发、政策的阻碍性落实都影响了区域的平衡与协调发展,让这里更多的体现是几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而非江浙沪那样的区域性发展。
但总的来说,近现代以来南洋地区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相连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也从这里开始。
通过香港,中国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对接的接口,可以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巨大投射力,反过来中国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
(3)华人移民
近代以来,中国的海外新移民,不管是来自东南沿海还是南洋地区,都将中国进一步的嵌合进了世界的体系当中。
这种个人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扩展。当然,这里的国家利益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或体现在政治,或体现在经济,或体现在文化上,不管何种领域,这种弥散全局的趋势必然导致世界对中国更为深刻地理解,也必然导致中国对世界更为深刻地建构。
施展所说,华人的移民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高度弥散性关系。但在我看来,不只是经济,而是中国全方位或多或少的影响,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建构起了这种高度弥散性关系。
3.中国的大陆秩序
中国的大陆秩序更多的以西南、西北地区为主,这种向内陆纵深的趋势,使这片区域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面貌,且这种面貌和中介地带——中原地区还有所不同。
中介地带的中原地区其实会有更多的陆权国家的面相,等级秩序、政治结构、历史渊源基本都以中原板块为承载进行千年嬗变,所以其陆权国家面相相对会呈现的更多。
而西南、西北地区的秩序受多种因素影响,反而呈现出了别的样态,这里我从地理、经济、制度和文化多角度去理解。
地理层面,西部地区平原相对较少,尤其是西南,破碎形地貌极易带来秩序的多元或崩坏。破碎性的地貌会极大增加管理成本,同时地理隔断也会减少文化交流,加之多民族的现象,进而产生多元的宗教信仰。再进一步,破碎性地貌且类型多为山地、高原、丘陵等,与农耕文明具有不适配性,其经济发展也难以得到提高,更别说近现代以来经济的传输路径主要是海洋,难以沿着陆地去纵深发展。加之其历史上远离中央王权,进一步带来管理统治成本的提高。
以上种种,都塑造了一个经济落后、文化多元、种族各异、地理破碎的区域面貌。而这却也能提供很多思考和视野。
其一是经济与政治的思考,其二是文化与精神的思考。经济与政治方面,这种区域面相有助于推动分配正义的实现。在国家精神的导向下,以及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转移支付、民族包容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倾斜。这种区域差异在精神追求的驱动下被尝试缩小,这种视野能更好地指引精神导向分配的正义。精神与文化方面,西部地区也提供了多种别样的生活面貌,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笔精神财富加上管理的视野,同中原文化和世界普遍精神相互交融发展,是更能推动中国完成世界化转型的。
综合来说,中国内部秩序的结构和世界秩序结构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将更加促进中国对自己以及中国对世界的体系化理解和结构性启示,这对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都是极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