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
(续上)
书法与诗的关联在书法作为现代艺术之时恰恰成为了最大的阻碍。…… 在现代中国,反复吟咏古人诗句最为频繁的领域或许便是书法界了,古诗或者伪古诗如幽灵一般萦绕在现代书法家的笔端。
唯有历经传统的断裂之后,书法、语言以及社会情境等诸要素之间的本质性关联才以一种极其清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书法、语言和社会情境之间哪怕稍许的抵触不合,在我们的感觉中都会被放大至几乎难以容忍的程度。于是,对于古人而言,书写疾病伤痛等日常琐事是自然而然的举动,到了现代书法家那里则变成了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行为;在古人的笔下掺入些许日常俗语、白话,显得天真烂漫,同样的情形出现在现代书法家的书写中却显得俗不可耐,难登大雅之堂。也就是说,在书法中的语言,现今注定以扭曲的形态存在。
可以列举二十世纪书法史上的一个实例,它展现了书法在新旧语言交替之际所能抵达的极限。这个例子便是白蕉的《兰题杂存》。《兰题杂存》无疑是一件已然历经时间检验并经典化了的作品,沙孟海在《白蕉兰题杂稿卷跋》中早有论断:“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沉浸于山阴书风,深具功夫。仓促困厄之时,也不失规范。三百年来能达此境界者寥寥无几。” 然而白蕉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件卓越的作品,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他是在运用自己鲜活的语言进行书写 —— 他书写这种语言就如同呼吸空气一般自然地存在于其中。
所以,我们在《兰题杂存》中看到的内容是鲜活的,其中既有清新睿智的三言两语,有清雅的旧体诗,也有这种类似于新诗般的句子:
没有什么高不可攀,莫说得她奇奇怪怪,送给你一阵香风,可有助于你思想生产。
但终究这样的语句于白蕉那里也只是某种天才式的偶然闪耀,在整个书法领域并未能激起丝毫涟漪。事实上,《白蕉先生自书诗册》里的短诗含有白话新语言清新特质。但总的说来影响太过微弱,远远不足以成为一种典范。故而,书法与语言的状况始终未曾得以改变:在抄写古诗词时,书法显得尴尬且做作,而当它试图抄写现代诗文,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蹩脚、贫乏的模样。
正如阿甘本断言:“传统的断裂并非意味着过去的丧失或贬值,相反,过去如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和影响力在发挥作用。…… 只要没有新的方法融入传统,它从此便只能是一个堆积物。” 在传统的内部,过去与未来、新与旧之间并未断裂,“因为每个对象在每个时刻都在流转,没有剩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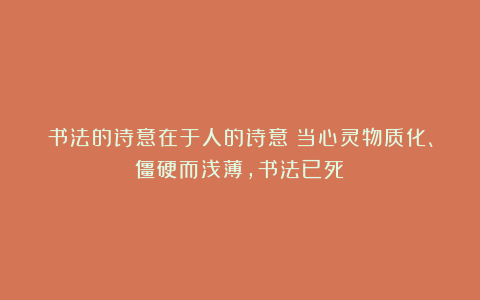
由于断裂的出现,我们在新与旧、过去与未来的事物中,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于是,站在时代的这一端,那种对古典语言的书写不再显得自然而不矫情:它已不再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语言革命一旦发生便难以逆转。书法的新生唯有通过直面这道语言的裂缝方可形成。
最后,回归我们标题中的问题:书法的诗意究竟去了何处?答案无疑是,当下书法的诗意已隐而不显,它既不在对古诗词的机械盲目抄写或者自作诗词之中,也不在对现代汉语及作为现代汉语结晶的新诗的简单拥抱之内 —— 用书法抄写新的内容是一件极易实现之事,但这内容要对书法本身真正产生作用必定极为艰难。
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可能性唯有维系于新的语言之上,毕竟,只有我们当下所使用的语言才是真正富有诗意之物。可以想见,新的书法诗意的生成需要穿越一个艰难的通道,因为它没有多少现成的可依赖的支撑点,由于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的某些改变,使得古典书法的诸多规范都会在此失效并需要被重新调整。
譬如,现代汉语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对于古典书法而言全然陌生;又比如现代汉语大量使用的 “的” 字,虽然在功能上相当于古汉语的 “之” 字,但 “之” 字在书法史的长河中经过无数双最为灵敏的手的锤炼,已然形成了千百种经典样式,足以应对一切需求,相较之下,“的” 字仿若一件未经锻造、贫乏而原始的工具。新的诗意定然不会是完美的 —— 古典书法恰恰是在各个方面都过于完美了,这使其沾染了浓厚的享乐主义色彩 —— 它会带着粗糙的质地,但必定强健、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