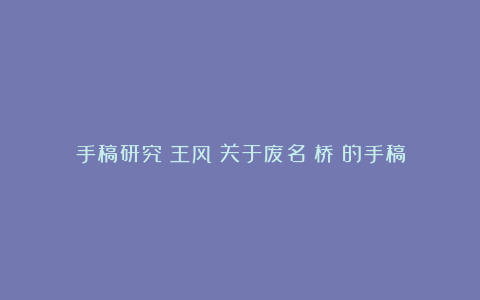|
废名代表作《桥》手稿现身,不仅是废名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研究史上的大事。作为《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编者,王风教授详细考释了《桥》的手稿的形成过程,充分阐释了这批手稿的学术价值。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感谢北京保利拍卖提供图片。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风
废名可谓之曰“作家的作家”,小说、诗歌、散文各文体均有成就,语体多变。虽于普通读者缘分不深,但对于同时代及后辈作家,影响深远。只是结集情况很不理想,所作小说基本留存下来,并大部成集出版;诗歌未曾结集,散佚至少数十首;至于文章,也有不少找不回来了。
废名文学创作方面的手稿,诗歌存散稿四五十页,另在周作人处有抄送的《镜》诗集手稿。至于散文,只有个别篇章遗存手迹。书信也极为罕觏。
小说方面,三本短篇小说集,与两部“莫须有先生”长篇,只有《坐飞机以后》最后两章存国图古籍部,此系未刊稿,因解放而不能续载,很可能是其时在北图工作的周丰一,代为藏存在那儿的。
唯有代表作《桥》,有非常完整的保存。此盖因废名对其极为重视,自以为是传世之作,而其他小说不与也。1957年《废名小说选·序》自谓“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所言应就是《桥》。因而无论南北流徙,此稿均带在身边。而且从草稿到历次修改稿,甚至谋篇布局时写下的片段,无一例外地都保留了下来。
本来著名作家代表作手稿,完整存世就极为罕见。像《桥》这样将历次修改,只字无遗地存留,可谓绝无仅有。
废名《桥》的写作延续了漫长的时间,起笔于1925年底,迤至1937年抗战伊始,实际上最终并未完成。关于这部长篇的构思,可以确认分上下两卷,而各卷又分上下篇,因而是四个部分。其中上卷上篇成十八章;上卷下篇共二十五章。1932年上卷成书由开明书店出版。随后续写下卷上篇,至抗战爆发,成十章,其中前九章定稿付多种杂志刊发,第十章还仅是初稿。
对于《桥》,废名有自己明确的写作理念。1930年8—9月,其上卷上篇厘定稿在《骆驼草》第十四—十九期连载,8月11日第十四期上“附记”自言:
关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我向来就有我的意见,一直到今日还没有什么改变……无论是长篇或短篇我一律是没有多大的故事的,所以要读故事的人尽可以掉头而不顾。我的长篇,于四年前开始时就想兼有一个短篇的方便,即是每章都要它自成一篇文章,连续看下去想增加读者的印象,打开一章看看也不致于完全摸不着头脑也。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时常姑且拿到定期刊物上发表一下。
所谓“姑且拿到定期刊物上发表一下”,指的是从1926年4月5日《语丝》第七三期,到1928年11月12日第四卷第四四期;1929年6月6日《华北日报副刊》第八二号至1930年3月10日第二八〇号,曾刊发上卷的大部分篇章。而《语丝》发表的部分,总题《无题》,并加编号,但这并非章节顺序,而是发表顺序。此间原因或许多端,作者本人的临时起意是一方面,部分章节作者自秘不拟过早公开是另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大概是要证明自己确实做到了“每章都要它自成一篇文章”。
《语丝》上所发表,均以“无题”为题,只有个别拟有章名。一开始写作时,对于书名,废名确乎没有个惬意的方案。不过早在《语丝》周刊1926年4月26日第七六期《无题之二》文末,附有4月8日致周作人函,言及:“现在这一套玩意儿,老是’无题’下去,仿佛欠了一笔债似的,今天把这一章誊写起来,不禁喜得大叫,得之矣:——《雁字记》,不很好听吗?你以为如何?”
此所谓“雁字”,正是《无题之二》亦即后来定名《狮子的影子》中,小林想起的事情:
六七岁的光景,他跟他的母亲下河洗衣,坐在洲上,见了雁,喊母亲看。一字形,母亲说,“这是一字;”人字形,“这是人字。”母亲还说雁可以带信,他说,“何不叫她多排几个呢?省得写。”……有一回,母亲衣洗完了,也坐下沙滩,替他系鞋带。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他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
不过随后还是“无题”下去,《雁字记》这一很有特色的书名,废名最终并没有采用。至1930年8月11日《骆驼草》第14期刊发首七章之时,已定名《桥》。“附记”云:
上卷脱稿时,自己展读一过,拟命名曰“塔”,而后来听说郭沫若先生有书曰《塔》,于是又改题曰“桥”。“桥”与“塔”都是篇中的章目,所以就拿来做一个总名,而又听说日本有一个讲桥与塔的书,名字就叫做“桥与塔”,则又不胜凑巧之至,这两个东西原来是这样有缘法。写至此,我又深深的有一段心事,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的故乡确乎也有一个桥与塔,过了桥就是塔,方我学步时便有人带我在那里玩,与诸君的世界自然无缘也。
废名故乡的“桥与塔”——出黄梅县城“便民门”,有一小桥和小塔,“过了桥就是塔”,是去往其外婆也是夫人所在岳家湾必经的道路。废名夫妻是表亲,妻子岳瑞仁长废名一岁,系其姨表姐,常见的“亲上加亲”。夫妻二人即《桥》中男女主人公的原型。
《桥》各类手稿的完整保存,可以极大程度还原废名的构思和写作过程。
试写稿“梅英本”第一章首页
试写稿“梅英本” 手稿中最早成组一份,无总题。共七章,有“一”至“七”序号。首页页边标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从字迹看,有可能是后来所追记。
此稿估计短时间内写成,涂改累累。计其内容,系成书后的前七章,“一”至“六”,对应“金银花”、“史家庄”、“井”、“落日”、“洲”、“猫”。而“七”,即成书的首章“第一回”。劈头言“我曾经读过希腊近代一位作家短短的一篇故事,题名失火。当我着手写我的故事的时候,我便不知不觉联想到那故事”。随后是这篇“失火”的内容。稿末大字书写“Fire Aspasia Stephanakis”。
此即希腊那篇故事的篇名,和两位小主人公的名字。有关此节,笔者编《废名集》时曾有考证,该“第一回”题注如下:
本回所谓“远方的一个海国”即希腊,“别的一个小故事”系希腊现代小说家蔼夫达利阿谛思(Argyris Ephtaliotis,1849-1923)所作𝘍𝘪𝘳𝘦(《火》)。英国古希腊学者劳斯(W.H.D.Rouse,1863-1950)译其作品27篇成《希腊岛小说集》(𝘛𝘢𝘭𝘦𝘴 𝘧𝘳𝘰𝘮 𝘵𝘩𝘦 𝘐𝘴𝘭𝘦𝘴 𝘰𝘧 𝘎𝘳𝘦𝘦𝘤𝘦,𝘣𝘦𝘪𝘯𝘨 𝘚𝘬𝘦𝘵𝘤𝘩𝘦𝘴 𝘰𝘧 𝘔𝘰𝘥𝘦𝘳𝘯 𝘎𝘳𝘦𝘦𝘬 𝘗𝘦𝘢𝘴𝘢𝘯𝘵 𝘓𝘪𝘧𝘦,London:J.M.Dent & Co.,1897)。周作人曾翻译过此书劳斯的序言《在希腊诸岛》(𝘐𝘯 𝘵𝘩𝘦 𝘎𝘳𝘦𝘦𝘬 𝘐𝘴𝘐𝘢𝘯𝘥𝘴),文末又有介绍和议论(《永日集》),可参看。又,周作人至少译过蔼夫达利阿谛思七八篇作品,均出于此书,不过没选中废名青睐的𝘍𝘪𝘳𝘦。废名遗物中存有这个故事的英文原文打印件。
废名即是在周作人处借阅了此书,而看到𝘍𝘪𝘳𝘦。至于“同我的故事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坐在树上掐金银花,一个站在树脚下接花”,也就是“金银花”一章的内容。
就《桥》的写作过程和结构关系看,此本前六章在废名那儿一直是一组独立的单元。而必须从“金银花”开始,因那是“诗眼”,和对全部故事的预言。初写此稿,在完成六章后,插入了“希腊近代一位作家短短的一篇故事”,并勾连到“金银花”,而“金银花”又远在开头就已写过。似乎这让他犹豫如何接叙以下的故事,而暂停了此本的推进。
这一版本与后来各版,在文字上自然有诸多不同。而最重要的差异,是小小的女主人公还不叫“琴子”而叫“梅英”。方便起见,可简称其为“梅英本”。
上卷上篇底本 “梅英本”1925年11月开笔,写了七章,推估在该年底前写成。重写可能在转年开始,亦即手稿中另外一套上卷上篇。序号从“一”到“十八”,其中缺“七”这一编号,计十七章。表面上看,似乎丢失了一章的手稿,但其实并非如是。这套手稿前六章,即“梅英本”之“一”到“六”的重写。“八”即后来成集本紧接着的“万寿宫”,其后直到“十八”,与成集本各章内容均对应。也就是说,并无缺失的章节。
之所以缺“七”这一编号,在于原来这个位置,是“梅英本”中废名“不知不觉联想到那故事”,即译写的𝘍𝘪𝘳𝘦。可以想见,如此安排,前后衔接都大成问题。显然废名一时也难以决定该如何处理,于是暂时搁置此节,由“八”继续他的故事。这是缺少“七”的真正原因。
1931年4月20日,废名为《桥》的出版作序,其中谈到:
本卷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以前我还常常不免有点性急,我的陈年的账总不能了结,我总是给我昨日的功课系住了,有一天我却一旦忽然贯通之,我感谢我的光阴是这样的过去了,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创造”。真的,我的《桥》牠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
对照这一套手稿,确乎停笔在这儿,此后的故事未留下片言只语的线索。他自己固然想明白道理而释然,但对于读者而言,遗憾总还是难以释怀吧。
上卷下篇底本 上卷下篇也存留一套手稿,序号从“一”到“二十六”,其中缺“二十一”。对照后来的成集本,知为“枫树”一章。不过在另外的散稿中,有未编号的此章完整内容,共5页粘连在一起,纸张不太一样。为何如此情形,难以忖度。不过如果插入此件,则无论如何也是全帙了。
“枫树”一章的内容有点儿特殊,讲的是“今天出现了一桩大事”,小林与狗姐姐重逢。上卷下篇全是小林、琴子、细竹之间的故事,狗姐姐一事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或许确乎有其原型,为废名所不能不记。
这套手稿编号至“二十六”,而后来结集时总共二十五章。其少掉的一章,在于前三章的调整。手稿“一”有如下内容:
……我的故事不必牵扯太多,只从他在最后所到之处写给他的姐姐的一封信上抄一句:“这里是我的新书”……在这“新书”当中,有一篇小小的文章是我此刻就要谈的。
“原文”省略了,并未抄到稿中。但显然废名是打算将上卷上篇中空缺的“七”的内容,移置到上卷下篇的开头。自然最后成集时,𝘍𝘪𝘳𝘦成了全书的“第一回”。如此下卷上篇就减少了一章。有关𝘍𝘪𝘳𝘦,如此调来调去,很可能是因为“金银花”对于废名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语丝》连载《无题》时,一直自秘该章,“留中不发”。或许他希望读者翻开书就看到“金银花”,而不愿意前头还有另一个故事。但𝘍𝘪𝘳𝘦本就是“金银花”的“引子”,最终他也不得不妥协。
上卷下篇的最后一章,成集后定题“桃林”。其中写到:“这个故事,本来已经搁了笔,要待明年再写,今天的事情虽然考证得确凿,是打算抛掉的……”又说“一位好事者硬要我补足”云云。著者故弄狡黠,但就笔者所猜测,此章不得不写又不情不愿,概因废名原有的计划,可能是全书一百章,上卷上、下篇,下卷上、下篇各二十五章。上卷上篇已写十八章,而“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大体原设想也是此数。如今上卷下篇多出“桃林”,成二十六章,数量冒了,所以有点儿不太舒服。自然最终由于𝘍𝘪𝘳𝘦前调书首的安排,减了一章,总算是满足了他的“洁癖”。
“桃林”一章末尾署“一九三〇,三,六。”字迹墨色连贯而下,一气呵成,显然是当时的原署,可想见那日废名志得意满的好心情了。
上卷下篇片段散页 手稿中还存留不少散页,大小不一。其中除“枫树”一份也可归此处且内容完整外,还有涉及𝘍𝘪𝘳𝘦的一页,是上卷上篇“第一回”的草稿。其他均属于上卷下篇的片段,其中关涉“今天下雨”2页;“桥”4页;“树”9页;“塔”3页;“桃林”1页。
从这些散页,可见废名写作时的雕肝镂肺,也可见他谋划此著的经心刻意,以至于要将自己所有的工作痕迹都保留下来。之所以这几章保留诸多残片,应不在于其他的已经丢失,大体上是他某些局部写作,表意不惬时的调整尝试,或临时攥住吉光片羽的紧急记录。
下卷上篇草拟稿 下卷上篇手稿,分布在三本软面抄中,两本开本较大,一本较小。其中的篇章,属于两个层面的版本。一本大开软面抄,封面大字“桥”,小字“下卷”,其下署“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动笔的日子。此本两章,第一章无序号,第二章署“二”,均无题名。
此稿涂抹殊甚,且许多页面的纸背,有修改或补充的片段。同类情况见于小开软面抄本,六到十章,其中六、七两章无序号,此后三章有序号。因此这两本均属于废名同系列的草拟稿。
下卷上篇底本 另一本大开软面抄,有一至七章,均标序号,其中前两章有篇题。此本固然前后笔迹墨色不一,但修改较少,且均未有纸背记录的片段,是共同的特点。故属于废名基本写定的本子。
“草拟稿”无三四五章,“底本”无八九十章,应该不是有所遗失,而是下卷从1932至1937年,整整五年才写10章,各个时期状态不一所致。因而有的章节并不草拟而直接大致写定;有的从草拟本直接边修改边誊清。
誊清本与清样 《桥》下卷1932年起,刊发稀疏。废名兴趣与事务渐多,已不复写上卷时的心无旁骛。大体是不时忆及此未竣的大事业,并有师长朋友邀稿,才写个一两章。1937年5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主事的朱光潜对废名文字极为推重,想必由于他的强力敦促,《桥》有了规律刊发的趋势。7月1日第一卷第三期刊发第七章《萤火》,已在抗战前夜;8月1日第四期刊发第八章《牵牛花》时,更是遍地烽火;9月1日该出版第五期,废名供稿第九章《蚌壳》,但刊物终于无法印出。
《桥》下卷誊清稿
《桥》的手稿堆中,留有两份废名的誊清稿,即《萤火》和《牵牛花》,字体极为端正。首页页边有废名亲笔“原稿用毕退还”、“原稿用毕请退还”字样。这是对朱光潜的过情之请了。当时报刊采用来稿,除非特别有身份的作者提出要求,一般不会答应这样一道麻烦的手续。《桥》留存的其他稿子,均是起草的草稿或底稿,横涂竖抹,只要自己看得明白即可。《桥》上卷的手稿,直行书写,不分段也没有标点,大体标点处空一格,分段处空两三格,典型的文不加点。显然是直到誊写送印时才补做这些“小事体”。下卷横行书写,大致分段加标点,但他人也不是很容易辨认其手迹。自然当年每个章节均会有外寄的誊清稿,但不会再回到他手中。这两章由于朱光潜格外的交情得以存留。就其字迹之整齐,可想见废名是生怕手民辨识不清,而将其心血文字排错。
《蚌壳》清样
《蚌壳》一章所存留的清样,显系杂志寄来让他校对。但淞沪会战该年8月13日打响,废名已不可能回寄清样,朱光潜更没有机会寄回誊清稿。这份清样的留存,也补充了新文学史的一个小细节,《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已经排好待印。只不过除了废名这篇外,已不清楚本期还有哪些人的文章。
至于第十章,如果没有战争,想必会在《文学杂志》1937年10月的第一卷第六期刊出。而如今,虽然拟稿尚在,我们终于还是连废名会给这一章取个什么样的篇题,也无从知晓了。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