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载道,心随世转的人生智慧
——读懂白居易
泰西凌波
导言:在断裂处寻找回响——诗歌何为?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众声喧哗的信息洪流,一个古老而紧迫的问题,便从历史幽深处反复传来叩击:诗歌何为?在这个话语被解构、意义被稀释、情感被消费的时代,诗歌是否仍能成为一种严肃的、介入现实的精神力量?抑或,它已退化为书斋里的语言游戏,或社交场域的点缀修辞?
当我们为当下的诗坛倍感困惑时,重返传统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找到一面镜子,照见自身的匮乏与可能。中国诗歌最伟大的传统之一,正是司马迁所倡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白居易所践行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份传统,将诗人的笔视为时代的良心,将诗歌的使命锚定于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与人文关怀。然而,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长廊后,抵达我们耳畔时,是否只剩下微弱的回音?
面对这份追问,我们需要一次双重的凝视:一次是向后的、深潜的,去重访一位古典大师——白居易——如何以其跌宕人生与三千诗章,将“诗以载道”与“心随世转”的智慧淬炼到极致;一次是向前的、敏锐的,去审视当代诗坛中那些仍在进行中的、鲜活的实践——比如山东诗人马启代与李林的创作——看他们如何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接续并激活这一传统,用诗歌为这个喧嚣而复杂的时代“立传”与“立言”。
这两次凝视并非简单的今昔对照,而是一场旨在探寻“诗歌精神何以可能”的深度对话。古典的辉煌能映照出当代的困境,而当代的挣扎与创造,亦能赋予古典传统以新的生命。让我们由此启程,在断裂处寻找那不绝的回响。
【正文】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晚号醉吟先生,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李白、杜甫并称“李杜白”。他的一生横跨中唐兴衰,仕途跌宕起伏,创作贯穿始终——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写下三千余首流传千古的诗篇;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在儒释道的交融中寻得内心平衡,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处世的典范。
一、少年苦读,崭露锋芒:漂泊中的生命启蒙
白居易的童年浸润于安史之乱后的凋敝与流离之中。家族自太原南迁,又因战火屡徙,“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的颠沛,不仅磨练其心志,更深植其目光向下的民本情怀。早年的苦难,成为他日后诗歌中深沉现实关怀的最初源泉。
其苦读之状,堪称自我淬炼的典范:“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乃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这不仅是才智的积累,更是心性的锻造。贞元三年(787年),十六岁少年怀揣着对文学的赤诚赴长安应试,登门拜谒时任著作郎的文坛宗师顾况。顾况见名帖“白居易”三字,打趣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言下之意是长安人才济济,无名少年想立足绝非易事。可当他展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目光骤然发亮,当即搁下笔改口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随即引白居易入座,秉烛夜谈至天明,从《诗经》的风雅传统聊到盛唐的诗坛气象,对少年的才情赞不绝口。次日便亲笔写信给长安各界友人,举荐这位“未来可期的诗坛新秀”,白居易也因此在长安文坛初露锋芒。此句不仅昭示其文学天赋,更隐喻了其一生将历经劫火而精神不灭的生命韧性,深契《周易》“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与元稹、李绅同登龙虎榜。三人初见便惺惺相惜,考场放榜后相约游长安曲江,在流觞曲水间饮酒赋诗,约定“苟富贵,勿相忘”,立誓要以诗文革新时政、体恤民生。尤与元稹,二人性情相投、志向相合,很快成为“生死之交”。他们常常同宿一处,秉烛探讨诗歌创作,从深夜聊至黎明,时而为一个意象争执不休,时而为一句警策击节赞叹。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任左拾遗,元稹奉命出使东川,二人分隔两地,却创下“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唱和纪录——元稹每到一处驿站,便将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诗篇,派驿骑快马送与白居易;而白居易收到诗稿后,往往彻夜不眠,挥笔应答,有时一日竟能回赠三首。有一次元稹在途中染病,写下“病中诗思转精深,满纸清愁寄故人”,白居易见诗后心急如焚,不仅回诗“遥知卧病孤灯下,感此相思泪满巾”,还特意托人送去良药与衣物。现存的《元白唱和集》收录二人唱和诗数百首,其中“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的诗句,正是这段“以诗为媒、灵魂相契”的深厚情谊的生动见证。
二、热血谏官,讽喻天下:以诗为谏的黄金时代
任左拾遗等谏官期间,白居易将“兼济天下”之志发挥到极致。他秉持“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原则,不仅在朝堂上直言进谏,更以诗歌为最锋利的谏书,与元稹、李绅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三人常常在白居易的居所彻夜研讨,窗外夜色深沉,屋内烛火通明,李绅先写下《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质朴诗句,让白居易与元稹深受触动。白居易当即拍案而起:“如此民生疾苦,当让天下人皆知!”随后便潜心创作《新乐府》五十首,元稹也提笔写下《新题乐府》二十首,形成“三子同心,以诗救世”的文坛盛景。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亲眼目睹农民盛夏割麦的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而一旁拾穗的贫妇更是衣衫褴褛,“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联想到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安逸生活,他内心备受煎熬,连夜写下《观刈麦》。诗成后,他第一时间寄给元稹,信中写道:“见其苦,感其难,夜不能寐,遂成此篇。愿与君共勉,不忘黎庶之艰。”元稹读罢热泪盈眶,当即回诗《田家词》,以“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的生动描写呼应,二人以诗唱和,共同揭露赋税苛重带给百姓的苦难。这种“观照”背后,是儒家仁政思想与《周易·谦卦》“卑以自牧”精神的交融——统治者当以谦卑之心体察民瘼,方能持盈保泰。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当代诗人李林在《红月亮——致敬父亲》中写下的“弯曲的背变成拉满的弓”,同样是对劳动者的深情刻画。白居易笔下的农人是“背灼炎天光”的群体群像,李林则聚焦于父亲这一个体,将岁月压弯的脊背比作“拉满的弓”,既写尽父爱的深沉,更暗含对千万劳动者在生活重压下坚韧不拔的敬意。二者虽跨越千年,却都以质朴而有力的笔触,捕捉到劳动者最本真的生命状态,践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初心。
元和四年(809年),长安城内“宫市”盛行,宦官借采购之名掠夺百姓财物,白居易目睹一位卖炭老翁的遭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了换取微薄的收入,即便“身上衣正单”,也只能“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最终,老翁的千余斤木炭竟被宦官以“半匹红纱一丈绫”强行换走。白居易目睹此景悲愤交加,回家后挥笔写下《卖炭翁》,字字泣血揭露掠夺的残酷。同年,江南遭遇大旱,衢州出现“人食人”的惨状,而长安城内的权贵们却依旧宴饮享乐,“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白居易得知后怒不可遏,写下《轻肥》一诗,以强烈的对比直指社会不公。李绅读罢《轻肥》,直言“字字泣血,振聋发聩”,随即创作《答白公》,痛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三人相互呼应,让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遍及朝野,不少权贵读后“皆变色”,也让唐宪宗不得不正视社会问题。
白居易《轻肥》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对比,在马启代的《然后……》中得到了当代回应:“麦香里藏着杀戮,炊烟下埋着呜咽”。马启代以“麦香”与“杀戮”、“炊烟”与“呜咽”的强烈对冲,揭露现代社会中自然掠夺与人性异化的困境,与白居易一样,都以诗为刃,刺破虚假的繁荣表象。不同的是,白居易批判的是封建皇权下的阶层剥削,马启代则直面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与社会矛盾,但二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使命一脉相承,都是对时代不公的勇敢发声。
此期杰作《长恨歌》的诞生,更藏着一段文人相契的佳话。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及安史之乱的往事,三人感慨万千。王质夫举杯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试为歌之,何如?”白居易欣然应允,陈鸿则承诺作《长恨歌传》与之相配。当晚,白居易在寺中秉烛疾书,从深夜写到东方发白,笔锋在浪漫爱情与历史兴衰间流转,既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深情,也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讽谏。次日清晨,他将诗作读给二人听,读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时,王质夫与陈鸿无不落泪,王质夫赞叹道:“此诗一出,必传千古!”这首诗将一场重大的政治灾难,融铸为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史诗,暗合《周易·乾卦》“亢龙有悔”的警示:极权与极欲,必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悔恨。诗作在浪漫叙事中,完成了对历史兴衰的深刻反思。
三、贬谪江州,心境转折:在“否塞”中窥见本心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朝堂上下一片噤声,白居易不顾自身职位低微,上书请求缉拿凶手,却被权贵罗织罪名,贬为江州司马。消息传来,元稹正在通州贬所,闻讯痛哭失声,不顾自身病弱,连夜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诗句中满是担忧与悲愤,白居易收到书信时,正乘船赴江州,读罢掩面长叹,在船上写下《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二人虽相隔千里,却以诗为桥,相互慰藉,这份情谊在宦海沉浮中更显珍贵。
江州的岁月,是白居易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光。他“谪居卧病浔阳城”,远离朝堂纷争,满心孤独落寞。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夜,他在湓浦口送别友人,忽闻江面传来琵琶声,“铮铮然有京都声”,便邀弹琵琶者相见。原来是一位从长安流落至此的歌女,早年曾是教坊名妓,“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如今却“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歌女弹奏琵琶,指法娴熟,“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琴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婉,诉说着身世的沉浮。白居易听着“弦弦掩抑声声思”的琴声,联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又忆起与元稹的分隔之苦,不禁泪湿青衫,感慨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晚便写下《琵琶行》这一千古名篇。诗成后,他抄录多份,分寄友人,元稹读罢写道:“乐天此诗,我读之三遍,每遍皆涕泗横流。君之遭遇,我之痛也。”
白居易在江州的孤独与共情,在李林的《一条游在夏天的鱼》中找到了跨越时空的回响:“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沦落与鱼“渴望清凉”的呐喊,都是对个体困境的真切诉说。白居易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表达共情,李林则以直白的呐喊传递渴望,二者虽表达方式不同,但都源于对生命苦难的深切感知,践行了“泄导人情”的诗歌使命。而马启代在《我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中写下的“风撕裂我的衣角,却吹不熄我眼底的光”,更与白居易贬谪后的坚守形成呼应——白居易在“否塞”中仍心系民生,马启代在时代风浪中始终保持清醒,都是“穷则独善其身”却不失锋芒的精神写照。
这段时期,白居易开始系统地汲取佛道思想资源,与庐山高僧如满禅师交往密切。如满禅师深知白居易心中郁结,时常邀他入山参禅,二人在庐山东林寺对坐品茗,探讨佛理。如满禅师曾对他说:“世事如露亦如电,唯有心安是归处。”白居易深受启发,在寺中居住月余,每日与僧人同吃同住,晨钟暮鼓间,心境逐渐平复。他写下《题东林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中虽有对人生境遇的感慨,却已透出几分豁达。他还效仿陶渊明,在江州城外开垦荒地,种菊栽竹,自号“醉吟先生”,时常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借酒抒怀,“醉里狂言醒可怕,杯中好物闲宜进”,在诗酒中寻求内心的平衡。
即便身处失意,白居易仍未完全放下为民之心。他发现江州百姓饮水困难,便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凿“琵琶井”,解决了周边居民的用水问题;见农田灌溉不足,便上书朝廷请求疏浚当地河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底层百姓的悲欢,也让他意识到,“兼济天下”并非只有朝堂进谏一条路,在地方上实实在在为民做事,亦是践行初心。
四、外放治民,闲适自守:实践中的“中和”之道
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是白居易将理想付诸实践的“中和”时期。他远离了朝堂党争的“亢龙”之危,在地方官的任上找到了“飞龙在天”(《乾卦》)的另一番天地——直接造福于民。
在杭州任上,白居易与时任越州刺史的元稹再度隔江相望,二人虽不能时常相见,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唱和。元稹寄来《寄乐天》,诗中描绘越州“镜水稽山满眼春,可怜名士往来频”的风光,白居易便回赠《答微之》,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描绘杭州盛景。这段唱和,后来演化成《忆江南》三首,成为千古绝唱。公务之余,白居易发现西湖水利失修,每逢旱季便农田缺水,雨季则洪水泛滥。他亲自带人勘察西湖,制定疏浚方案,组织百姓清除湖底淤泥,修筑堤坝,这便是著名的“白堤”。他还制定《钱塘湖石记》,详细记载西湖的水利管理方法,明确规定“湖水多少,各有定数”,让百姓按规用水,这份具有法规效力的文书,展现了他极高的行政理性与民生情怀。闲暇之时,他常与杭州文人游湖赋诗,春日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西湖的生机盎然与百姓的安居乐业,让他内心满是欣慰,《钱塘湖春行》中字里行间的欣悦,正是其治理初见成效后,内心与自然和谐共振的写照,体现了《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之美。
调任苏州后,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遇,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刘禹锡刚从朗州贬所召回,性格乐观豁达,时常以诗鼓励白居易。一次,二人同游苏州园林,面对满园春色,刘禹锡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劝慰白居易放下过往的失意,珍惜当下的时光。白居易读罢深受鼓舞,当即回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二人在苏州时常结伴出游,或登虎丘山,或游寒山寺,饮酒唱和,留下了“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唱和佳话。在刘禹锡的影响下,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更趋豁达,《暮江吟》中“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致描写,精准捕捉了黄昏阴阳交接、动静相宜的瞬间,这亦是其人生状态的隐喻:在进取(兼济)与退守(独善)之间,找到了一个从容的平衡点。
白居易在杭州、苏州的治民实践与闲适创作,与李林笔下的“白云山的晨雾、康王河的暮色”形成呼应。李林在诗中写道:“晨雾漫过田埂,每一滴都盛着百姓的炊烟”,他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乡土风光,背后是对家乡与百姓的深切眷恋;而白居易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看似写景,实则藏着对民生安乐的欣慰。二者都将个人心境与地方风物、百姓生活相融,让闲适诗不再是单纯的避世之作,而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巧妙平衡。
在苏州任上,白居易同样勤政爱民,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赋税,兴修水利。离任时,苏州百姓倾城相送,有人捧着自家种的瓜果,有人献上亲手缝制的衣物,还有老者拄着拐杖,一路送他至城外江边。白居易感动不已,写下《别苏州》:“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政声。”船行江上,百姓仍在岸边挥手呼喊,他站在船头,热泪盈眶,心中默念:“此生能得百姓如此相待,足矣。”这段外放经历,让白居易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仍践行着“兼济天下”的初心,只是将这份初心从朝堂讽谏转向了地方治理的实处。
五、晚归洛阳,乐天知命:融合三教的终极安顿
晚年致仕,退居洛阳香山,白居易完成了其人生哲学的最终整合。“香山居士”之号,标志其儒者、官员身份之外,佛门居士身份的明朗化。
此时的诗作,充满洞明世事的淡然与日常生活的暖意。他与友人刘十九的情谊,质朴而纯粹。刘十九是白居易的布衣之交,二人没有官场的繁文缛节,唯有朴素的情谊。寒冬腊月,大雪将至,白居易在家中温好酒,燃起红泥小火炉,想起远方的刘十九,便写下《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短短二十字,道尽知己相伴的温馨。刘十九收到诗后,当即冒着大雪赶来,二人围炉夜饮,从农事聊到诗文,从过往聊到当下,炉火映着笑脸,酒意伴着情谊,直至天明才尽兴而散。
裴度曾是宰相,与白居易志同道合,晚年也隐居洛阳。二人时常相约游香山寺,白居易发起“香山九老会”,邀请裴度、刘禹锡、如满禅师等九位老友,定期在香山寺聚会。聚会时,众人饮酒赋诗、抚琴下棋,不问世事纷争,只谈人生感悟。一次聚会中,白居易提议将众人诗作结集,裴度欣然应允,亲自为诗集作序,取名《香山九老诗集》。席间,白居易写下《达理二首》,以“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的诗句,抒发内心的豁达。此时的他,融合了儒家“居易俟命”的从容、道家“安时而处顺”的豁达与佛家“观空破执”的智慧,达到了“委顺”与“养浩然”的辩证统一。
白居易晚年“乐天知命”的豁达,在马启代的《暂住》中得到了当代诠释:“来一趟人间只是暂住,唯有良心是永恒的行囊”。白居易以“委顺以待终”的姿态接纳命运,马启代则以“暂住”的生命认知坚守良心,二者都在生命的沉淀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坚守。而白居易《忆江南》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好追忆,与李林“红月亮下,父亲的鼾声里藏着岁月的安暖”的诗句,都以温情笔触定格生命中的美好,展现了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释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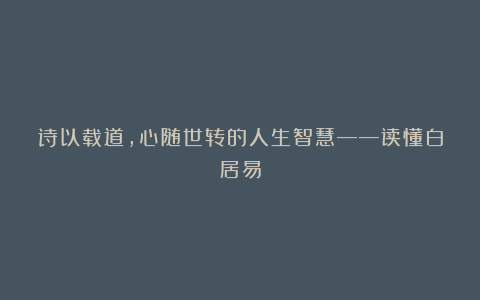
他还追忆早年在江南的生活,写下《忆江南》三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好回忆,不再仅是风景描绘,更是对生命中所有光明与美好时刻的凝练提取,暗合《周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和谐圆满之境。晚年的白居易,与高僧如满禅师交往愈发密切,每日清晨便入寺参禅,研读佛经,还出资修缮香山寺,舍宅为寺,皈依净土。他与诗人李商隐也有交往,李商隐年少时便仰慕白居易的才华,晚年专程赴洛阳拜访。二人相见时,白居易已年过七旬,李商隐正值壮年,白居易见他才思敏捷,感慨道:“我死后,转世为汝子,以续斯文。”李商隐听后深受感动,后来果然生一子,取名“白老”,以表对白居易的敬意与怀念。
会昌四年(844年),白居易病情加重,仍坚持整理诗文集《白氏长庆集》,将一生的创作与感悟留存后世。会昌六年(846年),白居易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五岁,葬于香山。临终前,他嘱托家人薄葬,不设墓碑,只在墓前种下几株松柏。友人裴度、李商隐等为他送行,裴度写下《哭乐天》:“四海齐名白与元,百年交分两心坚。谁知千古一骸骨,犹共今朝桃李春。”
六、人生思想与处世观解析:一个典范的精神结构
白居易的一生,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与现实碰撞、最终实现内心平衡的典范。
文学思想:诗以载道,经世致用。他始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诗歌视为反映现实、干预社会的重要工具。他的讽喻诗针砭时弊,感伤诗抒发真情,闲适诗寄托心境,无论何种题材,都离不开对“人”与“世”的深切关注。这种文学思想,本质上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生动体现。他以通俗浅白的语言创作,力求“老妪能解”,确保诗歌的社会传播力,真正践行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创作初衷。
这一思想在马启代与李林的创作中得到了忠实传承。马启代在《受难者之思》中写下“我以笔为剑,刺破黑暗,只为让光明照进苦难”,直言诗歌的批判使命,与白居易“补察时政”的主张一脉相承;李林则以“夏日的乌云,你是来拯救世间,还是助纣为虐”的追问,延续了白居易“泄导人情”的创作初心,二者都让诗歌成为连接个体与时代的纽带。
人生哲学:儒释道交融,达穷兼济。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完美诠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早年以儒家入世思想为核心,直言敢谏、心系民生;贬谪后逐渐吸纳道家避世与佛家禅意,在失意中寻求内心安宁;晚年则将三者融会贯通,形成“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他的思想转变,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不同人生阶段顺应时势,在阴阳转化中寻求平衡,深刻体现了《周易》“与时偕行”的核心智慧。
处世之道:刚柔并济,中庸平和。白居易的处世之道,兼具刚健与柔和的特质。早年作为谏官,他秉持原则、直言敢谏,展现了《周易·乾卦》的刚健之力;贬谪后收敛锋芒,以共情与包容对待他人与命运,体现了《周易·坤卦》的厚德载物;晚年则刚柔并济,在坚守内心道德准则(养浩然)的同时,顺应天道自然(委顺以待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平和境界。他与元稹、刘禹锡、裴度等友人的交往,始终坚守真诚与道义,成为千古佳话,也展现了他“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
七、文学史的坐标与东亚回响
白居易的文学成就,需置于中唐至晚唐的历史转型中审视。他与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不仅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传统的继承,更在理论与创作上形成系统化的文学革新思潮。其诗风的“浅切平易”,与韩愈、孟郊的奇崛险怪形成鲜明对照,共同构成中唐诗歌多元并峙的格局。尤为重要的是,白居易将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这一自我分类不仅完整呈现其创作全貌,更暗含对诗歌功能的结构性思考——文学既可载道刺世,亦可安顿心灵、记录人情,这种兼容性成为后世文人调和仕隐矛盾的重要文学范式。
其影响远播东亚,尤以日本为最。平安时代,《白氏文集》东渡日本,成为日本贵族与文人的必读书籍,嵯峨天皇甚至专门设立“《白氏文集》讲筵”,召集大臣与文人研读白居易的诗歌。日本诗人菅原道真、纪贯之等都深受白居易影响,菅原道真曾写道:“乐天诗章传海外,东瀛学子竞效仿”,其诗作中对民生的关怀、对自然的描摹,都可见白居易的影子。白居易诗中“闲适”“感伤”的情调,与日本物哀美学深度契合;其“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观,亦启发日本汉文学的现实关怀。直至江户时代,白居易仍是庶民教育的经典,其通俗性跨越阶层界限,成为东亚文化圈共享的精神资源。
八、思想矛盾的现代透视
白居易“兼济”与“独善”的平衡,并非线性过渡,而充满内在张力。晚年他自诩“中隐”——“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则是对传统“隐逸”概念的创造性转化:既不愿全然归隐牺牲物质安逸,又需与政治风险保持距离。这种“吏隐”姿态,固然是乱世中的生存智慧,却也折射出士大夫在专制皇权下的局限:当系统性的政治改革无望,个人的道德坚守往往退守为私人生活的精致化。其晚年大量闲适诗中,对园林、酒器、音乐的沉浸,固然有“乐天知命”的豁达,亦不无对现实责任的微妙回避。这种矛盾,正是中国古代文人面对“道”与“势”永恒困境的缩影。
这一矛盾在当代诗人马启代的诗作中也有呼应。他在《在风中睁着眼睛》中写道:“我站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既不愿沉沦,也无力突围”,道出了当代文人在复杂现实中的挣扎。与白居易不同的是,马启代并未选择“中隐”式的回避,而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持续以诗歌叩问现实,这种坚守让“诗以载道”的传统在当代更具锋芒。
九、生命伦理与终极安顿
白居易对生死问题的思考,经历了深刻演变。早年丧母、中年丧女、母、中年丧女、晚年丧子,连番打击使其不断叩问生命意义。他最终形成的“委顺”哲学,并非被动屈服,而是融合儒家的“居易俟命”、道家的“顺应自然”与佛家的“观空破执”。在《达理二首》中,他既言“我无奈命何”,又强调“唯当养浩然”,体现了“知命”与“立命”的辩证统一。临终前,他舍宅为寺、皈依净土,并以“遍览经藏,精修念佛”为归宿,完成了从文学抒情到宗教安顿的终极转向。这种融合三教的生死观,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纾解生命焦虑的精神路径。
十、历史形象的重塑与反思
白居易在后世的接受史,本身是一部被不断重塑的历史。宋代文人既推崇其“仁政爱民”的吏治典范,又对其晚年“蓄妓饮酒”的私生活多有微词,折射出理学兴起后道德标准的严苛化;明代袁宏道等人则从其闲适诗中读出了“性灵”解放的先声,加以推崇,将白居易视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先驱;至近代,其讽喻诗被赋予“人民性”解读,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源头。这些嬗变,揭示出白居易形象的多元性与可塑性:他如同一个深邃的文化符号,不断回应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诉求。而回到历史现场,白居易最根本的特质,或许正在于其“不完美”的真实性——一个有热血、有软弱、有矛盾、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断调适的鲜活生命。
结语:流动的智慧与永恒的回响
白居易的一生,是一部“诗与人互证”的精神史诗。他以诗歌为舟楫,载着儒者的忧患、道者的通达与佛者的慈悲,穿越中唐的政治风波与人生逆旅,最终抵达内心与世界的和解。他的智慧不在于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在于展现一种“流动中求平衡”的生命艺术:在兼济与独善间灵活切换,在讽谏与闲适间从容游刃,在执着与超脱间安然自处。这种智慧,如同其诗中的春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为我们应对变局、安顿身心,提供着不竭的精神滋养。
【精神谱系的艰难显影
一一从“江州司马青衫湿”到“在风中睁着眼睛” 】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对白居易精神世界的漫长跋涉。我们看到,一个灵魂如何在“兼济天下”的豪情与“独善其身”的智慧间从容摆渡,如何将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超脱与佛家的慈悲,熔铸为一种“乐天知命”而又不失锋芒的完整人格。他的诗歌,无论是《卖炭翁》里对掠夺的冷峻白描,还是《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抑或是晚岁闲适诗里“红泥小火炉”的温情,都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将个体生命体验,与更广阔的时代命运和人类普遍境遇紧密相连。
中国军旅作家诗人李林
当这曲回荡于中唐的诗歌交响渐行渐远,我们不禁要问:那“为事而作”的笔锋,今天是否已然锈蚀?那“补察时政”的良知,是否已在后现代的碎片中消散?
历史的回音并未断绝。在当代诗坛的多元喧哗中,我们仍能辨认出一些执着的身影,他们自觉地站在了这个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开创的精神谱系之中。然而,这绝非一次轻松的投奔,而是一场需要巨大勇气的当代转化。他们面对的“时”与“事”,其复杂性与悖论性已远非中唐可比:权力与资本以更精微、更系统的方式编织着生活的罗网;个体的异化不再仅是“满面尘灰”的劳苦,更是一种嵌入数字生存的精神漂泊;那“救济人病”的呐喊,需要在全球生态危机与技术伦理的混沌中,重新寻找锚点。他们书写的“纸”,也浸透了现代性的焦虑、断裂与无意义感。然而,正是在这更为破碎的舞台上,那颗以良心为笔、以现实为纸的初心,其坚守才更显出一种孤绝的勇气与悲壮的诗意。
如果说,白居易在江州秋夜,因琵琶女的琴声而“青衫湿”,那是士大夫与沦落人之间跨越阶层的共情,其背后尚有一个虽不完美但可理解的伦理世界;那么,千年后的今天,诗人马启代选择“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其所凝视的风暴,其成分已混杂了物质与信息的尘埃;李林从“红月亮”下父亲弯曲的脊背上读取的重量,既承着传统的农耕艰辛,也压着新时代城乡迁徙的无言阵痛。马启代在《然后……》中写下“麦香里藏着杀戮,炊烟下埋着呜咽”,以尖锐的对立揭示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人性困境,与白居易《轻肥》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李林则以“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的直白呐喊,延续了《琵琶行》中对个体苦难的深切共情。他们的姿态或许不同——一者如哲人般冷峻叩问存在本质,一者如赤子般热切拥抱生活粗粝的质感——但内核都是在意义漂浮的语境下,执意要为脚下的土地和生存其间的普通人,重新寻回一种可以被语言承载、被心灵共感的温度与尊严。
因此,对白居易的重新解读,并非一场怀旧的祭奠,而应成为一把钥匙,用以开启对当代诗歌价值与困境的再审视。让我们将目光从香山居士的墓阙收回,投向正在我们身边展开的、鲜活而真切的诗歌现场,看一看,那“野火烧不尽”的春草精神,如何在新的世纪风暴中,顽强地萌发新绿。
【写后记:良心为笔,时代为纸——马启代、李林的现实书写与文学传承】
近读山东诗人马启代、李林的作品,结合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诗歌的研究与学习,心有所感,更有所思。在诗坛不乏辞藻堆砌、情感空泛之作的当下,二人的创作如清风破雾,始终坚守“不无病呻吟,为时代发声”的初心,以生命体验为根、以苍生情怀为魂,用诗歌为时代立传、为人心立言,其精神内核与“李杜白”以来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在现实关怀与精神坚守中,构筑起当代诗歌的坚实底色。
马启代的诗歌,是“良心写作”的生动践行,更是对时代本质的深度叩问。四十载笔耕不辍,他始终以笔为刃,既直面现实的褶皱与暗角,又追问存在的价值与本质,作品兼具尖锐的现实观照与深沉的人文关怀。诗集《暂住》以“来一趟人间只是暂住”的生命认知为轴心,将个体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暂住”的轻盈与“良心永恒”的厚重形成鲜明对比,既暗含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又彰显对精神永恒性的坚守,与白居易“乐天知命”却“养浩然”的人生哲学异曲同工;《我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恰似他创作心境的自白,“风撕裂我的衣角,却吹不熄我眼底的光”,以极具张力的意象,展现了在时代风浪中保持清醒与坚守的精神,与白居易贬谪江州后仍心系民生的执着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然后……》则以“麦香与杀戮”的强烈对冲,“麦浪翻滚着金色的谎言,镰刀收割着最后的善良”,揭露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掠夺与人性的挣扎,用“黑白交替”的哲思隐喻生活的未知与迷茫,尽显对生态危机与人性困境的深切忧虑,其批判锋芒与白居易《轻肥》《卖炭翁》的讽喻精神一脉相承。从《幸存者笔记》到《受难者之思》,他的诗歌始终扎根时代土壤,将个人感悟升华为集体共鸣,既不回避社会的伤痛,也不放弃对良知的坚守。
如果说马启代的发声是哲思性的深度叩问,李林的诗歌则是生活化的真情呐喊。他的创作源于最本真的生存体验,正如马启代所评:“来自生活和生存体验的全部体悟,保鲜保真没有任何问题”。《红月亮——致敬父亲》中“弯曲的背变成拉满的弓”,以质朴却极具张力的意象,将父亲劳作一生的坚韧具象化,既写尽父爱的深沉厚重,也暗含对千万劳动者的崇高敬意——这与白居易《观刈麦》中对农人的悲悯情怀,在关注劳动者、赞美生命韧性上形成深刻共鸣;《夏日的乌云》中“你是来驱赶炎热拯救世间/还是增加闷热助纣为虐”的追问,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为切入点,折射出对社会现实的困惑与批判,延续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将“泄导人情”的诗歌功能落到实处;《一条游在夏天的鱼》里“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的呐喊,直白而真挚,既藏着对生命本真的怜悯,也饱含对自由与尊严的热切渴望,与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精神一脉相承。他并非刻意雕琢技巧的技术主义者,却以最鲜活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白云山的晨雾漫过田埂,每一滴都盛着百姓的炊烟”,将乡土风光与民生安乐相融,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闲适与民生关怀异曲同工。
两位诗人虽创作风格各异,却在“为时代发声”的内核上高度契合。马启代以哲思为骨,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构建起兼具思想厚度与艺术张力的诗歌体系,其“自守现实关怀的立场”让诗歌成为批判现实、反思人性的利器;李林以生活为源,在个人经历与人间烟火中,捕捉时代的细微脉动,用真诚无伪的表达,让诗歌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的情感纽带。他们都摒弃了无病呻吟的矫饰,拒绝脱离现实的空泛抒情:马启代的“良心”是对时代本质的坚守,李林的“真情”是对生活本真的敬畏;前者如深邃的观察者,于纷繁世事中洞见核心,后者如热忱的记录者,于日常点滴中映照时代。
在当代诗歌寻求突破的语境下,马启代与李林的创作给出了珍贵的答案——诗歌的生命力,永远根植于时代与人民。他们用作品证明,真正的诗歌不必依赖华丽辞藻的堆砌,不必追逐转瞬即逝的潮流热点,只需以良心为笔、以时代为纸,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集体的生存境遇相连,便能发出穿越时空的回响。这样的写作,既是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传统的虔诚继承,在诗学上,它亦是对抗语言空心化、经验碎片化的一剂峻药;更为当代诗歌的现实书写提供了鲜活范式,让我们重新看见诗歌在记录时代、慰藉心灵、启迪思考中的永恒价值。
当然,文学的疆域辽阔,“为时而著”的厚重仅是其中一道深刻的山脉。诗学探索的多元路径,诸如对语言本体的精研、对潜意识幽微的勘探、对文化符号的智性戏仿,皆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启代、李林们的意义在于,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诚恳与炽热,牢牢守住了诗歌与大地、与人民之间那条最古老也最易被遗忘的血脉。他们的创作,与那些专注于内在宇宙或形式革命的探索,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复杂而必要的精神地形图。
文学本就允许多元表达,既需要“为时而著”的厚重之作,也可以有“为己而吟”的轻灵之作;既需要针砭时弊的锐度,也可以有安放心灵的温度,不必以单一标准苛求所有创作。纵观古今,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存在优劣之分,而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永远是那些情感真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篇章。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白居易们的时代有他们的担当,我们的时代也有文人的坚守。当下,我们更需静下心来发掘那些真正的精品——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延续着中国诗词“言志、抒情、载道”的精神内核,在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光华。当我们将白居易的智慧、马启代的冷眼、李林的赤忱并置观之,我们所见证的,已不止是文学风格的接力,而是一种文明在应对不同历史周期之困厄时,其内在精神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显形。这,或许才是那“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所能给予我们的最深邃的启示。
作者简介
泰西凌波,英语高级教师。深耕教坛数载,精研英语教学与高中生生涯规划,愿以匠心与爱心,为学子未来筑基引航。
自年少便醉心诗词雅韵,尤钟情于家乡肥城的人文底蕴。今愿以文字为舟,打捞濒危的民俗遗珍,描摹生动的风土市井,以期唤醒尘封的记忆,赓续桑梓文脉。更致力于探寻各地的神话传说,让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在笔端交融,烛照当下,辉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