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
一汉碑的成长,壮伟的童年
位于西泠印社孤山之巅的“汉三老石室”,乃是由西泠先贤们慷慨解囊并倡导社会各界义卖募捐,成功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后特意建立的,行动成功关键在于:浙江地区的汉碑极为罕见,仅有此一块。《汉三老碑》若流失海外,不仅损害了浙江乡邦士绅的颜面,更是对祖先遗产的不敬。在秦汉三国时期,文明的中心位于西北和中原,如秦都咸阳、东汉洛阳、汉唐长安等。而吴越之地,即今天的江苏和浙江,当时处于边缘地带。唐代碑石多见于长安(今西安),南北朝碑多见于洛邑(今洛阳),而汉碑则多见于陕西和山东的兖州、徐州一带。随着时间流逝,汉碑的集中地转移至以学术圣地名誉的曲阜孔庙。
山东曲阜之所以汉碑众多,主要是由于孔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而,若严格追溯汉碑的起源,最早的是河南偃师出土的《袁安碑》(公元89年,永元四年)和《袁敞碑》(公元115年,元初二年)。随后是《西岳华山庙碑》(公元161年,延熹四年)。《袁安碑》和《袁敞碑》的形制已有立碑的功能,是已知最早的汉碑。但根据记载,《华山庙碑》提到在延熹四年立碑前的一百多年,华山岳庙已有碑石,只是如今已无法见到。这意味着,汉碑的历史可能比已知的《袁安碑》和《袁敞碑》还要早30至60年。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严格的汉碑形制,那么西汉时期的石刻更为丰富。例如,曲阜的西汉《鲁孝王刻石》,又称《五凤二年刻石》。新莽时期有作为坟坛刻石的《祝其卿刻石》和《上谷府卿刻石》;邹县孟庙则存有《莱子侯刻石》。此外,还有《大吉买山地记刻石》。然而,这些石刻并不能称为“碑”,而只能泛称为“刻石”,在学术上称为“碣”。若要称为“碑”,在形制上必须具备四个特征:首先,它必须是竖立于墓前的长方形片石;其次,必须有位于正文上端的“碑额”,底部则有呈龟形的“碑座”,又称“龟趺”;第三,碑面上必须有圆孔以系绳索,用于将棺材送入墓穴,这个圆孔称为“碑穿”;最后,正文碑记之后必须有韵律的铭辞。但西汉以来的《五凤二年》、《祝其卿》、《上谷府卿》、《莱子侯》等石刻,虽然都是刻在石板上,却缺少“碑额”和“碑穿”,也没有附有铭辞,且多为横式,因此不能被严格称为“碑”。
这些条件的完备和形制的发展,是在东汉时期的《西岳华山庙碑》以及《袁安碑》和《袁敞碑》时期。不过,《西岳华山庙碑》在百年前的立碑记载只见于文献;而《袁安碑》和《袁敞碑》虽有“碑穿”却缺少“碑额”,略有遗憾。此外,这两块碑文采用的是汉篆字体,而非标准的汉代隶书,这又是一大遗憾。作为汉碑的经典样式,它们仍显得不足。
至于“碑额”,它原本只是碑文的标题。其来源也颇为有趣。古代的石柱和石门框上常有刻字,如寺庙的山门或墓地的阙柱。汉代的石门阙最初并无刻字,仅立石柱为阙,后来才出现刻字,如《汉故兖州刺史王稚子阙》(山东)、《汉故幽州刺史冯焕阙》(四川)、《沈君阙》等。汉墓阙的题字开始盛行,到了东汉时期,正规的碑形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于是将石阙的形制转变为碑额,并加以发扬光大。今天的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仍值得我们参考。
学习汉隶可以学习“嵩山三阙”,追求骨势开张,避免流于俗媚。这《嵩山三阙》指的是河南嵩山的《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三块铭文,字形介于篆隶之间,浑厚而古朴,笔画虽残缺但仍显天机。大成按
二汉碑的繁丽世界,文、书、刻的互动
从“碣”(刻石)到“碑”,再到“阙”,石刻文化在汉末时期已基本形成了其历史形态。当然,这里所说的基本形成,是因为后世的石刻类型中还有墓志铭和造像记的出现。但“碣”、“碑”、“阙”,以及“摩崖”等,如陕西汉中褒斜栈道上的《开通褒斜道记》、《石门颂》、《鄐君表记》、《杨淮表记》、《西狭颂》等石门十三品,这些共同构成了石刻书法的重要部分。
汉碑的书法大多出自民间职业书匠之手。他们的崛起首先是因为汉字在社会应用层面的扩大,其次是东汉末年官僚豪强成为主导力量,大力推崇立碑风气,以碑文来谀墓颂德。立碑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撰写碑文和书法成为一种致富手段,不仅仅是糊口谋生。其中既有蔡邕这样的书法大师,也有官府的书佐、胥吏、抄书手,以及下层百姓中的秀才和塾师,还有专门凿石刻碑的工匠。在汉碑时代,已经出现了专职的撰文者、书写者和刻碑者的分工。
以我们熟悉的《张迁碑》为例,碑文中有一个有趣的错误,碑文中有“爰暨於君,盖其繵縺”。撰文四字铭记,体例如此。但由于书写者(包括刻工)只擅长书写技巧而不通字义,竟将“暨”字误写为“既且”,导致读不通亦不知何意。如果是撰、书、刻一体,文义通畅,书写者和刻凿者定不会出此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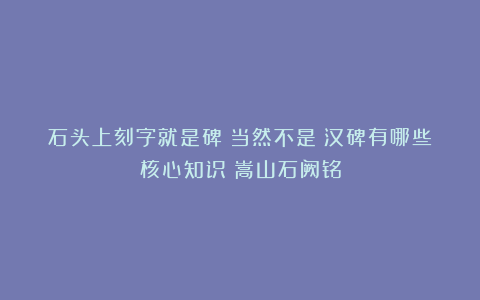
汉代的情况与南北朝和唐代不同。北魏的造像记和墓志,书法虽好但刻凿者文化水平低,常有缺笔漏字现象。而唐代碑版的书者多为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一代圣手,刻者有工匠也有名手,相传颜真卿就曾亲手刻碑。
从汉碑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类型:一是《张迁碑》类型,书写和刻凿者文化程度较低;二是北魏墓志铭造像记类型,书写无误但刻凿有误;三是隋唐碑版,书者文化修为较高,刻者错误较少。
在中国古代的碑刻文化中,撰文、书丹和镌刻三者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艺术整体。汉、北魏、唐代,各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展示了这一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汉代的碑刻中,如《张迁碑》,我们看到了一种朴拙而有力的风格。北魏的碑刻,尽管书写和雕刻的水平不一,但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至于唐代的碑刻,无论是书写还是雕刻,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
汉碑中的隶书,如《礼器碑》、《张迁碑》等,各具特色,难以简单地以“优劣”来评判。然而,《张迁碑》中的错讹,确实反映了书写者水平的问题。与此同时,其雕刻的浑厚朴茂,又显示了雕刻者的高超技艺。这或许可以作为沙孟海先生分类中“书劣刻佳”的例证。
三汉碑形制的定型
汉碑,作为中国石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可谓悠久而深邃。从最初简单的刻石,到形成具有特定形制和功能的碑,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艺术形式的演变,也映射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早期的草创期,石刻主要用于记事和纪念,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立石”、“刻石”、“石刻”,以及《汉书》中的“刻石记事”,都是这一用途的例证。这些石刻,多为简单的记述,形式上还未形成后世碑刻的典型特征。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碑”的定义——“碑,竖石也”,标志着“碑”这一概念的正式确立。而《西岳华山庙碑》中的描述,则进一步明确了碑的功能——刻记时事。
从实物来看,西汉时期的石刻,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等,多为横式,与后世的竖式碑不同。西汉末年的《麃孝禹碑》则是一个过渡性的关键物证。它虽然仍被称为刻石,但其形制已具有碑的特征,如小圜首、长方整饬、竖线界格等,显示出向碑的过渡。
东汉中后期,尤其是恒帝、灵帝、献帝时期,汉碑达到了全盛。这一时期的碑刻,具有了典型的碑的形制,如碑额、碑穿、龟趺、碑阴等,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