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难测。咱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诡事”,真真假假,搁在乡下的烟火日子里,总是带点人情味儿和说不清的凉意。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命运究竟谁说了算?有些故事你以为是鬼怪作祟,仔细琢磨,都是人自己心里的疙瘩。
那会儿是清朝末年,天下乌烟瘴气——老皇帝忙着割地赔款,一茬接一茬地糟心。京里头有大事,偏僻的小山村也逃不掉祸福。你要说百姓能过什么体面日子,倒不如说都在凑合。王家在村里不算显赫,好歹有仨儿子,也是苦出来的命。王家兄弟,老大老二踏实本分,认人夸句老实。有意思的是,老三——说实话,整个村子提起他都只摇头:吃软饭,怕吃苦,除了打瞌睡就会往锅里添饭。村里头常说:“王老三,油瓶倒了不挪窝。”一点不夸张。
话说回来,爹娘宠孩子那是一时心软,不想他越发像个没根草,日子也就如此糊里糊涂地过。可惜天不遂人愿,王家夫妇前脚没了,老大老二各自奔了自己的小日子,家就像入秋的枯藤,彻底散了。王老三这才知道,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可惜说归说,手里那点能耐,连买酱油的钱都抠不出来。
哥哥俩是实在人,看着自家老三这德性也不忍心,心里还幻想着,给这老幺娶个媳妇,兴许能把人带顺了。说是说,姑娘们谁愿意嫁给一个连自个儿都养不活的男人?托人说媒,是个有点名声的女儿都躲得远远的。看了个遍,最后才退一万步——托人说去寡妇家。
韩家就坐落在村边。韩若云,性子软,命更苦。头一回出嫁,夫家不幸早亡,她带着儿子东东回了娘家。可你知道,寄人篱下怎么都不是长久的事。家里哥嫂嫌她拖油瓶,恨不得早点另寻门第。机缘巧合,王家那边想娶媳妇,韩家的哥哥爽快做了主,韩若云也没什么异议:好歹有人家了,脚底终于有根。
新生活一开始,韩若云就发现家底比想象中还要薄,紧巴得透不过气。人能忍,她就拿出点小积蓄,帮着王老三拾掇了个杂货铺。开头总是难,可日子有时候还真像旧衣裳,缝缝补补也能过。王老三好像真转了性子,也上心起来,有了盼头,再不像从前只会嚷嚷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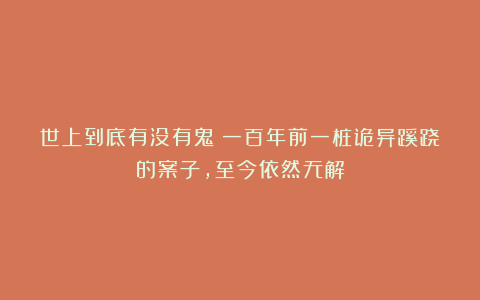
可是心里那点疙瘩,一直在。东东是上门的孩子,怎么瞧怎么别扭。王老三憋了一肚子不满,好容易自己有了儿子贵贵,眼里更容不下这“外头货”。不出所料,韩若云夹在中间,开不了口。她能说什么呢?娘不是石头做的,看着儿子挨打受骂,心一样似刀子割。不过这年月,女人有几个真能说了算?说来说去,还得自个儿扛。
东东最苦,说白了,他早早明白了“家不是归宿”是种什么滋味。王老三不让他读书,撂下一句“跟我做生意”。东东懂事,擦着鼻涕就去了,什么都不敢耽误。可再怎么勤快,王老三从来没一个笑脸。那孩子有时候,背着人抹眼泪,韩若云看见了,劝他一声“再忍忍,长大就不一样了……”但其实,她自己心里早凉透了。
村里有句闲话,怨不得。一天,东东忽然不见了。王老三一点不上心,淡淡地说,这孩子八成贪玩去了。韩若云嘴里倒苦水,一口气闹到快崩了。她拉着王老三,天一亮就到处找人,连野地都跑遍。后来,还是绕到自家杂货铺门外的枯井口,才把东东找到。唉,没人愿意复述,那味道混着泥腥,东东已经烂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若云魂差点没散,哭得没了人形。她有时也恨自己,怎么就硬不起心肠?可是老话的“天命”两个字,真能让人活得不是自己。死了一个儿子,这日子还能怎么过?可她不能丢下贵贵,只能拖着身子,和王老三一起搬到杂货铺里过。
说来也怪,从那时起,怪事接二连三。黑灯瞎火的夜里,王老三老是听见楼下有人走动的脚步声——那脚步轻飘飘,像是东东小时候,在屋里侧着身翻找糖罐的样子。外头风声嚷嚷,说老三心眼歹毒,狠心弄死了继子,现在报应来了。人言可畏,王老三却是真扛不住。他本也不是什么坚强的人,一来心虚,二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稳。韩若云见了,不过是叹口气。她或许想过去理论,可这一家子的苦水都吞进了肚子里。
没几天,王老三也不见了。人们寻来寻去,还是那口枯井——井里,这次横着的,就是王老三自己。两条命,而且都栽在一个地方。村子轰动,官府来了也查不出真相,问来问去只是摇头。尸身没什么伤,铺子里没打斗,家里人口单薄,更无旁人作案。案宗就这样一合,摘了顶“鬼神作祟”的帽子。凶案成了悬案,人没了痕迹,留下的只有井边荒草,还有夜里的风声。
后来这件事在村里传了很多年。有人说东东魂不散,缠上了王老三。也有人摇头叹息:王老三也不算坏人,就是混了点,可偏偏命不好,绷得太紧。夜里人走枯井边,老有人停步,远远瞅上一眼——谁都说不清,这枯井里头,真有鬼,还是只是人心太黑,照见了自己。
你要说世界上有没有鬼?不知道。但人要是活在亏心事里,鬼影重重也是自己给自己吓的。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鬼神,是自己的那点念头。你说,冤么?还是活该?这事,谁又能说得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