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河的湿气,是安丰县廨舍里抹不掉的底色。晨曦挣扎着透入值房低矮的窗棂,只照亮了案头一隅灰尘浮动的光柱,却驱不散那股子浸入木头纹理里的阴潮霉味。
刘主薄是安丰县正九品官员,埋首在堆叠的文牍山丘里,薄薄的官袍肩头,竟也隐隐洇出一圈深色的水痕。他袖口边缘磨得起了毛,指甲缝里塞着洗不净的墨渍与细小的泥点,如同河滩上被冲刷了无数次的碎石。
算盘珠子在他枯瘦的指下噼啪作响,单调得如同窗外屋檐滴落的积水声。他在算自己那份俸禄。月俸五石米,朝廷折钞发放,最终落到他手里的,是两张轻飘飘、墨迹都似乎带着敷衍的宝钞,统共两贯。
这点钱,莫说在官场上应付,便是养活他自己和县衙后头小院里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仆,加上偶尔接济一下乡下的远房穷亲戚,也是捉襟见肘。
他搁下笔,指尖捻了捻那两张薄纸,一股子廉价的油墨和朽木混合的气味钻入鼻腔。窗外的太皇河在远处低吼,浑浊的浪头拍打着残破的旧堤,声音沉闷地传进来,仿佛压在人心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值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带进一股裹着尘土和汗味的燥热空气。来人身材壮实,穿着簇新的茧绸直裰,腰间悬着巡检司的腰牌,正是本县豪强、兼着巡检职衔的丘尊龙。
他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靴子上的泥点在青砖地上印出清晰的痕迹,目光扫过刘主簿案头那两张刺眼的宝钞,嘴角牵动了一下,似笑非笑。
“刘主簿,辛苦!”丘尊龙的声音洪亮,震得小小的值房嗡嗡作响。他身后跟着个精悍的随从,手里拎着个看着颇有分量的青布包袱。
丘尊龙也不待刘主簿起身,径自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不堪重负地呻吟了一声。他挥了挥手,那随从立刻上前,将包袱轻轻搁在刘主簿的案头。包袱落在文书堆上,发出一声沉甸甸的闷响。
“一点心意,给主簿大人润润笔!”丘尊龙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昵,“今年雨水看着邪性,那几处老堤,顶怕撑不住。巡检司人手器械都备下了,只是这动员民夫、调拨草袋木桩的文书签押,还望刘主簿这边……费费心,催得紧些。早日动工,大家心里都踏实不是?”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丘尊龙的话语如同河堤上的土石,看似随意堆叠,却严丝合缝,堵住了所有查贪的缺口。什么“润笔”,什么“踏实”,不过是堤防加固的工程里,从那些砖窑、石料场又能吃进一大笔回扣的暗示罢了。
刘主簿抬起眼皮,目光在那包袱上停留了一瞬。青布的纹理清晰可见,里面硬物的轮廓棱角分明。他脸上没什么波澜,只慢条斯理地伸出手,指尖在那包袱上轻轻拂过,像是拂去一层看不见的灰尘。指腹传来的坚硬而冰冷的触感,让他心头那点因俸禄而生的寒意悄然退去。
“丘巡检心系桑梓,拳拳之意,下官感佩!”刘主簿的声音平缓,听不出情绪,“堤防事大,关乎阖县安危,自当从速办理。”
他顿了顿,话锋极其自然地一转,“听闻丘巡检在城西新置的庄子,今年麦子长势极好!风调雨顺,丘巡检福泽深远啊!”这话说得极有分寸,既留下了这个包袱,又点明了彼此都心知肚明的“福泽”。
丘尊龙哈哈一笑,声震屋瓦:“托赖托赖!到时新麦下来,定要请刘主簿尝尝头道面!”两人目光一碰,彼此都从对方眼底看到了那份无需多言的默契。又闲话几句河工土方、天气晴雨,丘尊龙便起身告辞,靴声橐橐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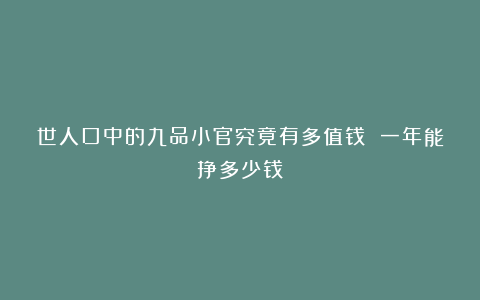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案头那青布包袱,无声地散发着诱惑。刘主簿枯坐片刻,终是起身,将那包袱塞进身后一个半旧书箱的底层,压在一摞发黄的旧档册下面。做完这一切,他整了整并无线头的衣襟,踱出廨舍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他背着手,看似随意地沿着街边荫凉处踱步。刚走到街角那株枝叶还算茂盛的老榆树下,斜刺里一个穿着体面酱色绸衫的中年人便快步迎了上来,脸上堆满了恰到好处的惊喜:“哎呀呀!刘主簿!这可真是巧了!刚还说去衙门口递个帖子呢!”正是城里“瑞福祥”绸缎庄的掌柜,姓钱。
刘主簿停下脚步,微微颔首,脸上挂着官场上常见的疏淡笑意:“钱掌柜,生意兴隆?”
“托主簿大人洪福!还过得去,还过得去!”钱掌柜搓着手,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极低,语速却飞快,“就是……就是上回那批江南来的新样苏缎,税关那边查验的手续,多亏了主簿大人您跟仓大使打了招呼,才顺顺当当过了。小号上下,感激不尽!这点小意思,给大人添个茶资,万望笑纳,日后仰仗的地方还多……”说话间,他那宽大的袖口仿佛不经意地往刘主簿袖边一蹭。
刘主簿只觉袖笼里微微一沉,滑入一张叠得方正硬挺的桑皮纸。那触感,薄而韧,带着纸张特有的微凉和摩擦感。他袖中的手极其自然地一拢,指尖一捻,便知数额不小,且是信誉极好的“汇通”钱庄见票即兑的银票。整个动作在宽袍大袖的掩映下,迅捷无声,如同掠过水面的飞鸟。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钱掌柜客气了!”刘主簿面上波澜不惊,只淡淡应了一句,“商货流通,乃本分。循章办事便好!”他微微颔首,算是应承了这份“茶资”和那未出口的“日后仰仗”。钱掌柜得了这句,如同吃了定心丸,脸上笑容更深,又连声道了几句谢,才躬身告退,脚步轻快地消失在街角。
袖中那张薄纸,却仿佛有了温度,熨帖着刘主簿的手臂。他并未立刻回衙,而是脚步一转,不疾不徐地出了南城门。城外,视野骤然开阔。暮春的风带着泥土和刚抽穗的麦苗的清新气息,吹拂在脸上,比城里那股子浊气舒爽得多。一片望不到边的麦田铺展在眼前,麦浪在阳光下翻滚,闪烁着诱人的、金子般的光泽。这光泽,比那两张轻飘飘的宝钞要厚重千万倍。
田埂尽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前,蹲着个皮肤黝黑的老农,那是中人老孙头。见刘主簿过来,老孙头慌忙起身,在衣襟上使劲擦了擦手,脸上挤出谦卑又热切的笑容:“主簿大人,您来啦!地都给您看好啦,就在这眼前,靠河湾那一片,五十亩整!土头肥得能攥出油!原主家急着用钱,价钱也实在!”
刘主簿没说话,背着手,目光沉沉地扫过那片在风中起伏的、青中泛黄的麦田。麦穗已灌浆饱满,沉甸甸地垂着,散发出一种令人心安的、粮食特有的甜香。他看得仔细,仿佛要将每一垄麦子的长势都刻进眼里。半晌,才缓缓点了点头。
“契书呢?”
“备好了!备好了!”老孙头忙不迭地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纸细心包好的文书,双手捧着递过来。契纸是坚韧厚实的棉纸,上面用浓墨工整地写着田亩四至、原主姓名、中人姓名。刘主薄三个字,作为新主,早已预留了位置。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刘主簿接过契书,展开。夕阳的金辉落在那微微泛黄的纸页上,也落在他瘦削的指节上。他伸出右手食指,探入袖中,准确地捻出那张“瑞福祥”钱掌柜塞来的桑皮纸银票。指腹划过银票边缘,触感光滑而微韧,带着钱庄印鉴微微凸起的纹路。他将银票递给老孙头,换过一支笔管粗秃的毛笔。
笔尖饱蘸了浓稠的墨汁,悬停在“刘主薄”三个字上方。一股墨香混合着泥土与麦苗的气息,钻入他的鼻腔。这一刻,值房里宝钞的朽气、丘巡检包袱的冰冷、袖中银票的滑腻触感……都奇异地沉淀下去。眼前只有这方方正正的田契,和田野里无边无际、涌动着生机的麦浪。
他深吸了一口田野里饱含生命力的空气,手腕沉稳落下。笔尖触到棉纸,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墨迹随之流畅地洇开,“刘主薄”三字跃然纸上。
远处的太皇河依旧沉闷地流淌,而那片已经姓刘的麦田,在暮色中沉默地铺展,麦芒在晚风里轻轻摇曳,指向灰蓝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