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带着毛人凤等一批忠诚心腹逃往台湾初期,制造了许多“间谍案件”。在1950年4月2日,一份岛上的报纸(因为质量不高,名字就不提了)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3月23日,数名高级军事官员被枪决,其中包括六名中将和十三名少将,他们都与共党有勾结。”
《台历史纲要》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从1949年到1952年,约有四千人被台当局以’匪谍’的罪名枪决,另外还有八千到一万多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而那些被秘密处决的人,至今无从统计。”
在1950年3月23日的枪决中,虽然六名中将被处决,但我们熟知的“密使一号”吴石中将和他的联络员“海鸟”朱枫并不在其中。吴石中将与陈宝仓、聂曦、朱枫等四位烈士,在1950年6月10日英勇就义。吴将军在临终时留下的遗言是:“两岸同根同源,这是血脉与民心的纽带。几十年后,我必定会回到故里。”
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并非电视剧《潜伏》中的吴敬中原型。实际上,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应该是吴石中将,而电视剧中的余则成原型可能是“海鸟”朱枫。对于历史人物是否在剧中出现,性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的生平轨迹是否有交集。
至于“密使一号”吴石中将是否是吴敬中的历史原型,以及余则成是否源自“海鸟”朱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通过这两位真实人物的捕获和牺牲,来分析电视剧中吴敬中与余则成的命运。如果将剧中人物放回真实历史中,他们是否会在潜伏与反潜伏的博弈中犯下致命错误?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史料中找出答案。吴石中将与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吴石之子吴韶成共同回忆并总结的《潜伏者归来·真实“余则成”的尘封记忆》一书中提到:“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在1949年2月解放军攻占天津之前,由吴站长紧急带上飞机,飞往广州。飞机上,他们被告知将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的成员,直接飞往台湾。余则成的故事从此画上句号,虽然他在台湾继续潜伏,剧集为观众留下了许多悬念,但其历史却一直在鲜为人知的角落里继续上演。”
在历史的真实版本中,保密局天津站的少将站长吴敬中(或称吴景中)被毛人凤亲自捕捉,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去香港探访时并未见到吴敬中,虽然他们是老同事、老朋友。吴敬中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史料中未曾留下任何记载,甚至同事们也无从得知他的下落。通过查看吴敬中的履历,可以得知毛人凤及蒋特组织抹去他历史痕迹的真实原因:吴敬中与蒋建丰、后来担任“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处理吴敬中的问题必须小心谨慎,即使他是潜伏者,也需绝对保密——如果处理不当,蒋建丰与郑介民的面子都难以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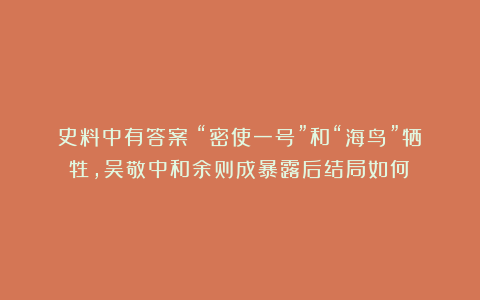
吴敬中消失并不令人意外,谍报工作本来就是在险境中舞蹈,每一步都充满风险。只要一丁点疏忽,就可能致命。吴石中将被揭露就是因为他身边的某些人发现了蛛丝马迹。南怀瑾的儿子南小舜曾回忆道:“基隆卫戍司令在拜访父亲时,讲到’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案的侦破过程。”当时的基隆卫戍司令透露,老蒋退台初期,情报机关每天晚上八点左右都会监听到密电信号,经破译发现,这些密电来自台北市吴石中将的官邸。于是,毛人凤立即组织精锐力量进行侦查,并选出一名看似迟钝憨厚的女特工潜入吴府。通过细致的监控和巧妙的潜伏,特工最终发现了吴石使用的微型电台。
潜伏者的生死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防范身边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眼睛。吴石中将虽谨慎,每晚锁好浴室门,但仍被特工机关成功发现秘密。即使再小心翼翼,终究无法逃脱被暴露的命运。余则成在《潜伏》中的谨慎,也面临着类似的隐患。他的致命弱点在于“心重手不狠”,尤其是在面对汉奸穆连成的侄女穆晚秋时,余则成的轻信与保护,给自己和组织带来了隐患。穆晚秋在剧中表现出不凡的特工潜质,而她通过调查与推测揭示了余则成的身份,种种迹象都表明她不简单。如果她真的有特工背景,余则成保护她无异于为自己埋下大祸根。
“心重手不狠”是潜伏者最大的忌讳。余则成对穆晚秋的轻信,最终成了自己潜伏事业中的致命隐患。当然,《潜伏》作为一部谍战剧,其剧情与真实的间谍世界有着巨大的差距。通过吴石中将与朱枫的暴露、被捕与牺牲,剧集与现实的差异显而易见。余则成在真实历史中的生存能力,也未必能够超过“鬼子六”郑耀先,他的潜伏之路,可能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潜伏》是一部精湛的谍战剧,《风筝》则通过更加沉重的后半部分展现了特工的真实困境。事实上,剧中嚣张的“军统六哥”郑耀先,比余则成更不适合潜伏。在特务头子如戴笠、毛人凤的怀疑与打压面前,郑耀先不去依附蒋建丰,而是盲目自信,最终可能暴露得更快。而像吴石中将、余则成这样的高级特工,正面临着同样的潜伏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