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龟兹回来2个月了,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整理这趟行程。除了记下的窟号,别的,什么都带不回来。记忆,是有欺骗性的。一个月前,用国庆假日的时间,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的官网上找图。黑白老照片,似乎唤起了一部分回忆。赶紧记下。
此图源于网络,后用ps拉伸调整,并用红字放大了一部分窟号
反复琢磨,没有可能一篇笔记就把克孜尔千佛洞全记录了。在不断的资料收集、整理、理解的巨大工作量下,先一个个窟来整理,或许较为理性。未来在世界某个博物馆参观看到石窟碎片时,也方便及时调取。
76窟
B0637
先来看位置。如今访问克孜尔石窟,我们没可能拥有一百年前德国人的机位。所以,反倒是黑白照片更清晰。上图红框部分就是75-77窟。
B0610
76窟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B0648
要命的是,翻遍了手机,没能找到拍76的门牌。只有拍了77的。做了一个今昔对比。
整理这份笔记,犹如在一团毛线中找线头。76窟或许就是我的“线头”,抓到了,就不可能放手。德国人当年给它取的名字叫——孔雀窟,记忆太深刻了。
# 孔雀窟
Peacock Cave,德文是Pfauenhöhle,因为这个窟的主室穹窿顶上有大量精美的孔雀羽毛,如今似乎还能看到一小片。
图源Wikipedia
图源Wikipedia
# 两个阶段&前室
76窟是克孜尔千佛洞中的早期石窟,经历过重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在其著作《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中提到“此窟最初是一座小型且无装饰的方形窟。相对位置显示出其曾有一间较深的前室,主室平面呈长方形,顶为覆斗顶,壁面涂有草泥层且刷白灰浆,但不绘壁画…… 主室的右侧部分在随后的改建中被拆毁……改建后的洞窟包括一间宽敞、充满装饰的大前室,其地坪低于主室地坪约50厘米。主室平面呈方形,顶为穹窿顶……”
考古学家辨析出了76窟的两个阶段。一百年前德国人走进这里的时候,还清晰地见到了保存尚好、还有家具的“前室”,今天我们如果能进去的话,可以看到考古意义上还留存着的须弥座。
这是一百年前德国探险队第三次探险活动期间拍摄的76窟前室,有大量的木质器具:
III7139
III7384
B0794
B0795
B0798
B0799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的雕像,如今都在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III8135
III8146
III8147
III8148
III8151
III7409
# 孔雀窟的主室
主室地面中心有一座预留岩体雕刻而成的须弥座。须弥座上可能原有一尊坐佛像(从B0797老照片中可看到此坐佛跏趺坐的腿部),位于穹窿顶下。
B0797
根据德国人发表的材料,该窟主室正、右、左三壁上绘有连续方格式佛传图。
图源Wikipedia
图源Wikipedia
根据下图黑白老照片比对时,会发现无法与上2张源于Wikipedia的拼图完全吻合。这可能是德国人拍摄的玻璃底片洗出来是呈镜面图像所致。再将其镜面翻转后,便发现完全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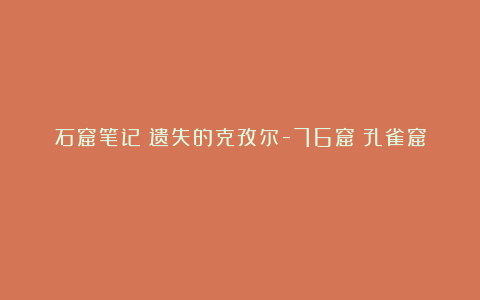
B0670
B0670镜面翻转
当年德国人将壁画切割带回后,收藏于原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并做了一个原壁画的“复制窟”(见下图),可惜后来因战争连带壁画一同被毁,今只剩下图像。
图源:翻拍《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P23,魏正中、桧山智美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格伦威德尔见到主室时,仅主室左壁保存相对完好。依据所收集的素材,中间一层可辨认的佛传故事图像题材有:
(1)出游四门
B0670镜面翻转-截取
(2)魔女诱惑
(3)降魔成道
那么,按这样看,左起第一铺漫漶不清的,大概就是“太子诞生”:
B0670镜面翻转-截取
此外,还有“涅槃”、“举哀”、“茶毗”等场景:
图源Wikipedia
这组佛传图意义非凡。还不仅仅是因为时间早,更要加上空间地域概念,位于龟兹地区-说一切有部影响之下的佛传图,其中的细节所对应的经典出处,与我们内陆其他地方所见的不同。这部分的论述,在《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一书P198-203有专门解读。
# 主室窟顶
主室的穹窿顶,是“孔雀窟”的由来,也是从美术角度来说最为精彩的部分,哪怕如今只留下一片羽毛,仍然令人叫绝。
图源Wikipedia
这个穹窿顶由八片扇形构成,每一面绘飞天,翱翔于孔雀羽纹之间。
穹顶周缘绘过去佛与诸天众像。
图源《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P148-149,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1995年8月第一版
# 唯一“幸存者”
经过德国的战火,此窟壁画在德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块壁画,现藏于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有一说是因为当年不知道这一片壁画应该拼在哪个位置,故一直留在库房,反而逃过一劫。
III8842
魏正中在书中提及它在原窟中的位置是“正壁与左壁转角处”。
关于这块壁画所呈现之内容与题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如因缘故事或说法故事。
例如:2020年,学者Satomi Hiyama,在其发表的论文《New Identification of the Mural Fragment fromthe ʻPfauenhöhleʼ (Kizil Cave 76, III 8842) 》提出一种可能性:第76窟主室后壁( 原文:on the rear wall of themain chamber of Cave 76,系每位学者对主室方向定义不同)的叙事场景未必均属佛传题材,而可能包含其他叙事主题,例如佛陀说法框架内的各类譬喻故事。
“佛陀身旁绘有五名持剑青年,其前方另有一跪姿男子。后者双手捧一篮状物(曾被误读为编织坐垫),其上至少可辨识出两个蛇头。此人眉头紧锁,似在表达不安情绪。场景中所有男性均裸上身,配饰璎珞披帛却无头光,应为普通印度民众形象。画面顶部点缀飘落的花瓣。此场景所有现存元素,均与《杂阿含经》第1172经所载‘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之喻高度契合。”(摘取自《New Identification of the Mural Fragment fromthe ʻPfauenhöhleʼ (Kizil Cave 76, III 8842) 》)
《增一阿含经·卷23》(引自CBETA)
# 最后:回到须弥座
B0797
最后允许我“卖弄”一些现学现卖的知识。考古学家可以从这个须弥座(图像与现今留存物)复原出坐佛的高度。
当我们把目光统统关注在76窟的壁画图像上面的时候,是否很容易忽略此窟原应有之聚焦重点?
看,德国人当年的复原窟,竟然也没有示意此处有一尊坐佛。
图源:翻拍《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P23,魏正中、桧山智美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让我们回到我这篇笔记重复参考的一本著作的封面图,来看一下,76窟的空间感和视觉究竟是怎样的?信众,应该在什么位置——
参考资料:
-
《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魏正中、桧山智美 著,附录 基弗尔-普尔兹、谷口阳子,王倩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
《New Identification of the Mural Fragment fromthe ʻPfauenhöhleʼ (Kizil Cave 76, III 8842) 》,Satomi Hiyama,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indo-asiatische Kunst,24·2020
-
除标注具体出处的图片,其余用【B】或【III】标注的图片均截取自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官网
( END )。
本文为个人学习笔记,除极个别个人推测思考之外,大量为参考已公开发表的研究著作,已在参考资料中列明。文中所用配图,除单独标注图源,其余均为本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