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中国山水画“师法自然”与“含道暎物”的创作法则,探讨近现代山水画家在面对自然对象时如何实现笔墨语言的有效表达。文章指出,传统笔墨程式虽具高度审美价值,但在直接面对现实景物的写生实践中常显局限。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绘画观念影响与表现现实生活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山水画家通过写生探索传统笔墨的转化路径,形成了“以古法写新境”与“以真景创笔墨”两种主要模式。通过对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代表性画家个案的分析,本文论证了写生不仅是造型训练手段,更是激活传统、生成新笔墨的重要机制。研究认为,近现代山水画的发展并未背离“师法自然”的根本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深化了“道”与“物”的互动关系,实现了笔墨语言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山水画;写生;笔墨语言;师法自然;含道暎物;传统转化;近现代美术
一、引言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根本法则,它确立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画家需以自然为师,在观察与体悟中提炼形象,最终将外在物象转化为内在心象。这一过程的核心媒介,正是笔墨。笔墨既是对自然形态的描绘工具,也是主体精神与宇宙之道相契合的载体,即所谓“含道暎物”(宗炳)。在传统文人画体系中,笔墨的传承多通过临摹经典完成,形成了一套高度程式化的语言系统。
然而,当山水画家走出书斋,直面真实山川进行写生时,传统笔墨程式往往难以完全应对复杂多变的自然景象。尤其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视觉经验与艺术功能的深刻变化,山水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传入带来了新的观察方法与表现技术;另一方面,20世纪中期以来“表现工农兵生活”“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现实主义要求,促使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描绘真实场景。在此背景下,如何将自然对象转化为具有笔墨美感的艺术形式,成为山水画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近现代山水画在写生实践中对传统笔墨的继承与突破。通过梳理“师法自然”理念的历史演变,分析代表性画家的写生实践,揭示其在“以古法写新境”与“以真景创笔墨”之间的探索路径,进而阐明写生作为传统转化机制在近现代山水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二、“师法自然”的历史逻辑与笔墨程式的形成
“师法自然”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新观念,而是贯穿中国山水画史的基本准则。早在南朝宗炳《画山水序》中即提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强调画家应亲历山水,用心观照。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字,更精辟概括了艺术创造的双重来源:既要有对外部世界的细致观察,又要有内在心灵的消化与升华。
在长期实践中,历代画家通过对自然的反复体察,逐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笔墨程式。如五代荆浩隐居太行,写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终创“皴法”之先河;北宋范宽卜居终南、太华,岩岫巉绝,林麓苍郁,遂有《溪山行旅图》之雄浑气象。这些经典作品皆源于对特定地域地貌的深入观察,其笔墨语言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
然而,随着文人画传统的成熟,笔墨逐渐从“再现自然”转向“表达心性”,临摹古人成为学习绘画的主要途径。元代以后,“复古”思潮盛行,赵孟頫倡“作画贵有古意”,董其昌标举“南北宗论”,皆强调师承谱系的重要性。至清代“四王”,几乎以摹古为宗,笔墨程式趋于固化。此时,“师法自然”虽仍被提及,但更多是作为理论前提而非实践常态,画家往往“以古人为师”多于“以造化为师”。
这种倾向导致笔墨与真实自然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脱节。当画家面对未经程式化的现实景物时,常感无所适从。因此,恢复“师法自然”的实践传统,成为近现代山水画变革的重要突破口。
三、写生作为传统转化的机制
20世纪以来,面对西画冲击与时代需求,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写生,试图重建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批评院体画“萎弱柔媚”,主张“合中西而为画新纪元”;徐悲鸿则大力推行素描写生,强调“致广大,尽精微”。尽管其方法带有明显西化色彩,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画家重新走向自然。
在这一背景下,山水画家的写生实践呈现出两种典型路径:一是“以古法写新境”,即运用传统笔墨程式描绘现实景物;二是“以真景创笔墨”,即根据具体对象创造新的表现语言。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构成互补的转化机制。
1. 以古法写新境:黄宾虹的“浑厚华滋”之路
黄宾虹(1865—1955)是传统笔墨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年尤重写生。其写生稿多为速写式勾勒,不求形似,重在记录山川气脉。他主张“画有三要素:曰笔、曰墨、曰章法”,强调笔墨本身的独立价值。在写生中,他并不机械照搬对象,而是以“五笔七墨”之法加以提炼。如其黄山写生,虽取实景,然用笔圆浑,墨色层层积染,终成“黑、密、厚、重”的典型风格。黄宾虹的实践表明,传统笔墨并非僵化教条,只要理解其内在理法,便可灵活运用于不同对象,实现“古法”与“新境”的融合。
2. 以真景创笔墨:李可染的“为祖国河山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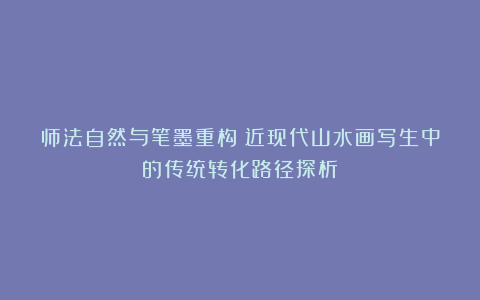
李可染(1907—1989)则代表另一种取向。他早年受西画训练,后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致力于打通中西。自1954年起,他多次赴江南、川蜀、桂林等地写生,明确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其写生作品如《苏州拙政园》《漓江胜境图》,虽保留水墨材质,但在构图上吸收焦点透视,在光影处理上借鉴明暗法,同时创造“逆光山水”新样式。其用墨浓重,善用积墨法表现山体体积,笔触坚实有力,极具现场感。李可染的探索证明,面对真实自然,传统笔墨可以被解构、重组,从而生成新的视觉语言。
3. 心象与物象的交融:傅抱石的“散锋破笔”实验
傅抱石(1904—1965)的写生实践更具主观性。他主张“一切技法皆从对象出发”,在写生中大胆创新。其最具代表性的“抱石皴”,以散锋破笔横扫竖抹,笔势奔放,墨色淋漓,既能表现南方山林的苍茫湿润,又充满激情与动感。如《漫游太华》《雨景图》等写生作品,虽源自实景,然笔墨自由挥洒,物象几近抽象。傅抱石的成功在于,他并未抛弃笔墨本质,而是将书法性的用笔与写意精神推向极致,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四、写生背后的观念转型
近现代山水画的写生实践,不仅改变了创作方法,更引发深层的观念转型。
首先,“自然”的内涵发生扩展。传统“造化”多指理想化的山水意境,而近现代写生则强调具体地域的真实风貌。画家开始关注城市景观、工厂矿山、农田水利等新题材,如钱松喦《红岩》、石鲁《山区修梯田》,皆将革命圣地或劳动场景纳入山水画范畴。这种转变使山水画从文人雅趣走向公共叙事,拓展了“师法自然”的边界。
其次,“道”与“物”的关系被重新诠释。“含道暎物”不再局限于个体隐逸情怀的寄托,而被赋予时代精神与民族意识。李可染称其写生是“为祖国河山立传”,傅抱石绘《江山如此多娇》象征国家气象,皆体现出山水画功能的公共化转向。笔墨不再是避世的工具,而成为建构民族视觉认同的媒介。
再次,写生本身成为创作方式。传统山水画多为“腹稿”经营,写生仅作素材积累;而近现代许多作品直接由写生稿加工而成,甚至保留写生的即时性与生动感。这种“写生即创作”的模式,打破了临摹—创作的二元结构,使艺术生产更加贴近现实体验。
五、结语
近现代山水画的发展,并未背离“师法自然”与“含道暎物”的根本法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面对西方影响与现实需求,山水画家通过写生实践,探索出传统笔墨的更新路径。无论是黄宾虹以古法写新境的内敛深化,还是李可染以真景创笔墨的外向突破,抑或傅抱石心物交融的个性表达,皆表明笔墨语言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写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既是连接自然与艺术的桥梁,也是激活传统、催生新质的机制。通过写生,山水画重新确立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避免了因程式固化而导致的艺术僵化。同时,写生也促使画家反思笔墨的本质——它不应是封闭的符号系统,而应是开放的、可生长的语言。
当代山水画的发展,仍需继承这一传统:在尊重笔墨规律的基础上,持续深入自然,回应时代命题。唯有如此,山水画才能真正实现“笔墨当随时代”(石涛)的理想,在古今中西的对话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与艺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