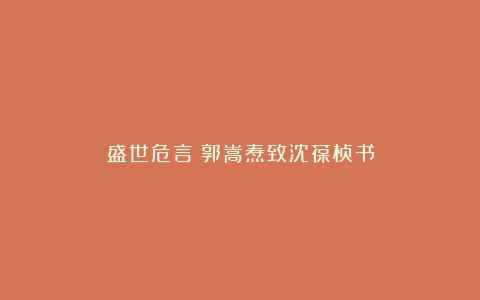郭嵩焘致沈葆桢书
昆三见示郭筠仙与文肃公书札一巨轴[帙]。皆外间所未尝见,而《养知书屋集》所未尝刊者,真同光间佳史料也。兹甄录数书(函),皆光绪元年筠仙出使英国前后所作者。一函云:
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
除日奉读赐书,并蒙宠颁炭资,深感懃懃垂注之盛心,眷德勤施,至周以渥,服膺曷已。敬諗履端笃祜,播闿宣猷,伏增祝祷。
嵩春一官逶迤,自度洋务粗有所见,思稍尽斡旋之力。窃以为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以制其鹗张之气,求因应之宜,而力争先着,以杜其要挟之心。传曰:“凡事豫则立。”而与外人相接,理不壮即气不充。京师士大夫务为虚侨,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视前二十年之见解无以易也。
方见各口通商十六,内达汉江,洋人实绾其利权。沿海机器局及学馆,洋人实司其训课。谓宜视彼所长而效法之,视彼之足为吾利病者,而求所以御之,一切内自毖焉,而引以为耻,未尝不可及时图功。故日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殆未易一一为今时士大夫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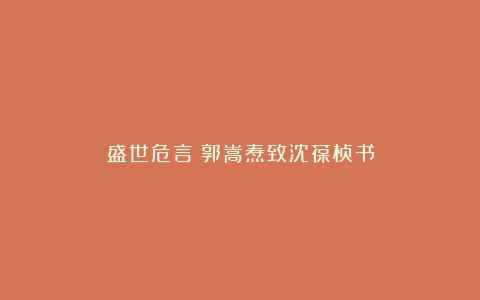
滇案本易理处,徒为议论所持,濡延至今。倭人近与朝鲜构难,其蓄谋已久,理处较难,而所以自处之道,固有未尽者。租界免厘,为患甚巨,赫总税司议上数万言,通中外筹之,大致合华商与洋商捐税为一例,合各国通商条约为一例,合各口商务、政务及词讼为一例。而析分此三者,疏陈其利病,各为四议,上者不能行,则行其次者。其论甚精,所见亦至深远,然行之不得当,则利在外人,而国家适承其敝。鄙意外而通商各省,内而驻京各国公使,均应知照会议,其间亦尽有各国不愿行者,必俟询谋佥同,而后酌择其可行之,此尤宜及早会商者。滇案或有牴牾,则前者贸然允之,今者又将贸然行之,鄙人所不敢知也。
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也。武穴之煤厂,兴国之铁矿,肇始湖北,为天下倡,近始具奏,喜慰无量。而睹鄂抚分解海防经费一咨,宣述盛意,以北洋方造办兵船,推以与之,廓然昭示大公,而又切当情事,使防海纷纭之议,至今乃有归宿处,斯为明通公溥之量,无愧古之贤者,为之额手称庆。禹生抚闽,岘庄督粤,殆亦沿海一时之盛矣。手肃申谢,敬敂崇安,无任驰仰。嵩焘顿启。正月初十日。
黄濬评:
函中所云“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一段,实为言外交者之秘钥。盖中国未尝无讲外交之人才,而“去猜嫌之见”五字最难。
当时国人见解,恒以为各国皆日夜协以谋我,而累次败衄之馀,又皆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悲。于是虽迫不获已,强颜与异族周旋,心中实日夜猜之嫌之。此种心理,甲申、甲午两役,愈经挫折,怨毒之心愈甚。至庚子,则公然降谕与列国宣战。虽曰妖后昏嚚,实亦举国对外人积蓄猜嫌之潜意识一旦暴发也。
筠仙所谓“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之义,彼时上下皆未能领会。而筠仙犹恐其以礼自守之说或有流弊,故其下文又日,“一切内自毖,而引以为耻,未尝不可及时图功,故日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其言盖完全以自己反省,自己充实,为唯一之外交制胜策。惜乎,当时朝士之不足语此也。筠仙于中日争端已见其微,其判断曰:“蓄谋较久,理处较难,而所以自处之道,固有未尽者。”此等敏锐公平之言,至今可为龟鉴。
【原题:郭嵩焘使英前后致沈葆桢书;录自《花随人圣盦摭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