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上的巨大封土
时间还要回到2021年8月20日,大墓所在的窝托村村民反映称,最近连续一个多月,每晚都有陌生人驾车在村里游荡,他们头戴带灯头盔,携带拉杆、辘轳等物件,行踪诡异。警方接到情报后高度重视,立即展开暗中侦查,发现这伙人每晚都会在古墓附近停留数小时,携带专业盗墓工具,且现场已出现新土、探眼和伪装盗洞。
文保部门的专家核查后惊呼,盗掘者已逼近主墓室边缘,一旦墓室被打通,里面的珍贵文物将面临被盗流失的灭顶之灾,而且珍贵文物到手后,嫌疑人将立刻四散跑路,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于是,为保护大墓不被破坏,并力求将盗掘分子一网打尽,警方决定立即收网,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这场跨越数月的盗掘与守护之战,最终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但盗掘行为对古墓结构造成了严重损坏,历史、考古与艺术价值都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座大墓为何会被盗墓团伙盯上?
这座被盗墓分子盯上的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西部大武镇窝托村,当地群众称为“窝托冢”“驸马冢”“相公冢”,并认为墓主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齐上大夫、稷下先生淳于髡。
1978年,胶济铁路东风站扩建,工人从封土堆取土时挖出了一些青铜器,后经过考古部门勘测,土堆下面分布有1座主墓和5个陪葬坑,而且均未被盗!5个陪葬坑由于附近居民经常取土,日积月累,距地面越来越浅,考古人员勘测时只有半米深左右了,出于文物安全考虑不得不进行了发掘。附近老百姓知道情况后,还开玩笑地说“要早知道的话我们就用锄头刨出来了”。而主墓室限于当年科技考古手段有限,恐不能有效保护出土文物,而没有发掘,这才让不少不法分子惦记上了。
5个陪葬坑经发掘表明:1号坑为器物坑,随葬品主要是礼器和生活用具;2号坑为殉狗坑,是5个坑中最小的一个;3号坑为兵器仪仗坑;4号坑为车马坑;5号坑为兵器和器物坑。这5个陪葬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银器、铅器、漆器、骨器等12100余件,其中的矩形铜镜为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还有鎏金龙凤纹银盘、鎏金熏炉、铜骰子等,都堪称稀世珍品。
齐王墓五号器物坑龙纹大方镜
(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矩形铜镜。长115.1cm,宽57.7cm,厚1.2cm,重56.5kg。形体之巨大,纹饰之精美,为历来著录和考古出土的铜镜之冠。)
(下方的龙凤纹鎏金银盘,经专家考证为秦代器皿。该盘口径37cm,高5.5cm,重1705g。外底刻“御羞”铭文,表明其为秦代帝王御用食器。盘内底錾刻三条盘龙纹,纹饰全部鎏金,形成黄白对比,被视为唐代“金花银器”工艺前身。铭文“三十三年左工□名吉”经考证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刻制,“左工”指秦代左工师监造。铭文中重量、容量经多次校刻,采用战国三晋地区计量单位,为研究秦代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该盘为全国唯一刻有秦代纪年的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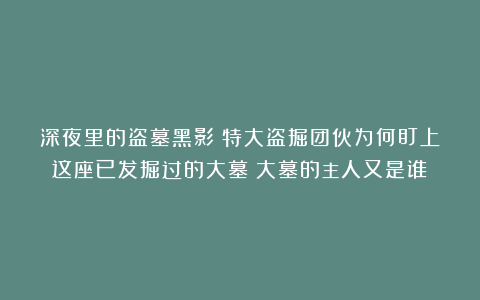
(以上图片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霍宏伟:镜中之王:淄博西汉齐王墓器物坑龙纹大方镜品读 )
除了发现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矩形铜镜,在陪葬坑里还发现了14件青铜鼎!关于青铜鼎的使用,古代有着明确的等级规范。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而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却陪葬了14件青铜鼎,这一罕见的现象让当时的考古人员一时也无法解释。随后的研究表明,这批青铜鼎的形制雷同,大小却并不一致,可分为七款,每款各有两件,可形成7个一组的组合。也就是说,这14件鼎应当是两套,不过7鼎的组合也表明墓主人应当是诸侯王一级的人物。
整个墓葬规模宏大!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封土高32米,南北200米,东西250米。墓口长约 42米,宽约41米,墓室深约17—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出土的器物和墓葬规模显示,这个大墓显然不是战国中期大夫级别的淳于髡能拥有的。
究竟是谁修建了如此规格的墓葬?
为了确定墓主人身份,考古队员对出土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确定一号陪葬坑中,不仅存在具有战国遗风的器物,还有一大批具有西汉初年特征的器物,表明这座大墓应当是西汉墓。
随后,考古队员又在青铜器上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了词:齐大官。大官即太官,是汉代少府的属官,主管宫廷膳食,其中的齐指的应当是齐国。这样的发现,令考古队员惊喜不已。这个大墓的主人是汉代齐国的哪位齐王呢?
刘邦建立起大汉王朝后,为稳固天下局势,分封诸侯,他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封地便在今天的山东淄博。西汉初年,同姓齐王共传有六代,他们分别是齐悼王刘肥,高祖六年 (前201年)至惠帝六年 (前189年),在位13年;齐哀王刘襄,惠帝七年 (前188年)至文帝元年 (前179年),在位10年;齐文王刘则,文帝二年 (前178年)至文帝十五年 (前165年),在位14年;齐孝王刘将闾,文帝十六年 (前164年)至景帝三年 (前154年),在位11年;齐懿王刘寿,景帝四年 (前153年)至武帝元光三年 (前132年),在位22年;齐厉王刘次昌,武帝元光四年 (前131年)至武帝元朔二年 (前127年),在位5年。这六位中哪一位才会是这座墓葬真正的主人呢?
考古队员分析后认为,有能力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墓的齐王,仅有最初的三位,也就是刘肥、刘襄和刘则,这三位齐王在位时期正是西汉齐国最鼎盛的阶段。由于文献明确记载首代齐王刘肥墓在临淄城东;第三代齐王刘则无子嗣继承王位,封地被汉朝中央掌管,因此刘泽死后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只有齐哀王刘襄符合条件,他在位时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具备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实力。因此,专家推测这座大墓是第二代齐王刘襄的墓。这位有着巨大规模地下世界的齐王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历史人物呢?
铜骰子学名叫做博茕,投焭(qióng),是古代人玩“六博”游戏的关键棋具,作为中国博戏中六博之一,被视作中国博具之祖,在春秋战国末期已较为流行。)
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刘恒为安抚刘襄,将吕后割走的三郡归还齐国。但就在这一年,刘襄突然去世,《史记》《汉书》仅以 “齐哀王薨” 四字一笔带过,连 “病逝” 的记载都没有。按史料推算,刘襄去世时仅22—25 岁,且史书中从未提及他身患疾病。史家王成胜在《汉初宗室死亡疑案考》中直言:“刘襄之死绝非偶然——文帝需解决’入继合法性’隐患,而有诛吕首功、宗室号召力的刘襄,是必须消失的障碍。” 这种猜测并非无稽之谈。刘襄若活着,其 “刘邦长孙” 的身份始终是刘恒皇位的潜在威胁,而刘襄死后,齐国势力逐渐分化,文帝的皇权才得以稳固。
如今,临淄窝托村的汉齐王墓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仍在诉说着墓主生前的权势。但再多的陪葬品,也弥补不了 “帝王梦碎” 的遗憾。
刘襄有勇有谋,以雷霆手段匡扶刘氏社稷,却因政治格局的制约抱憾而终。这位悲情的齐王,用 “高开低走”的短暂一生见证了汉初宗室、功臣与外戚的复杂权力纠葛,也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关于机遇与宿命的深沉思考。他的人生悲剧不仅揭示了封建时代权力游戏的残酷,也告诉我们有时功劳与能力,反而会成为致命的 “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