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13级小朱同学来信:
“我看到语言与文化课的第二章内容里有’语言制约认知’,我想提前提一个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希望可以在之后那节课上得到解答。
“之前我看过一个TED,名字叫做《你存钱的能力跟你用的语言有关?》。从提出’为什么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看起来相似的国家间,国民储蓄习惯差别如此之大’这个思考开始,讲者提出,使用不区分将来时态的语言的国家,比使用有将来时态语言的国家,平均存钱能力强很多(数据也真的是如此)。因为将来语态会迫使我们把’将来’与’现在’区分开来,从而让我们在’现在’为’将来’付出得更少。
“他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证实,还可以推广到吸烟上,因为吸烟可以看作是一种负向储蓄(因为储蓄是牺牲现在来使未来更好,而吸烟是用以后的痛苦为代价而获得现在的快乐),而数据也正好说明,在使用不区分将来时态语言的国家,吸烟的人比区分将来时态的国家少很多。
“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新颖的,但是同时我也存在疑问。这些现象是应该看作语言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环境呢,还是我们的文化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环境,并且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语言呢?语言和储蓄之类的问题,是真的有因果联系,还是因为碰巧是同一个自变量的两个因变量而又有了联系呢?
“我非常希望能得知老师您的想法,我对于语言到底有多大的功能,能影响我们到什么地步十分好奇,同时我对于这个新颖的观点也十分感兴趣。”
我对小朱同学说:“很高兴你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不是’课外’的问题,而是课内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语言和存钱能力的“文化相关性”
2013年,经济学家凯斯·陈发表论文谈语言与储蓄行为的关系,题目是《语言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来自储蓄率、健康行为和退休资产的证据》。他发现,使用不区分将来时态的语言,如中文、日語等,这样的国家,居民储蓄率较高;而使用有将来时态的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这样的国家,居民储蓄率相对较低。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什么来呢?
1. 语言的两种时间形态:“今明分离”vs“今明一体”
一种语言,明确区分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它会潜意识地强调“将来”与“现在”的分离。反之,一种语言表达将来事件时,使用现在时或上下文暗示,则会更倾向于将将来视为现在的延续。
语言形态上的“今明(将来)分离”,或“今明一体”,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从而影响决策,影响储蓄行为。
2. 语言形态中的“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
“今明分离”的语言人,其意识中的“将来”被语法化为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时态,这会在心理上拉大“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距离,更倾向于将将来视为“遥远的”或“不确定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估值低于当前的收益,时间的折扣率高,于是更看重当前消费,减少储蓄;另一方面,当“未来”显得遥远、陌生时,人们更难与未来的自己共情,从而更不愿意为“那个陌生人”牺牲当前的享受。
“今明一体”的语言人,其意识中的“将来”和“现在”在语言表达上更接近,心理距离更小,这会促进“将来”与“现在”的心理融合,人们更容易将“未来的自己”视为“现在的自己”的延续,从而更愿意为未来投资,为未来做准备。由于时间的折扣率低,也就更愿意储蓄,而且在健康行为上也更具“未来导向”,更少吸烟、更注重健康、更早进行退休规划。
3. 语言形态中的“时间人格”:准备型人格vs不备型人格
这样看来,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模具”。我们如何“说”时间,会影响我们如何“想”时间:是与未来一体,做好充分准备,还是与未来分离,满足于当下?时间在语言的建构下人格化,型塑我们的“时间人格”。
一种语言的“将来时”会“提醒”你“那是将来的事”,合理化你只顾眼前的想法,塑造你的不备型人格。
而一种没有“将来时”的语言,会引导你规避各种短视行为,把未来视为“现在”的自然延伸,从而自觉为未来做各种准备,塑造你的准备型人格。
二、中文的“时间人格”:整体思维
中文是一种很少形态变化的语言。中文从“根”上就藐视对事象的刚性切割,秉持万物连通,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
汉语虽然也有“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的表达,但这些表达是以词汇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表达不是必需的。当一个人说“他来了”,听话人可以理解为他已经来了(过去时)或他就要来了(将来时),这说明在汉语思维中,虽然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本质上并不严格区分。
在中文里,任何分析(例如字与字的析断、功能与功能的析断)都不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具有“可断可连”的灵活性。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在一个整体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一个过程。在一个句子中,各个句段也都是相辅相成,互文一体的。这也是我们汉语的句子为什么总是喜欢用逗号的原因。
中文的逗号既承接了上文的辞气,具有充足的铺垫,又启示了未竟之意,为下文做好了准备。这样的逗号,采用了西式标点的形式,其实已经不是西方句法相对于动词中心的结构标记,而是传统中文句法的停顿标记,呼吸标记。
相对于这样的“逗号”,中文的句子概念就不是一个时态切割的概念,而是一个有头有尾鱼贯而入的叙事概念。每一个过往句段,都承先启后,以柔软的身段“接住”前段丰富的信息,延伸出新的信息,为后续句段的语义和节律做好了准备。这样的“首尾相衔”,早已逸出了西方句法单位焦点透视的向心主义逻辑,而独树中文句法单位(句读段)散点透视的顺序主义逻辑。
这样一个“今明一体”的单位,已经不是西方“今明分离”意义上的“一句话”(a sentence)单位,而是中文整体叙事的“一件事”单位,一个意尽为界的单位。这里的“意”,就是句子的表达功能。中文句子以意尽为界,就是特定表达功能之完足为界。
同学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文学语言,我们的网络聊天,句号的使用大都是很主观的——不是结构上的“自足”让我们打句号,而是功能、意义上的“自足”让我们打句号。而这个“自足”,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前后关联范围的理解。这样自由裁量的范围,让一个人的主体意识自由驰骋,其留下的句号,是远非西方语言的sentence范畴能够理解和分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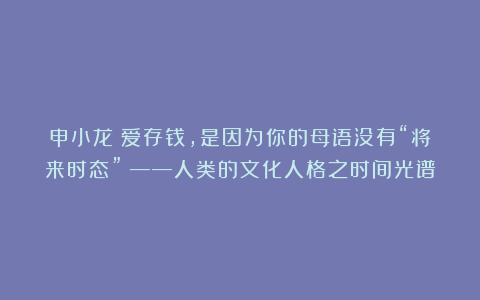
由于把一切看作一个过程中的“顺序”,而非孤立的片段,我们自然会为时间的变化、过程的发展做好准备。这就是中国人储蓄高的思维路径。
由此我们也会明白,在没有“将来时”的中文里,会有这么多成语,告诉你竭泽而渔、焚林而田、杀鸡取卵、饮鸩止渴、苟且偷安、急功近利、螳螂捕蝉……是多么鼠目寸光。这些“金句”不断在劝勉我们,要积谷防饥,要居安思危,要未雨绸缪,要磨砺以须,要蓄势待发,要有备无患,要防患未然,要目光远大,要为未来而不懈准备。
三、人类文化人格的时间光谱
在重视准备的时间人格上,中文和西文的对立并不是极致对立,这从欧洲语言和美洲霍皮语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来。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对此有深入的论述。
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欧洲语言的句子以动词为核心,所有的句法单位都被设定在相对于核心动词的关系位置上,切割性很强。欧洲语言的三时系统就是一种切割。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指出,三时系统的切割完全是人为的,人类对真实的时间过程的基本区别其实只有早和晚。而在这个不断由早而晚“渐渐远逝”的过程,其本质正是因“今明一体”而不断为未来积累能量,充分准备的过程。
沃尔夫对美洲印第安霍皮人的语言和文化做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霍皮人的时间观是“序数”式的。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按日子的周而复始,切割性地计算天数,将时间的天数看作一个集合体——“十天”就像“十个人”那样由个体堆积而成。霍皮人是按同一个日子的依次再现来作时间运算,就像用同一个人的连续访问次数来计算人数一样。
这种“序数”式的计算方式便于进行准备。因为孤立地看,人们不能通过作用于一个人而达到作用于几个人的目的,但通过计算同一个人的访问次数来做运算,人们就能够做好准备以影响这一个人后续的几次访问。
这种“序数”式的时间观注重事件的现时准备性,通过在一个现实情景中工作,将现实情境中一些既明显又神秘的印记导入未来,由此,作用于未来事件。
“序数”式的时间观又注重事件的重复性,认为事件的发展在于不断地重复。重复所形成的“序数”,积累和延续了事件的能量。这又是由霍皮语的型式决定的。
沃尔夫认为,那种来自无数小的冲动的积累性的价值感,在欧洲文化中被一种客体化空间化的时间观给淡化了,而在霍皮文化中则被一种持续性的、将事件视为在不停中“渐渐远逝”的主观思维方式所提升了。
在欧洲文化看来,时间是在一定空间内离我们而去的运动,因而持久不变的重复似乎是将它的力量分散在那个空间的一长串单位中,被浪费了。而在霍皮文化看来,不是时间经过客体化而消逝,而是已完成的事件在“渐渐远逝”。重复对于时间可能不重要,但对于事件却是一个积累力量的方式。
持久不变的重复把看不见的变化贮存起来,使它保持在后来的事件中。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我们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比过去更成熟一些,但他不是换了一个人。他带给我们的是“昨日”印象,而非“他日”印象。
沃尔夫就是这样,从霍皮语的“序数化时间”进入霍皮文化的过程化认知,将霍皮族村落文化中求雨和祈丰收的礼仪舞蹈中“持久性重复”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在霍皮语和霍皮人短短的,像活塞一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千万次重复的舞步之间,找到了一种文化的结构通约。
从沃尔夫对欧洲语言和霍皮语的时间观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化人格在“准备”维度上的两个端点。
1. 高准备人格:认定时间单位的序数本质,一切都在变化流逝的动态过程中,都由前期积累的能量推动演进,没有静止、孤立的时间单位。
2. 低准备人格:认定时间单位的基数本质,一切都是静止的、可切割可分析的。即使是抽象的东西,也可以在虚拟的结构框架中切分和静置。因此自然过程是不重要、不需要畏惧的。人为赋予的逻辑框架才是事物的本质。
霍皮语在高准备一端,欧洲语言在低准备一端;两端之间,是中文的合适的位置。
由此,人类文化人格在“准备”维度上呈现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
中文不否定分析,也愿意进行分析,就好像中文可以用非常欧化的方法表述那些需要严格规制的内容。
但中文始终意识到,把事物分开来只是一种便捷的方法,一种工具理性,它不能僭越事物的普遍联系本质。
任何一个分析单位,如果它缺乏弹性,缺乏单位之间的互文性,缺乏语境的默契,它就不是一个“活体”,而成了一个“死体”,失去了生命力。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语法那些范畴,用在中文文法分析上,都会画地自限,肘手炼足,最终“尸横遍野”……
回到小朱同学的提问:“语言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环境呢,还是我们的文化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环境,并且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语言呢?语言和储蓄之类的问题,是真的有因果联系,还是因为碰巧是同一个自变量的两个因变量而又有了联系呢?”这个问题简单回答比较容易:
由于现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范围的数据支持,所以语言的确有可能通过细微的认知机制影响经济决策。
但即使已有的研究已经控制了不少变量,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否认影响储蓄行为的其他经济、文化、制度因素。例如东亚文化普遍强调节俭、家庭责任,这可能是东亚地区人们储蓄率高更直观的原因。
说到底,即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控制更多的变量,语言和储蓄的单一因果关系还是难以完全确立。而在语言这里,“将来”概念的表达,从词法,到词汇,再到句法,人类语言的状况是非常复杂的,难以一刀划开两个阵营。
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许多探讨,深入下去,都在这样一条科学性与人文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拉扯”地带,戛然而止。要找到一条普遍适用的“铁律”,几无可能。
我们只能这样说:
从群体发生(文化起源)来说,语言与文化是相互塑造的关系;而从个体发生(个人成长)来说,语言决定文化。
这个回答同学们一定觉得很“抽象”,但已经是目前最具批判性,也最具阐释力的答案了。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
编年目录链接(九)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