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当每天早晨沈巍以一个流浪汉的形象,出现在白鹤的街头时,是他血槽接近危险临界点的时候,就像《天龙八部》里的天山童姥一样,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用他的放大的声音与赤膊上阵的肉体来应对激怒他的蓄意挑衅。
那些挑衅他的人,正如我们上回分析的一样,真正的目的不是挑战一个流浪汉,因为很明显,他浪迹街头26年,并没有人来骚扰他,看起来流浪时期是他最为脆弱的时段,反而他安然无恙,波澜不惊。
这根本原因,那时候的他是一下真正的流浪汉,他身上所通联着的能够进入高层的暗道(虫洞)尚没有凸显出来,不具有吸引眼睛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他被忽视,忍受着无边无际的孤寂。而现在的他不同了,他的身上有着牵连着高端的能量,挑战他,能够搏得关注,那些挑衅者,其实挑衅的是他身上的高端冰山底座。
沈巍在早上,对着那些挑衅他的人,揭示出他们的实质:“你们地位这么低下,你们真正的谁也斗不了,只能跟我来搅局。”
这是沈巍之前曾经说过的“你们是底层人,也只能欺负底层人”的实战翻版。
这就是沈巍难以割舍他的流浪生存期间的现场场景而导致的必然的困顿。解开这个困顿,成为沈巍粉丝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最常规的解决办法,就是另觅一个独家小院,能够控制人员的进入,形成一个相对宁静的活动空间,容纳沈巍在这个空间里,继续他的文化输出。
沈巍的跟班前一阵子一度宣布已经找到了一个小院,一时,沈巍的网友奔走相告,但实际上,沈巍并没有相中这个新的草庐,而是选择了苏、沪交界处的新胜桥下。
今天新胜桥下的唯一剩下的空间,又堆来了用着防汛用的木头与竹子,当沈巍看到这些不断蚕食他在桥下的活动天地的时候,一定会联想到孔子周游列国时到处受到驱赶的命运,而乐观的沈巍,只是举重若轻地谈及了他自己的命运,就像孔子也乐于调侃自己,把自己比喻着丧家狗一样。甚至在孔子暮年,他时常会提及他在陈、蔡游学时被驱赶的弟子,而这时候,这些陪伴着他度过最艰难岁月的弟子,已经基本不在他的身边了。
人到暮年,回忆那些最艰难时期的身边的人,是最容易产生依恋与怀旧情结的。
这一次,沈巍逐渐召唤出2019年高科的老战友,把他们悉数招到自己的身边,鸳梦重温,也是因为这些高科老人,在他第一次爆火之后进入低谷期的苦涩时光里,给了他不同形式的慰藉。他也知道这些人中,有人黑过他,盘过他,但他知道,他们没有往死里整他。他今天还调侃高科老队友“光二”,曾经取关他,但是第二天还是悄悄地再次关注了他,这就是这些曾经有过背叛之心但终于没有一杆子到底的老友,经过时间的历练,他觉得他们还是可靠的可依赖的部分。
这些老友的慰藉,多少能够化解他惶惶如孔子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无处立足的窘境,因而他也能用孔子自嘲自己的语言,作出含笑应对的“新论语”:“驱赶人有两种赶法,一种叫武赶,一种叫文赶,文赶是看不出的赶,但是你也只好乖乖的站起来走人。”
沈巍一早,经过新胜桥下又一起短暂的言语冲突之后,他选择了“走人”,陪同广西来的一位粉丝,开启了到上海市区的一逛,其中自然包括外滩一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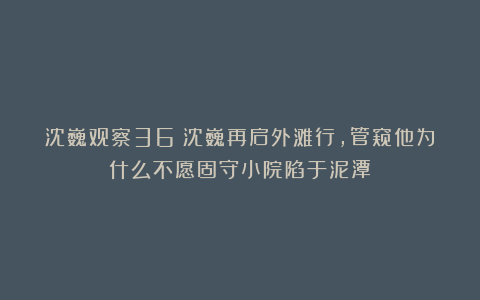
这不是沈巍今年第二次爆火以来的第二次市区行。大约在5月份的时候,他也曾经陪同一位来自外地的网友,到上海市区一游。当时,沈巍所在的位置,在小区的门外马路上,身边围拢的拍客还不是太多,但已经开始渐有影响,全国各地的粉丝,有人开始涉足此处,当时沈巍身边的拍客并不多,稀少的来客显然寡不敌众,大多规规矩矩,不像现在蜂拥而至的来人中鱼龙混杂,陌生面孔越来越多,也更无忌惮,导致摩擦越来越频繁。
对5月份这位外来的网友,当时沈巍说陪他去看看外滩,说走就走,当时天色已晚,就在黑暗中,沈巍带着那位外地来的粉丝,去看了一下外滩的万家灯火,一路上并没有停车,就像今天他带着广西粉丝,也是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上海闹市区。
那些熟悉的国际饭店、和平饭店、人民广场、光明电影院,曾经是沈巍儿时出没的地方,而今天,这是他偶尔必须跋涉一段长途才能达到的地方,他无由地发出一声慨叹:现在我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
在上海市区,他最为留恋的地方,就是福州路上的旧书店,他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耗在这条当年文化街上的新书店、旧书店里,所以,他今天,特意让车子绕到这条街上,去见识一下这条文化气氛日益疏远的文化老街。
他还特意提到绕到兴业路去,去遥观一下这里的一大会址,感受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拥有着新中国成立的最核心的密码。当年我从寄住的黄河路上,与亲戚家的孩子,穿过人民广场,沿着大同小异的石库门的一排排房子,走了不多远,就能走到一大旧址,但后来再去的时候,发现周边的老建筑都拆光了,只留下圣地相关的几排老房子。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不仅是沈巍的直感,也是每一个对这座城市有着记忆的过客,都能体味到的一种惊奇。
沈巍让他的视线,游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沟回,他太过熟悉,包括黄金荣扫街的地方,他也能够清晰地指出具体的定位,如果深刻地了解上海,他是一个出色的向导,他不仅对上海的地理面目,能够辨别出它们细微的纹路,而且对这些纹路里的历史积淀,都能竹筒倒豆子一般阐幽发微。他能够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活的指南针与导游图。
这样更显得游刃有余的行走的沈巍,自然不愿意把他的脚步固守在城市的一隅,遭受多如牛毛、寻踪上门来的吊打。
他今天直接否认了选择一座“小院”的打算,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意味着他要“奉陪出他的全部时间与生活”,而这不是他喜欢的生活。身边的人,无一不是动员他能够快速地确定这样的一座单门独院,让他在这里写字画画。
但是,换一个角度,这样的小院真的出现的时候,每天的沈巍,不是像牛马一样,活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空间里,不断像挤牛奶一样不停地哗哗挤出书画纸页,这样的生活,不要说是沈巍了,即使是一个普通人,愿意这样生活吗?
他一辈子的自由生活,在晚年的时候,却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挥汗如雨,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
你想沈巍会回到这样的作茧自缚的“小院”生活吗?
那些一步步想把他套入到“小院”的樊篱与囹圄的人,究竟是出于好心,还是出于一己私利呢?
所以,沈巍说:来到他的身边的人,很少有懂你的,尤其是其中还有一种人,是想指导你的。
他的潜台词中,这种指导你的,才是最可怕的一种人。
在沈巍的身边人中,常常以一种关心与爱护的口吻,为他打算,为他谋划,动员沈巍如何利用他的流量,赚一大笔财富。而设立一个固定的小院,就是这种最常规的思路之一。
但是沈巍清醒地知道,开一个小院,他就必须每天守着这个固定的空间,就像背上了一个包袱,而他驮着这一个包袱,能够“挤奶的”,他是唯一的“孺子牛”。整个小院里,唯一干活的就是他。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那些一门心思地为他设想着要打造一个独立的小院的人,难道沈巍不知道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吗?
所以,沈巍坚决不上套。他需要以自由之身,去走他选择的路。就像今天的上海市区之行,如果他有一个小院了,他还能移步出行吗?
实际上,一个不被束缚的人,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沈巍在2019年爆火之后,曾经被操控着,丧失了自我,并最终导致他退网归隐。
这一次他再次爆火,他对当初一窍不通的互联网有了知根知底的认知,他还会重蹈覆辙吗?
相信,沈巍正走在一条最庸常的智慧都能够选择的道路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他自嘲自己被驱赶的命运,但他自我的感觉很好,他怕的不是被驱赶,而是被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