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破译远古神灵的玉石面容
一组横跨数千年的史前器物,构成了一幅强有力的视觉图景,揭示了根植于长江流域、一条长期而连续的本土巫觋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绵延数千年,通过特定的身体改造仪式——纹面与穿耳——来定义自身,并以此区别于东亚新石器时代其他的文化领域。长江流域,尤其是其中游地区,成为了一个孕育复杂社会的熔炉,在这里,精神权威与艺术表现在史前时期达到了一个早期的高峰。
本文将追溯这一文化序列的演进:从双墩文化(约7300年前)以陶器为媒介的初步表达,经过凌家滩文化(约5300年前)玉石艺术的萌芽,直至石家河文化(约4000年前)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精神高度。这一清晰的演化路径,为我们勾勒出长江流域史前巫觋原型的变迁。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石家河文化中呈舞蹈姿态的玉巫觋形象,是长江流域一个历经三千余年发展的精神与艺术传统的巅峰结晶。该传统以仪式性的身体改造(面部刺纹与硕大耳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一种独特的宇宙观。本文将通过考古实证、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后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对这些非凡器物的内涵与功能进行深度的重构与解读。
第一部分:神圣传统的起源:长江流域的早期印记
1.1 仪式性身体改造的黎明:双墩文化(约7300年前)
长江流域巫觋传统的滥觞,可追溯至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该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塑人头像,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同时表现纹面与穿耳习俗的实物证据,为我们理解这一悠久传统的源头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基点。
-
面部刺纹(雕题/纹面):这件人头像的额头正中刻有一个同心圆,脸颊两侧则对称排列着五个可以连成一线的戳刺圆点 。这些并非随意的装饰,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图案,代表了“雕题”(额头刻纹)与“纹面”(面部刺青)的早期形式。这种规范化的标记体系,很可能是一种用以区分社会身份或精神角色的符号系统。
图:双墩文化陶人面雕像,双墩文化是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文化,距今约7300年,因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该遗址于1985年发现,经过三次系统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角器等大量文物,其中最具特色的是630余件陶器刻划符号。
-
穿耳习俗:人像的双耳耳垂部位有明显的穿孔,孔洞尺寸较大,清晰地表明在7300年前,硕大耳洞这一习俗便已确立,成为此后数千年长江流域神圣形象的关键特征之一。
-
材质与神情:陶像的制作材料也颇具深意。陶土中掺入了云母,使得人像面部在光线下闪闪发亮,这无疑是制作者有意为之,旨在赋予其一种超凡脱俗的神圣特质。人像嘴角微扬,面带一丝神秘的微笑,传递出一种超越世俗的静谧与智慧,仿佛处于某种宗教体验或出神的状态。
图:双墩文化陶人面雕像,陶土中掺入了云母,使得人像面部在光线下闪闪发亮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更北方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均有出土体现巫师形象的玉石器,陶塑等,但这些巫师形象却均未体现出“耳洞”,“纹面”这两个特征,受限于当前原始材料的佐证,因此至少当前可认为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时期巫师形象来源应该是和江淮流域的文化交流。
图:在长江中游,下游,以及北方的红山文化区均有出土体现巫觋形象的玉石器,但这些形象均未体现出“耳洞”,“纹面”特征。因此,尽管史前中国各大文化区可能都有巫师存在,但其形象特征可能各有所不同。
1.2 玉巫觋的登场:凌家滩文化(约5300年前)
时间推移约2000年后,在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中,我们看到了巫觋形象从陶土向玉石这一更高等级媒介的转变。凌家滩出土的玉人,是连接早期陶塑与晚期石家河玉雕的关键一环,标志着巫觋信仰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显著提升。当然,凌家滩巫师玉人形象在以往的文章已有分析,也是和其他文化(红山文化)有所交流的产物。
图:凌家滩文化巫师玉雕像
-
文化特征的延续:凌家滩玉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其硕大的双耳以及耳垂上清晰的穿孔,这直接延续了双墩文化的身体改造传统 。此外,其面颊两侧似乎也刻有浅淡的纹饰,暗示了纹面习俗的传承。
-
姿态与功能:与后世石家河玉人充满动感的舞姿不同,凌家滩玉人呈蹲踞姿态,双臂弯曲,十指张开置于胸前,仿佛在进行某种祈祷或与神灵沟通的仪式 。这种静态的、沉思的姿态,可能代表了巫觋在仪式中进行冥想或祝祷的特定环节。
-
技术与材料的飞跃:玉,作为一种珍稀且加工难度极高的材料,其选择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凌家滩先民掌握了惊人的微型管钻工艺,能够在这件玉人背后钻出直径仅0.15毫米的隧孔用于佩戴,其抛光技术也极为精湛 。从普遍的陶器到贵重的玉器,这一材质上的飞跃,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专门化的玉器手工业的出现,服务于一个能够掌控稀缺资源和高超技艺的精英阶层,神圣形象的塑造与精英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系列考古证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从双墩到凌家滩,硕大耳洞与纹面这两个核心特征在一脉相承的地理空间内延续了超过两千年,这强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巫觋文化传统的本土起源性与连续性,而非源于后来的外部影响。同时,承载巫觋形象的物质媒介从陶土到玉石的演变,也清晰地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当神圣的形象必须以最珍贵的材料来塑造时,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权威正日益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物质的价值与神权的象征开始合二为一。这为理解石家河文化时期宗教活动的“独占性和垄断性” 提供了重要的前史背景。
第二部分:技艺与精神的巅峰:石家河的巫觋舞者(约4000年前)
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将史前玉器文明推向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在这一时期,延续数千年的巫觋传统与登峰造极的琢玉技艺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表现力和精神感染力的艺术品——呈舞蹈状的玉巫觋。
2.1 史前琢玉工艺的丰碑
石家河文化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谭家岭遗址一次性出土的240余件玉器,其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彻底改写了中国古玉史。石家河的玉工们娴熟地运用了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多种复杂技术,常常在尺寸极小的玉料上进行创作,其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从象征祥瑞的玉凤 ,到形态各异的神人头像,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高超的技术,更透露出一个成熟、自信且内涵深刻的文化与宗教世界。
图:石家河文化玉神祖面的特征就是耳洞,所有体现神/人面形象的玉器均拥有硕大的“耳洞”
2.2 解码舞蹈的巫觋:狂喜的图像学
石家河玉巫觋最震撼人心的特征,是其充满动感的舞蹈姿态。这些玉人不再是凌家滩文化中静态祈祷的形象,而是被定格在祭祀狂舞的瞬间——双臂张开上举,双膝弯曲下蹲,身体呈“介”字形,充满了力量与动感。这种姿态并非单纯的艺术造型,而是对巫觋仪式核心行为的精确描绘:通过狂热的舞蹈进入出神状态,从而实现与神灵世界的沟通。
图:石家河文化巫师舞动片雕玉饰件,法国塞奴仕美术馆收藏,虽被认为可能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但该巫师形象特征和雕刻技艺均为石家河文化风格,并不见于西周。这种体现石家河巫师整体形象的玉舞人,在全球收藏机构中存有两件,如图所示稍有不同。
-
核心图像特征:
-
硕大耳洞与耳饰:作为长江流域巫觋传统的标志,硕大的耳洞在石家河玉人身上得到延续和强调。许多玉人不仅有巨大的耳孔,还佩戴着玉环,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特征作为巫觋或神祇身份标识的重要性。
-
獠牙与威严神情:这些玉人常被刻画为大眼圆睁、阔口微张,甚至露出獠牙的形象 。这表明它们并非普通人的写照,而是巫觋在仪式中发生神性转变的瞬间。獠牙象征着巫觋获得了某种猛兽(如虎、野猪)的力量,或正在扮演某个具有威慑力的神灵。其神情充满了宗教的威严与狂热,而非世俗的平和。
-
华丽的冠饰:玉人头戴复杂的冠冕,有些冠饰上还融入了鸟类或其他动物的元素,这既是其崇高地位的象征,也暗示了其与天界或动物神灵的特殊联系。
2.3 巫觋的法衣与神性转化
石家河文化出土的许多玉器,包括各种动物形象和神面像,其背面都钻有可供穿系的小孔。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表明这些精美的玉器并非孤立的摆件或手持物,而是被大量缀缝或镶嵌在巫觋的祭祀法衣之上的组件。
从凌家滩玉人静态虔诚的祝祷,到石家河玉人动态的狂舞,这一图像学的演变,深刻地反映了宗教观念与祭祀实践的进化。它标志着一种更为主动、更具表演性的宗教仪式的成熟,巫觋的身体及其在舞蹈中的超常状态,成为了通神仪式的核心载体。石家河的艺术家们选择将祭祀仪式中最高潮、最富神性的瞬间——狂舞,用最珍贵的玉石永恒地记录下来,足见其在整个信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同时,石家河玉人所呈现的人兽合一的混合形态,完美地诠释了萨满式转化的核心理念。巫觋是行走于人界与神界之间的“边缘人”,而这些玉器艺术正是在捕捉其处于“转化”过程中的神圣状态。獠牙与巨眼并非写实,而是象征着巫觋已成功引导或化身为强大的动物守护灵,这与《山海经》中大量人兽同体的神祇形象在思想内核上高度一致。
第三部分:跨文化的比较视野
3.1 两种传统的对话:石家河与北方红山文化
通过与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进行比较,长江流域巫觋传统的独特性得以更加清晰地彰显。这两种伟大的史前文化,虽然都创造了辉煌的玉器文明,并在信仰体系中赋予巫觋中心地位,但其对巫觋形象的艺术表达却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规范。
-
红山文化的巫觋形象:红山文化的玉、石、陶质人像,通常表现为静态的、肃立祈祷的姿态 。其面部特征高度概括,双眼微闭或半睁,表情呈现出一种内向的、沉浸于冥想的“痴迷状态” 。
图:红山文化祈祷玉人,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 -
关键的差异: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红山文化的巫觋造像上,普遍缺失硕大耳洞和明确的面部刺纹这两大定义了长江流域传统的特征 。尽管红山文化也制作和使用玉玦等耳饰,但穿戴大耳饰并未被视为巫觋形象的核心身份标识而被刻画在神圣雕像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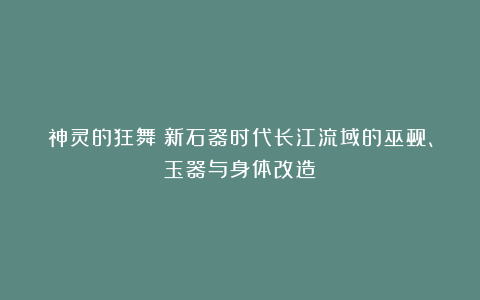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平行发展与核心差异,下表对各项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
| 特征 | 双墩文化 (约7300年前) | 凌家滩文化 (约5300年前) | 石家河文化 (约4000年前) | 红山文化 (约6500-5000年前) |
| 主要材质 |
陶 |
玉、石 |
玉 |
玉、石、陶 |
| 面部刺纹 |
存在 (戳点、圆圈) |
|
|
缺失 |
| 硕大耳洞 |
存在 (大穿孔) |
存在 (大穿孔) |
存在 (突出的大穿孔) |
巫觋像上缺失 |
| 身体姿态 |
|
静态 (蹲踞祈祷) |
|
静态 (站立祈祷) |
| 面部表情 |
神秘微笑 |
中性、程式化 |
威严、张口、露獠牙 |
出神、闭目/半闭 |
这种在宗教核心图像上的显著差异,并非偶然的风格选择,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观和仪式体系。硕大耳洞作为一种持续了数千年的身体标识,在长江流域可能象征着某种特殊的“聆听”神谕的能力,或是佩戴特定神圣徽记的资格。这一特征的有无,如同文化基因的显性与隐性,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两大文明圈的轮廓。
3.2 青铜的回响:在三星堆文化中的不朽传承
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其精神内核的消亡。数百年后,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兴起了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出土的巨大青铜头像、面具和立人像,其最令人震撼的特征之一,便是与石家河玉人如出一辙的、贯穿耳垂的硕大耳洞。这种高度相似的、非同寻常的图像学元素,绝非巧合。它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内部存在着一条深刻而持久的文化传播与认同链。发源于石家河文化圈的核心信仰符号与审美范式,沿着长江水系向上游传播,被后继的三星堆文明所继承、改造和发扬,并以更为雄伟的青铜艺术形式予以再现。
图: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人面像均有“耳洞”,仅右上这种体现“纵目”形象的青铜人像没有“耳洞”。
3.3 全球视野下的共鸣:史前巫觋的普遍性
将视野扩展至全球史前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巫觋(萨满)作为沟通人与神灵世界的媒介,是一种近乎普遍的文化现象 。其仪式行为,如借助舞蹈音乐进入出神状态、与动物神灵沟通、使用特定的法器等,在全球各地的早期文化中都留下了印记。
-
特殊的地位:这位女性被单独埋葬在一个精心修建的墓穴中,并用一块巨石封顶,显示出其在社群中的崇高地位。
-
动物守护灵:墓中随葬了数量惊人的动物遗骸,包括50个完整的龟甲、豹的骨盆、鹰的翅膀、野猪的前臂骨等 。这与巫觋作为“动物之主”的观念完全吻合,这些动物并非食物,而是其在精神世界中的同盟与力量来源。这一观念,与石家河巫觋将动物玉雕缀于法衣之上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
身体的印记:考古研究发现,这位以色列巫觋生前患有骨骼疾病,导致其行走姿态异于常人 。在全球的萨满文化中,身体的与众不同(无论是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改造)常常被视为具有特殊精神潜质的标志。这与长江流域通过纹面和穿耳等主动的身体改造方式来标识巫觋身份的做法,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观念:巫觋的身体本身,就是其神圣职能的载体和明证。
第四部分:来自典籍的微光:巫觋实践的文献印证
尽管史前玉器沉默无言,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寻找到解读其文化密码的线索。成书于东周时期的《楚辞》与《山海经》,虽然与石家河文化存在千余年的时间间隔,但其诞生的地理与文化背景,正是石家河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楚文化。因此,这些典籍中保存的关于巫术、祭祀和神话的记述,可以被视为一种“深时”的口述史,为我们理解史前巫觋的形象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4.1 《楚辞》中的狂舞与华服
《楚辞》,尤其是其中的《九歌》,被普遍认为是根据楚地民间祭神乐歌加工而成的文学作品,其内容生动地反映了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浓厚巫术文化传统 。《九歌》中描绘的祭祀场景,与石家河玉巫觋的形象形成了惊人的互文关系。
-
《东皇太一》篇中,“灵偃蹇兮姣服” ,意为“巫师穿着美丽的服装,跳起优雅回旋的舞蹈”。句中的“偃蹇”一词,生动地描绘了舞蹈中屈伸起伏的动态,与石家河玉人弯腰屈膝的“介”字形舞姿高度契合。“姣服”则印证了巫觋在仪式中身着特制华服(即“法衣”)的习俗。
-
同篇中,“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意为“手抚玉饰的宝剑,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此句不仅点明了玉器是巫觋仪式中的重要法器,更强调了其听觉效果。“琳琅”描绘了众玉佩在舞动中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这正是石家河巫觋满身玉饰在狂舞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珥”字本指耳饰,在此虽可能指剑柄上的饰物,但也与整个文化中对耳朵装饰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有趣的关联。
-
《云中君》篇中,“华采衣兮若英” ,意为“(巫师)穿着像花朵一样华美的衣裳”。这再次强化了对巫觋法衣华丽多彩的印象,为我们想象那些石家河玉器如何被组合、点缀于织物之上,提供了生动的文学想象。
4.2 《山海经》中的神话形态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地理与巫术的奇书,其中充满了人兽同体的神祇形象,反映了与萨满教“转化”观念相通的宇宙观 。书中对神祇形象的描述,为我们理解石家河玉人的一些奇特造型提供了神话学的解释框架。
-
“珥”的母题——作为神祇标识的耳饰:书中反复以“珥”(佩戴在耳上)来描述神祇的特征与神力。例如《大荒东经》记载了一位名为“禺虢”的海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 ,即长着人的面孔、鸟的身体,以两条黄蛇作为耳饰。
-
解读:这一神话母题为考古发现的硕大耳洞提供了功能与象征层面的解释。巨大的耳孔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能够佩戴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饰物。在《山海经》的想象世界里,这些饰物可以是蛇这样充满原始力量的动物。将动物神灵“穿戴”于耳上,成为一种掌控其力量、彰显其神性的终极表达。这使得石家河玉人那看似夸张的耳洞,在神话的语境中获得了深刻的合理性。
将这些后世文献与史前考古发现并置对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化基因的传承脉络。石家河时代的核心宗教观念与仪式行为,并未随着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结束而彻底湮灭,而是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渗透到后继的楚文化之中,最终被以诗歌和神话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中华文明记忆深处的一部分。这些文献,为我们跨越数千年的时空,去“聆听”那些沉默玉器所讲述的故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钥匙。
结论:长江流域不朽的精灵
通过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巫觋形象长达三千余年演变历程的系统梳理,本文的结论得以清晰呈现。从双墩文化的陶塑雏形,到凌家滩文化的玉石转型,再到石家河文化的艺术巅峰,一条以纹面与硕大耳洞为核心标识的本土巫觋文化传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稳定地传承、发展,形成了与北方红山文化截然不同的精神与艺术范式。
石家河文化无疑是这一伟大传统的集大成者。它不仅代表了史前东亚地区琢玉工艺的最高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将数千年来积淀的宗教观念与仪式实践,通过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力,物化为一件件充满生命力的玉雕杰作。那呈“介”字形狂舞的玉巫觋,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是石家河文明精神世界最凝练、最深刻的表达——是艺术、宗教与仪式的完美融合体,是通神瞬间的永恒定格。
这一古老传统的生命力并未因石家河的远去而终结。其核心的图像符号,如硕大的耳洞,在数百年后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中得到雄伟的再现;其内在的巫觋精神,在楚文化的诗歌与神话中获得了不朽的文学形态。这充分证明了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个重要、且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中心,其文化影响力深远而持久。
今天,当我们凝视着这些跨越四千年而来的玉石精灵,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原始、神秘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们是长江流域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早已失落的信仰世界中,关于沟通天地、神人共舞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