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心之期许,果然。
落雨的绍兴,才更有绍兴的味道,或许卷了大多游人的兴致,却还了老街难得的清静。
青灰,暗绿,乌黑的瓦当和石板路,在雨里泛着冷色,地上的积水和溅起的水珠,每一滴都倒映着街上的霓虹,像一幅未干的油画。
百草园出来,是一条胡同,胡同口有一座石坊,南面坊书“仁里”,且有楹联:“旭日辉仁里,祥云护德邻”;北面坊书“德邻”,楹联:“翠竹虚心有节,君子朴实无华”,细雨沾湿了石坊,字迹却鲜亮了许多。
百草园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细考却是朱家的,熟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为证: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
文中提到的朱文公,是朱家的祖先,现代铜艺建筑大师、熔铜艺术创始人朱炳仁就是这一脉后裔。
绍兴,鲁迅故里。
朱家与周家比邻而居,离得有多近呢,就好比那座石坊,一面是“仁里”,转身就是“德邻”。
鲁迅故里当然是鲁迅先生的故园。
鲁迅是谁?
民国时期,有一个外国的汉学家曾说,“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最懂这个国家,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蒋介石,还有半个,是毛泽东。”
当年冯雪峰把这句话学给主席听时,主席笑了,未置可否。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引发全国哀悼。为纪念其精神品格和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出席葬礼,递交了民国政府批准的10万法币慰问金,并发表祭文。
绍兴地方当局还在鲁迅故里核心区域设立了那座刻有仁里和德邻的石坊,以彰显其人格光辉。
远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哀悼,1938年,为纪念鲁迅先生,毛主席还特意命名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就是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他生在清末,名闻于民国时代,难得的是无论是民国,还是红色中国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能为敌对的双方同时认可,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给予极高评价的实为罕见。
八十年代中期,关于鲁迅的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渐入学术领域,学界与民间的“鲁迅争议”,到了新世纪,有了“还原鲁迅”的主流。
记得读高中时,经常会要求大段大段地背诵先生的经典,每逢考试都要“读取一段话,深刻分析其思想内涵”,从不愿为背诵付出努力的自己,宁愿舍弃这个得分点,也不愿去抠先生晦涩难懂的句子。
私下里,却寻来未被选中的文字读得津津有味。记得故事新语里有一篇《铸剑》,写了一个叫眉间尺少年为父报仇的故事,看得心惊胆寒,手心冒汗,比那些精选在课本里的文章好看得太多。
《铸剑》初发表时,其实名为《眉间尺》,写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中有如下的记载: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
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
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
及至君觉,杀干将。
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
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
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
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
遇客,欲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
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
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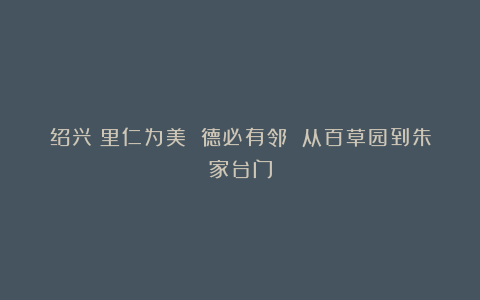
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日三王冢。”
看完《铸剑》,拍案称绝,细腻,鲜活,刺激,悬念迭出,简直停不下来,原来先生才是扩写的大师,古语短短几段,先生笔下便是一篇好看的剧本杀。
那以后先生也不再是那个端坐在书案前,“横眉冷对千夫指”不怒而威的样子了。
后来是从陈丹青的书里看到了先生的另一面,认同他说的“大先生好看,好玩”。
单看先生的神态,存留下的照片中绝无媚俗之气,从容而孤傲,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好看!他自己也说样子好看。有一次,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称赞他好样子,先生应声说,“早年的样子还要好。”
如何好玩呢,有文章说:
有一天,章衣萍的太太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从四川北路往家走,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众人一直撵到他家门口。
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老先生“噢、噢、噢……”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他笑着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得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
章太太这才明白,先生又在开玩笑,因为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再读鲁迅,没有了老师要求,也不用顾虑考题的分数,倒是读懂了先生的体贴,犀利,厚道,激烈,清醒和不妥协。
文章的张力,也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也是人格的维度,先生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亦成独特风格,字里行间能读出先生的“贪生”和“怕死”,明白了眉间尺为啥毫不迟疑地削掉自己的头颅,在翻滚的油锅中追逐厮杀仇人,正是因为痛恨死亡,才尤为渴望新生。
“救救孩子”
“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
“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纪念也从人间消去”(《坟》)。
每每读到先生这些生生死死的文字,倾听他嘶哑的低吼时,眼泪总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久久不能自已,为先生的善良,为他的悲悯,这是他文字里的力量。
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这一点绍兴人做到了。
先生笔下的人物活在了绍兴的街巷间,活在烟火街巷里,绍兴黄酒和茴香豆的醇香,弥漫在美食作坊和船坞里。就连地图上本没有的鲁镇,也梦幻般地显现在绍兴柯岩景区,在碧波荡漾的鉴湖之滨,一时间恍如踏进了另一个时空,走进了先生笔中的世界。
那晚,细雨织成薄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周家台门徜徉到周家新台门,还能看到一座嵌着铜瓦的大宅院,门楼两侧挂有铸铜的一副对联:“熔铸春秋 耕读传家”,这就是朱文公家族的一脉,朱家台门。
朱家台门的铜艺从清末的铜铺做起,到朱炳仁这一代,不仅没有失落,还实现了古老的铸铜到现代熔铜艺术的飞跃。
清同治末年,绍兴石灰桥(今日晖桥)河下,朱雨相、朱庆润兄弟弃文从匠,挂出“朱府义大铜铺”的招牌,把书香底蕴铸入铜艺,在铜盆、酒壶上雕龙刻凤。当时绍兴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嫁女的铜,朱家的工”,极尽了对朱家铜艺的推崇。
第二代朱宝堂迁店至北后街,更名“瑞昌铜铺”,以佛心铸铜器,为寺院精制香炉法器,将虔诚和修行熔入每一件禅修器物。
2006年,朱家工坊失火,朱炳仁面对眼前的狼藉,伏下身去,发现大火熔化了铜液,呈现出一种自然肌理之美。在众人的哀伤里,朱炳仁却灵光一闪:“能否丢开模具,熔铜而塑”,熔铜的艺术灵感油然而生。
那天恰逢朱家添人进口,朱氏铜艺涅槃而生,应了那句“祸兮福所倚”,人都说,这是朱家“修来”的福气。
从此以后,朱炳仁的熔铜作品一发不可收,先是《阙立》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后熔铜山水、梵高《向日葵》系列在柏林、威尼斯展上引发“熔现实主义”风潮。
朱炳仁说到熔铜艺术时说,上天给了我一个新的密码,一个铜文化发展的新密码。
雷峰塔重建时,朱炳仁大胆提出使用铜瓦,为塔身铸铜衣,着金身,既能防蛀,更显佛塔神韵。就这样,雷峰塔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西子湖畔,雨天铜瓦敲击声清越悠长,与西湖烟雨形成亦刚亦柔的和声。
后来,朱军岷(朱炳仁之子)在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用数千片铜瓦复原“黛瓦长廊”。雨日里,铜瓦泛幽蓝光泽,与河道烟雨倒影交织,诗云:“铜瓦一片承匠魄,烟雨半帘邀客舟”。
一条街上两台门,周家与朱家两个家族跨越百年诗书耕读,铜铸春秋留下千古佳话。
绵绵的细雨里,游人不多,石栏下,石埠旁,有几只乌蓬小舟,载着几对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一时间犹如穿越会稽山,披着蓑衣的船夫坐在后梢,竟然是不用手,而是光着脚来摇橹的,脚踏在桨柄末端,一伸一缩,那桨便一上一下地划水,即使是两只船相向而遇,也能平稳自如,交错穿行。
说来也巧,很多年以前去杭州玩,看上了一个铜艺香薰台,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伏在青绿的荷叶上,古朴的青铜绿完美地衬出蛙与荷叶底色,虽然只有手掌大小,可一路背回来,还是沉甸甸的,现在还一直摆在桌案上。
喜欢就点在看
喜欢就请分享